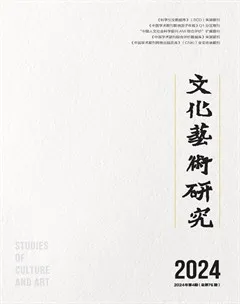越界与变脸:激进文艺思潮的前世今生(三人谈)
摘要:激进思潮与文艺有不解之缘。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感性的文艺与政治的询唤永远在纠缠打斗。20 世纪60 年代席卷全球的激进运动,既产生了鲍勃·迪伦、滚石乐队,也推起了福柯、德勒兹以及今天在中国大热的齐泽克、巴迪乌、韩炳哲等。激进思潮不断越界、变脸,挟互联网之便利,与全球盛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各种意识形态话术病毒式传播,去疆域化成了部落化,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添加更多焦虑和撕裂。聚焦“后学”激进文艺思潮的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从激进文艺理论的美国化、中国化的角度,反思情绪骚动(或曰“情动”)与理性实践的失衡,乃是知识人的职责所在。
关键词:激进思潮;美国化;中国化;情动;齐泽克;韩炳哲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4)04-0010-08
感性的文艺与政治的询唤:激进思潮的“ 美国化”和“ 中国化”
刘康:激进思潮与文艺有不解之缘。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感性的文艺与政治的询唤永远纠缠打斗。20 世纪60 年代席卷全球的激进运动,既产生了鲍勃·迪伦、滚石乐队,也推起了福柯、德勒兹以及今天在中国大热的齐泽克、巴迪乌、韩炳哲等。但今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什么是“美国化”与“中国化”。
先说中国化。文艺学是不是很中国化?中国大学的文学系都分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还有文艺学专业,这是不是很有中国特色?那么,这是中国化吗?文艺学源自苏联,这算不算苏联体制的中国化?中国的人文学科现在变化很大,但我感觉在体制、机构层面,以及在政治无意识或者潜意识层面,都还是苏俄化,几十年来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改革开放40 年以来,欧美思想和学术观点大量涌入中国,其影响在每一个学者的研究和著述论述上都得到体现。但是在学科组织结构、学术模式、思维逻辑上,大致上还是苏联模式的。我从海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看得很明显。虽然中国从20 世纪中叶开始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对抗,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苏俄式的学术和思维架构,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我说,这是一种“political unconscious”(政治无意识),不完全是制度和结构上的东西。这种体制、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或者说这种政治无意识,自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接轨,与现代世界的思想理论碰撞,有很多摩擦、冲突。既有思想上的巨变,也有机构上的变与不变,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思考的课题。
大概从七八年前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叫“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包括学术机构和建制、思维模式和方法等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中国问题。这是否就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不然。中国化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特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自有一套逻辑,有一套表述,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近三四十年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理论,算不算是普遍真理?其实,这些理论都是在批判和反思西方启蒙理性认定的普遍真理。再进一步想,这些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了吗?这就更说不清楚了。所以,简单地说西方理论中国化不太合适。但是,西方理论遭遇中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摩擦、矛盾、对立,都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要从机构(institution)角度,从它的制度、结构、思维模式和潜意识、潜在的逻辑的角度,来认真反思和批判。曾军一直以来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近几年张法、朱国华、杨建刚等人也写了不少文章,讨论中国文艺学的谱系、体制的建构等。现在,我们大家慢慢走到一起,都在想这个问题,令人欣慰。就我本人来讲,法国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尤其是福柯,他讲得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指出这是一个知识与权力的架构。这里说到的知识,主要是讲它的结构、机制与体制等;权力,当然也不是简单地说行政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它来自方方面面。福柯说得很透,他说权力在当代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毛细血管化”的运作,它无处不在,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每个人的思维的细微末节,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被这个知识与权力的架构所左右。
那么,什么是欧陆理论、法国理论的美国化?我觉得“美国化”,也许可以套用“中国化”的说法。法国理论,或欧陆理论,它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就是现代的普遍性或曰普遍真理,是当代西方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些理论到了美国之后,我们确实能看到它们与美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暂且借用这个说法。
美国化有两个套路。第一个套路,仍然是将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与欧陆形式主义文本解读的套路,与英美的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结合在一起,给英美的文科教育制度化提供一个新的动力。所以,它主要是一个学科化或者文本化的动力,延续的是欧美的自由主义,亦即被称为“Liberal Art”的传统,是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文艺自洽、学术象牙塔的套路。另一个套路,就是很强大的左翼激进主义,20 世纪60 — 70 年代的法国理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左翼的、批判的、干预社会的特征。我们有时候称其为批判理论,有时候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等。这一股左翼思潮到了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五花八门,不完全是法国理论,也包括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等欧陆国家的思想界,都是在反思批判康德以降的启蒙思想。当然,美国比较独特,它在科技上有大量的原创,但在思想上、人文上没有太多的原创。思想集市的说法来自启蒙运动的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Milton)和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后来美国把英国的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了。美国是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是一个思想和学术的大卖场、集散地,也就是说它不一定需要原创。美国不是西方文明的原创地,而是传承者、传播者,这就是美国的特色和套路。刚才我说过,它那种文本细读的、形式主义的学科和文本化套路,跟英美的新批评完美对接,是一种思想的贩卖或者变换。欧陆激进思潮到了美国,其路径也是一样,它有几个“二道贩子”,另外还有一伙“搬运工”。相比之下,“二道贩子”把理论包装上市了,比搬运工的层次略高一阶。我所说的欧陆理论的美国化,就是靠这些“二道贩子”和“搬运工”来完成的。“二道贩子”里有两个人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我现在的同事詹姆逊,他是美式西马的一个代言人。他在中国影响巨大,演变出了一个“中国詹姆逊主义”。另一个是萨义德,已经去世多年了。没有人说他是西马,也没人说他是后现代,他是后殖民理论的首创者或设计师。他下面有印度的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学者,他们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建设者。这批激进的人物和他们这一批激进的思潮应该是在最近的40 年开始的。
这40 年正好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彼时我刚去美国,适逢欧陆理论美国化的酝酿和传播的过程。我到美国时,后学的“大卖场”已经建好了,可以说到处都是后学“大润发”,每个大学的比较文学系都是一个大卖场的分支,我们就把各种新鲜的东西都捡过来,包括詹姆逊和萨义德。不仅是激进理论,文本化的那套理论也很流行,比如耶鲁的保罗·德曼和西利斯·米勒,还有乔纳森·卡勒,他们都是欧陆理论的“搬运工”。欧陆理论在美国传播和流行了40 年,应该说他们成功孵化出了一个很具有美国特色的理论,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我们讲“后学”,比如后结构主义时,可以说完全是法国的,跟美国不搭边;但提到后现代主义,就有一半要涉及美国,比如詹姆逊就讲过很多后现代的内容——当然,还是以法国人为主。但是到了后殖民主义的时代,法国人在学术界已经渐渐没有了声音。
近40 年来,法国还有当年的思想高原吗?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了。法国现在正好有四位热闹的人物,这“四大金刚”不完全是法国人:巴迪欧和朗西埃是法国人,另外还有意大利的阿甘本,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齐泽克。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他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现在美国学界就看中了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我在美国曾与齐泽克有一场论战,对于他利用这个身份掩饰其话语矛盾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这场论战在英语学术圈影响很大,但在中国出于某些原因从未被提起。实际上,“四大金刚”都很边缘,在法国乃至欧陆没什么动静,但美国人喜欢他们。因为当今世界,英语是通用语言,英美人喜欢的也就变成世界的。中国最近这几十年的学术译介,主要来源都是英语。所以英美学界说啥,中国人就跟着说点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美国化理论真正形成气候的就是后殖民理论。这些年来,我写了一些中英文的文章,介绍后殖民理论在美国如何演变,它如何从一个非常晦涩深奥的、小众精英的学术话语,变成一个全面参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口号。现在美国社会认识到,这正是造成美国社会分裂、部落化和意识形态化,推动美国版本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通常叫作“critical race theory(批判种族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批判理论其实不是一回事,也许其中能找到左翼思潮的渊源,但其实找不到一块去。后殖民理论依据的是美国经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地地道道的“世界村”,但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不治之症”,就是美国的黑奴问题。会不会有朝一日,这个不治之症就把美国给摧毁了?说不定。一个国家从兴到衰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罗马帝国历经千年从兴到衰,一时好一时坏,美国会不会变成第二个罗马帝国,现在犹未可知。但大家都知道,黑奴制度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症结,它引发的黑人运动从南北战争直到今天,现在变成了一个撕裂美国的重要原因。
就这个话题,我最近在《上海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去疆域化,还是部落化?——英语人文学界的理论旅行》的文章,我现在还在写后续的文章,但写得很费劲,因为时势和时局的变化太大,有时出乎我的意料。a 最近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国内媒体上可能没有太大波澜,但绝对值得中国学界的关注。这件事就是三位常春藤联盟学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受到国会议员质询和保守派严重的攻击,相继宣布辞职。这一事件和我们讨论的题目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的激进理论演化到现在的美国化,已经成为现在美国社会撕裂和部落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影响美国乃至影响全世界。当然,美国真正的意识形态、真正的政治动力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criticalrace theory”,而是现在甚嚣尘上的,我称之为“两民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后殖民等激进理论都做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推手或附庸。所以,美国的学术将向何处去?激进理论将向何处去?有什么答案吗?我很担忧,但目前看来无解,我觉得事情越变越糟。
“ 山寨”和“ 游击性”:激进思潮在世界中的重组
刘欣:谢谢刚才刘康老师介绍的激进理论,包括中国化以及美国化中出现的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说激进理论是“在世界中”的?因为激进理论虽然是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或话语,却已经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它成为了一种日常生活的语言,它就变成了话语- 实践,进而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包括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我想先讲一下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激进理论的中国化”。关于激进理论,我们都知道,与马克思是密切相关的。在讨论中国化时,我想借用“山寨”这一概念。英文里面的“shanzhai”实际上就是山寨的拼音,所以用“山寨”这个词来阐释中国对于激进理论的研究还是很有意思。山寨首先要求的就是一种游击性,山寨的产品是要跟原产的产品打游击的,它把最新的技术复制过来,在中国的市场中进行贩卖。
那么,中国的激进理论研究是不是也有这种游击性和灵活性,有这种及时的变通性?实际上是有的。根据我的观察,激进理论最早进入中国就是因为刚才刘康老师提到的“四大金刚”。齐泽克大概在1999 年才被中国知道,巴迪欧大约在2006 年传到中国,彼时已经是互联网非常普及的时代了。之后的阿甘本、朗西埃等人进入中国,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非常成体系的激进理论原文和译文被共享到网络。这是激进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一环,正是需要有这样的一批人作为中介代表,来打“游击战”。这些中介代表最初是缺少学术地位和资源的,后来在这种传播过程中积累了“搞学术”的象征资本。这种“游击战”非常有意思,对于我们这一波20 世纪80 — 90 年代生人和以后的年轻学者具有不小的影响力。在没有掌握大量学术资源的时候,他们还是以网民的身份出现,或者说是网络学术游侠,我前面所说的山寨性就体现在这种游击性上。此外,也有一些小的平台,比如以豆瓣为中心的论坛和一些公众号,会形成一些相对集中的对激进理论的翻译和分享。
略显悖论和讽刺的是,通过这种“游击战”,激进理论研究逐渐成为了集团作战,成为正规军。如果说以前是游击作战,那么现在就是变成大规模作战,我们可以看到,对巴迪欧和齐泽克的研究已进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体现出一种从上到下的意图。刚才我们提到了山寨,也就是将原件进行重新组装,将它拆开再重组。那么,如何重组,也就是在所谓的“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来重组激进理论。
但这里提到的“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加了引号的,激进理论的那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齐泽克,实际上对于“中国崛起”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同时,山寨本身实际上也带有一种游戏性。比如我们熟知的在山寨的产品里较早出现的球鞋和运动鞋,在我的学生时代,很多产品将类似阿迪达斯“Adidas”的品牌名称的字母顺序调整一下,就成为一个新的品牌,从而避免版权纠纷,山寨产品就这样产生了。这就有点像达达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那些文字符号的游戏,相对来说就具有一种游戏性,但这种游戏性在我看来多少都带有一些喜剧色彩。之前我也考察过齐泽克这个例子,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齐泽克的形象和他的这种喜剧性就会越来越彰显。在类似微博、豆瓣等网络平台大量传播时,网友们会起一些非常浮夸的标题,比如“哲学界大拿齐泽克:看看现在的中国,唱衰社会主义的都出来走两步”,或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牛”“世界哲学家齐泽克看看中国如何崛起”,以诸如此类的标题来凸显齐泽克的理论,或者说激进理论跟中国的契合性,这完全是一种扭曲。
刘康:还有一位哲学家韩炳哲,他有一本书就叫《山寨:中国式解构》[1]。他认为,中国式解构就是典型的中国现象,彰显了一种中国精神,带有一种颠覆性。他都是用德语写作,我们很快就将它翻译出来,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十几本他的著作。韩炳哲写的书在英美也销路不错,他是一个流行的明星式的畅销作家,写作的文体算是“哲学鸡汤”。今天这个时代,要扩大传播就一定要流行化或者说游戏化,要畅销,要鸡汤。但韩炳哲的东西在德国本土的畅销程度似乎不怎么样,他和德国人不是一种气质。我最近每年都要去德国待几个月,据我观察,德国的学术界几乎没人谈论他,他的名声在外。其实,只要是欧陆理论,势必要经过法国化、美国化的过程,才能被世界承认。像巴迪欧以及巴迪欧的学生梅亚苏,他们在法国本土的影响力都极其有限,甚至几乎不存在影响力。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在美国的传播,得到美国人的喜欢,进而再影响到中国人喜欢,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些法国学者的处境比较尴尬。激进派不受法国人自己的喜欢,那他们要怎么办?谁来替他们包装?是让美国人替他们包装吗?但是法国的学界事实上又瞧不起美国人,这到底要怎么办?
刘欣:是的。所以山寨化的最后一个体现就是这个理论最终要经过我们中国学者的删减重装,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学科化,这其实就是一种去政治化。因为关于学科,福柯曾说“discipline”,就是“规训”,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学科”。学科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规训,包括我们的文艺学实际上也是这样。
刘康:福柯与他著作的英语译者曾有过讨论。他说,“监控”这个词,如果严格翻译成监控,并不能完全体现它表达的一些内容,使用“discipline”一词可能比法语的“监控”更好。他那本书中法语的原文是“surveiller et punir”,“surveille”翻译成英语就是“surveillance(监控)”,“punir”就是“punish(惩罚)”。他的英语译者提议,不用“surveillance”,而用“discipline”会不会更好?福柯表示这个词选得好。其实,福柯一开始说的是监控,而规训就是监控。这个词现在在学术界都主要指“学科”。
刘欣:对。所以在中国的学科中,激进理论在哪些学科最受欢迎?首屈一指的就是我们的文艺学。
刘康:对,肯定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学者是不是都在文艺学学科?
刘欣:也不完全是,也包括政治哲学,还有外国文学的比较文学。这些学科都非常需要激进理论的资源,所以相当于将它诗学化了。这也是2011 年刘康老师在美国Positions 期刊上与齐泽克激烈论战的主题,刘老师说齐泽克把中国革命诗学化,把血与火的历史事件变成了一种文本解读的方法。
刘康:其实当时我用的诗学化(poeticization)这个词,现在看来还觉得太文雅了一点。实际上齐泽克就是把它摇滚化、好莱坞化,他是把中国革命变成一个摇滚乐或好莱坞电影里的镜像。
刘欣:这正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些学者是怎样在学科里获得成功的呢?不管是对激进理论进行讨论,甚至是将它放在毕业论文答辩、发表文章和获取课题项目的过程中,激进理论本身的激进性在各种学科的学科化过程中,被大量溶解稀释,成为一个纯粹的“知识”。这和刘老师您说的美国学科化、文本化的套路如出一辙。
刘康:而且这种溶解是很流行化、明星化的。
刘欣:甚至成为娱乐化、游戏化、小资化、文青化的理论。所以我们现在都喜欢韩炳哲,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米兰·昆德拉。
刘康:对,他俩确实有点相像。今天的捷克人,为什么推崇的是卡夫卡、哈维尔?捷克人眼中的米兰·昆德拉就是一个小丑,即便他在中国那么火。捷克人觉得,战胜权威的精神力量来自卡夫卡,他说这个世界极端的荒谬,我们必须以荒谬对荒谬;而哈维尔就用勇气战胜强权,是一个真正的斗士。捷克人其实瞧不起昆德拉,觉得他很油滑,将反抗专制强权的主题,变脸为色情游戏的“媚俗”。
刘欣:跟刘老师访学的时候,我说我对这些激进理论的东西还挺熟悉的,这方面的资料我读得特别多。刘老师问我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我自我反思,我看中的好像就是这种文青气质。激进理论为什么吸引我,不是它们有多“激进”,而是它很时尚、很小资。就像我们今天对本雅明的持续性狂热,都是被他身上忧郁的文人气质所吸引。忧郁是一种优雅的、波希米亚(bohemian)式浪漫的、自由的、流浪的气质,正是这些诗化的、审美化的东西吸引着我们,而不是理论的内容、深度或者“真理性”,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了。
刘康:刘欣讲得太好了,每一句话都讲到点子上了。1933 年,瞿秋白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时,就批判“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流浪人知识青年”。[2]三年后(1936)瞿秋白被捕,在就义之前写了《多余的话》,再度反省自我身上体现的“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3]心态。看来,这种心态延绵不绝啊。
时间性和“ 当代化”:激进理论的另一种可能
单小曦:关于激进理论,我的理解和两位老师略有差异。刘欣用了一个词“山寨”,我觉得挺好的,有游戏性、模仿性,然后表现了戏剧化,或者说是“玩”。而且刘欣的理解,我也是认可的。激进理论到中国后已经不激进了,已经被解构了,最后形成的效果,就是这一批年轻学人获得了好处,比如申报项目和发论文。这些年轻人打了一个信息差或者说玩了一套策略,利用这样的激进思维和激进的做法,触碰到当代社会的某个点,而这恰恰是某些人想看到的东西。我认为,中国的这些年轻人“玩”的所谓激进,从学术上来说,我不像刘欣那样肯定,我认为在理论上可能走不了多远。也许,激进理论不应该全属于左派理论,特别是西方似的左派理论,它进入中国后可能已经变形了。今天我们谈了中国化、美国化,其实按这种说法,还应当有世界化、全球化。
刘康:好像确有一个世界化的说法。
单小曦:现在就连全球化都不太有人提起,好像是已经过时了,现在有人谈的是逆全球化问题。其实我认为,相对于中国化、美国化、世界化、全球化等说法,今天更应该谈“当代化”。前面那些“化”都是从空间角度说的,当代化则是从时间角度切入的,是以时间范畴覆盖了空间范畴,强调的是时间维度。
刘欣:那这个当代化实际上不还是西方现代性吗?
单小曦:现代性很复杂。今天我们说的现代性常常就是指美国性,后现代性和现代性还是来自于西方。
刘康:所以你认为还有一种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
单小曦:以前人们在谈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时,常常不是立足于西方文论,就是重返中国古代,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今天我们谈论的美国化、中国化,实际上也暗含着这种思维模式,而当代化的说法一定程度上也许能克服这种思维。比如在谈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问题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既不能从西方出发,也不能重返中国古代,而应该立足于100 多年来的五四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就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古代的,而是100 年来中西交融后的,这就是当代化的结果。它不是美国式的现代性,也不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还魂,它已经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同样,回到今天或者说当代看,我们面临的文化现实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数字文化时代,我们对世界或者说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了。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我们可以按照口传文化、书写印刷文化和数字文化对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做出划分。数字文化就是我们面对的当代文化,也就是当代化的产物。
刘康:那也就是AI 化、人工智能化。
单小曦:AI 是后来才出现的。数字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以计算机的发明为开端,第二阶段以互联网的发明为标志,第三阶段就是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
刘康:对,现在已经到了第三阶段。
单小曦: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讨论的话,所谓的激进理论就不再只是局限于非常狭隘的社会学、批判理论范畴。我所理解的激进理论,就是在解释世界时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和保守的、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最看重的是不同于人文主义的那些理论,比如新物质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后人类理论、物导向存在论、媒介存在论等,这些理论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完全不同于上面所说的那些社会学的激进理论,或许,它们才是更为激进的激进理论。比如唐娜·哈拉维提出的人类纪、资本纪和克苏鲁纪的“三纪”理论,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激进解释,还有库兹韦尔的文明六大阶段说,赫拉利的原始、文明、超人说,等等。
刘康:赫拉利对AI 的观感很不好。他觉得AI 统治了人类。
单小曦:我的意思是,理论是用来解释世界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似乎这里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对立的。其实,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都是一种实践,解释世界的同时也许就在改造世界。而在解释世界问题上,今天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的那些解释,都可能是一种激进理论。
刘康:所以,理论本身就是实践,对吧?
单小曦:理论解释就是实践。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世界,各种理论可以共存,没有必要你死我活。
刘康: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改造了世界吗?
单小曦:对,我们今天解释完世界之后,世界就已经变了。比如我们现在从数字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世界和之前从传统角度去解释的世界就不一样了,这个过程也就是对世界的改造。所以我们从这个问题出发,激进理论里面必然还包括这样的一个分支,它不完全是上面谈的社会学的,还可能是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
刘康:是社会学里时间的历史的解释,对吧?
单小曦:对,都会有的。形而上的,历史的,形而下的,还可能是数字的,AI 的。之前刘欣说了很多韩炳哲,其实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中国也火过一阵子,现在也有一部分人还是在研究他。中国人是怎么发现赫拉利的?他们为什么能火起来?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些理论中,有些理论反对在人与自然之间划出界线,认为不应说人类天然就是人,其他万物就是非人,自然和人之间可能是杂糅的。哈拉维说的克苏鲁纪就是一个杂糅的世界,这种杂糅不仅是打破了任何物的界限,还包括现在、过去、未来在时间上的杂糅。
刘康:赫拉利最近一直在与 AI 对抗。AI 领域的大佬之间一直在激烈争论,前段时间争论的焦点是ChatGPT 对人类的利与弊。赫拉利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某一天AI 拥有了智慧,它可以做出决策,发明了自己的语言,那人类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赫拉利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因为有语言,有讲故事的能力,有独立的思考的能力,有使用符号的能力。如果这些能力被AI 夺去了,那么原本是人创造出AI,或许哪一天人就被AI 创造了。赫拉利等人吵得翻天覆地,有些人站在他一边,有些人不站在他一边。
单小曦:这些人谈论的东西都可以说是激进理论。
刘康:赫拉利的确有些激进,他在牛津大学读的博士,读了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理论比较了解。他有点像韩炳哲,也是一个畅销作者(popular writer),对于他的观点也不需要想得太深。
单小曦:他是面向大众写作的,但是他的有些观点还是非常激进的。
刘康:像是中国式rock style。激进理论现在变得非常时尚和摇滚,但与崔健“一无所有”式的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摇滚已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单小曦: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恰恰需要这种游戏的人。
刘康:观点发表出来时,就得“今隐其名”,因为是“某君昆仲”。[4]但事情还是要讲的,《狂人日记》终究还是要登出来。为什么?因为反思“情绪骚动”[或曰“情动”(affect)]与理性实践的失衡,乃知识人的职责所在。从斯宾诺莎到德勒兹,他们关于affect 发表了许多议论,但多半语焉不详。大意是说affect 更多是肉体欲望的,是前思维、前理性和前主体的,或者说是更具动物本能的情感和情绪反应。这个词近年来在中国也大热,被莫名其妙地译成“情动”。这个中译词,说的是动态的情绪?还是运动中的情感和情欲?难道说,还有不动的、静止的情绪和情感吗?译词、造词的话术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题内之义,所以我姑且称之为“情绪骚动”,针对的是当下各类激进文艺理论的变脸,以及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国)的变脸背后,究竟有哪些情绪骚动。
参考文献:
[1]韩炳哲. 山寨:中国式解构[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
[2]瞿秋白,编. 鲁迅杂感选集[M]. 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0.
[3]瞿秋白. 多余的话[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14.
[4]鲁迅. 朝花夕拾[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174.
(责任编辑: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