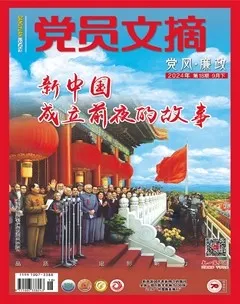城管新“局”:求解“看得见管不着”

江西南昌的城市管理执法体制,再一次迎来变革。
2024年7月18日,南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更名为南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指挥中心,不再有执法职责。南昌市城管局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执法职责划归市生态环境局,其他的执法权下放至各区。
撤销市级机构、充实区县执法力量,是2024年以来各地改革城管执法体制的通行做法。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沈荣华观察,本轮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的趋势是“执法重心和管理资源的下移”。
尽管是机构改革的要求,但各地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的差异性较大,背后也存在着全国性城市管理立法缺失的问题。
组建5年后被撤销
公开报道中,2024年打响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第一枪”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于6月10日撤销了市一级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人员下沉到新成立的区局。
其实,早在5年前,北海就进行过一次较大力度的改革。
2019年3月,北海将住建、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11个领域的行政执法职责整合,组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
同时,北海市城市管理局更名为市政管理局,主要负责城市园林绿化、城市道路、排水设施等方面的规划、建设、监督工作,而原北海市城管局的执法职责合并至综合行政执法局。
沈荣华注意到,北海市在2019年组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把大部分执法职责都整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按照中央2018年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推动整合同一领域或相近领域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设置”要求推进的。
那么,在成立5年之后,该局为何又被撤销?
北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相关人员表示,此次启动机构改革的背景仍然是中央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机构改革要求。
2024年4月9日,北海市委书记蔡锦军在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议上说,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面,“要实行以县级执法为主的体制”。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指出,继续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设区市与市辖区原则上只设一个行政执法层级,县(市、区、旗)一般实行“局队合一”体制,乡镇(街道)逐步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的改革原则和要求。
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王毅分析,执法力量下沉主要是为了解决“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以部分发生在街道的行政违法行为为例,在街道无权管辖的情况下必须上报市级城管执法局等单位,再交由市级城管执法单位行使执法职责,而此时违法行为的结果已然产生。
下放程度、方式不同
尽管秉持着“一支队伍管执法”的相同目标,但各地下放城管行政执法权的改革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2010年,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派驻市辖区的机构移交属地管理;2011年,南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成立以后,执法职责划分又经过多轮改革;2015年,南昌将占道餐点等部分具有属地特殊性的事项执法权下放给各城区;2018年,南昌根据各属地的执法权承接情况又进一步实行整体性下放。
南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指挥中心综合股负责人虞超伟表示,执法职责的划分难以一步到位,部分涉及专业性执法,部分涉及和老百姓打交道,这都需要市级和区级、市级内部各部门间的多方协调。
改革前,南昌市级和各城区都拥有行政执法权。在虞超伟看来,2024年南昌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此次市级的执法权下放给各城区行使后,市、区两级执法只保留一级,已经下放的不再收回”。
除北海、南昌等地直接撤销市级城管执法队伍、下放执法职责外,也有不少地区视情况下放部分执法权,仍保留市级城管执法队伍。
在浙江杭州的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市级执法队伍与下辖各区级一并划入当地执法队伍网络,共同处理杭州市执法事项。
此外,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在城市行政执法权下放至区县、乡镇综合执法局后,也保留了市级执法队伍,负责占道经营、生态治理等多项执法工作。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各地都在探索试点不同的改革模式,这取决于各地实际情况和改革力度,“全部下放是理想形态,但是不少地区达不到要求,改革阻力较大,存在行政执法权不完全下放的问题”。
属地管理
执法权下放之后,各地原有的行政执法格局也随之改变。共同的趋势是,原有的垂直管理体系基本解体,执法机构的属地管理色彩更加鲜明。
南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指挥中心挂牌成立后,除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执法职能划归市生态环境局外,原市城管执法局其他的执法权下放至各主城区和高新区、经开区、湾里管理局。
南昌市高新区城管执法局相关人员说,由于高新区、经开区并未设人民政府,其城管执法局本来就是市局的派出机构,“所有执法权均来自南昌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委托,既有执法权限基本是完整的,因此,此次改革前后高新区的权责范围没有变化”。
南昌市西湖区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公房违建、燃气、水务监管等职责,在改革之前属于市级执法事项,“我们城区如果排查到相关线索,要移交给市里,而改革后就完全由我们属地负责”。
执法职责划归各城区后,原南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的行政执法权被完全分解,而新挂牌成立的南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指挥中心又将承担什么职责?
虞超伟表示,综合指挥中心目前的主要工作包括城管执法队伍的顶层架构和设计、规章制度的出台,以及日常协助城管执法局开展监督、考核、调度等相关工作。
在广西北海,市局垂直管理派出机构的执法体系也完全解体。新的执法格局是,市级层面的执法工作回归各个职能部门,区一级各职能部门仍然没有执法权,隶属于区政府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履行执法职责。
那么,北海市为什么没有选择在保留市局的前提下在区县设置垂直管理的分局?沈荣华分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保留市局再设置分局,不符合既要“减少层级”又要“执法力量下沉”的改革精神。
缺乏全国视野
王毅发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地改革成效仍与预期有差距。他认为,各地执法权下放方案主要由各地党委、政府制定,缺乏基于全国视野的顶层设计是改革未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
马亮也认为,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体化的行政执法权下放方案,“当前五花八门的行政执法,恰恰说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
不过,建立全国性的制度规范并非易事。
2014年3月,王毅带领团队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专家建议稿)。2018年3月,住建部曾召开城市管理立法研讨会,听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立项报告和框架的意见。但这项工作未能取得太大进展。
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城市管理是否有必要进行全国性立法,认识并不统一。王毅回忆,当初他向人大提交的立法议案被搁置的原因是,有人认为城市管理是地方政府事务,国家没必要作具体规定。支持立法者则认为,城市管理局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必须全国统一规定,明确城市管理的内容、管什么、谁来管、怎么管,以及提供法治保障、经费和物质保障等。
2023年12月8日,住建部在江苏扬州召开了一次课题评审会。此前,住建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委托扬州大学承担了《城市管理立法研究》,课题成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送审稿)。
王毅回忆,在评审会上,住建部城市管理监督局人员和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苏、陕西、河北等省市的评审专家,对课题成果均有积极评价。
目前,南昌、北海等地虽已明确行政执法权下放行动,但工作仍在交接中,具体下放的执法事项清单仍未制定完成,各项执法权下放到区县、街道还是乡镇也尚未明确。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