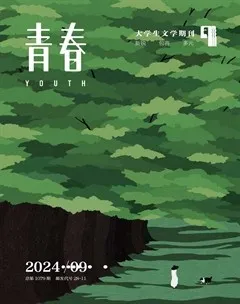南厝东寨
古厝
七月的时候,外边的热气散在半空里,抬头看过去是一片片摇晃的空气。我们的老屋子正躲在古厝阴凉的那一边,后边另起的一处小砖楼也用阴影遮蔽着我们,风从古厝厅堂上的天窗落下,落在那个干枯的雨池里,里面的砖缝上长满了黄绿色的苔和枯卷的蕨。
风从雨池里徘徊出来,经过短短的过廊,便一头闯进了我们不设防的老屋。年迈的祖父躺在他的竹躺椅上,敞着胸膛,感受这股风,轻轻地发出一声满意的鼻音。他扇动起他的旧蒲扇,便又是一阵带着草木味道的小风,连他身下的竹躺椅都开始微微摇动起来。
这个季节的午后,即便是一生在田地上洒汗的祖父也不敢再轻举妄动。村子里彻彻底底地安静,村人们都和祖父一样躺在属于他们的竹躺椅上,午时下过蛋的母鸡也收拢起喉咙,在鸡舍里难得地安静下来。
七月的天是蓝蓝的,太阳是那样高,把它一切的热焰都投在大地上。就算是一到这个季节就疯长的鬼针草也扛不住这样的热气,早早低下了头,在路边一丛一丛地蔫了下来,唯有它们枝头上的小白花还拼命地开着。
几个皮肤黝黑的娃子站立在古厝大门的石门坎上,他们的背后是古厝的厅堂,厅堂上的神龛里立着一排排的灵牌,几根未灭的香烛生出一缕缕白烟,在厅堂里慢慢飘散。黑娃子们看着外面的天,实在不敢出去,便又退回到厅堂里,把那雨池围了起来。
一个黑娃子站在雨池的上头,那儿立了一个抽水泵,雨池底下还是一个黑娃子,他拿了几块红砖堵在雨池的排水口。上面的那个开始一下下按压着水泵,水泵里传来几声如同干呕的声响后,便冒出了清凉的水来。靠得近的伸出手,接了一捧清凉的水后,打在了自己的脸上,水花四溅,几注水流滑进了衣缝,在胸膛上流过,凉得打了一个哆嗦。
其余的黑娃子看他打了哆嗦,便指着他笑了起来。那个按水泵的更加卖力了,水泵一下下地把凉水从地下抽上来。凉水像激流一样在水泵里激荡,哗啦啦的水声,把那些热气都赶去了,水花从水泵里激出,打在一个黑娃子身上,打在其余所有黑娃子的身上。
雨池里慢慢地积攒起了一片小水洼,砖缝间即将枯死的苔和蕨又得到了水的滋润,努力吸收着那些清凉的水,不眨眼,苔便一下就从黄绿色变成了青青翠翠的样子。可黑娃子们的目的可不在于此,凉水从苔上渗透进那些稍大的砖缝里,里面藏着一个青绿的小东西,这小东西被潮湿的水汽唤醒,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叫声。
黑娃子们跳进雨池,极有经验地探索着那些砖缝,拨开细小的蕨。那青绿的小东西被它家门外的巨人惊吓到,往深处后退了几步。黑娃子们找来一根细长的树枝,把那青绿的小东西逼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在缝隙里躲藏热气的小青蛙。
它跳出了缝隙,落在那小水洼里,小小的身躯浮在水面上。然后它收拢起后腿,猛地一蹬,便在水面快速地飞了出去,在小水洼上带起了一阵阵涟漪。黑娃子们都欣喜地看着那小青蛙,看它游到岸边,坐立在那,下颌处收缩起伏着,又看它鼓起了气囊,发出一声响亮的鸣叫。
它的身躯那么小,叫声却那么大,回荡在厅堂里,一声接着一声,就像雨后的青蛙的叫声那样有力。可一看它身处在那小水洼里,对它而言如同拥有着一整座湖泊,它独享着,确实应该要比那些雨后的青蛙还要快乐。
那小青蛙还在鸣叫着,祖父却从他的竹躺椅上起了身,竹躺椅在屋子里空空摇晃,祖父一直走到厅堂里。黑娃子们还没发现厅堂里多了个人,祖父站在稍远处看见那雨池里的蛙,便知道扰了他闲睡的蛙是这几个黑娃子找出来的。他走到其中一个黑娃子身后,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那黑娃子一回头看见了他的祖父,僵笑了起来。

祖父没有和他们多言语,看了下外面渐落的黄昏,把他们赶出了古厝,让他们自个儿到晒场上玩去。青蛙的叫声开始稀疏起来,祖父也没有理会那池里的蛙,只跨过了雨池,朝着神龛走去。
神龛下的香炉里,香灰叠满,只剩三根红色的小棍。祖父取出四根香点燃,火柴划在擦纸上,发出黄色的光。厅堂里又升起了一缕缕的白烟,祖父把剩下的那根插在天窗下的吊炉上,那缕烟便直直地升向天空。半小时后,祖父的老屋里、烟囱里,也冒出了烟,直直地升向了天空。
山寨
闽东的大山里,幺婆婆站在寨子前。那里是一小片平地。在这个初秋的淡金色季节,小平地上被寨民们用木头桩子立起了一排排架子。幺婆婆弯腰从竹筐里拿出一挂挂打结的玉米,分岔着披在那木架子上。玉米棒上一粒粒不尽是金黄,紫色、淡红色、浅白色掺杂在玉米棒上。幺婆婆觉得这样的玉米才算好吃,微微带点甜,也没有那么糯,不然沾在她的假牙上,还得摘下来费力刷洗。
这个寨子从她小时就在了。那时寨子还没这么大,后来几代人下来,寨子里嫁娶生娃,人多起来了,寨子自然就跟着大了起来,从山脚一连建到了小山腰。幺婆婆提着空竹筐从寨子下面一路向上走去,一栋栋木屋在她的眼里交错出现,一条小土路在她脚下延伸着。
走到略高的地方,有一处两层的木屋,连着屋前的那一方小水池子,占地颇大。这一处木屋是幺婆婆和她的丈夫在几十年前建起的,木屋依旧如几十年前那样矗立在这山上,只是细看那屋檐和木脊已经发褐,岁月的霉斑每一年都在木窗上生长,然后又退去。
纤细的电线钉在木屋上,打开发黄的钨丝灯,木屋在灯光里显出老态。幺婆婆的丈夫一去也有十余年,他们的孩子一朝飞出了大山,多年后孩子又把她的孩子交给了她,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拉着她醒来。
幺婆婆站在木屋前,看着黄昏渐落的山间。一条小溪从另一边的山口处流出,经过寨子脚下,远远地弯弯曲曲越过多少座山。
初秋的溪水泛着一点凉,几个身影却是不怕,在溪中戏水。他们站在凸起的河石上,其中一个手上提着一个鱼篓,里面还有东西摆动,其余的此时都用羡慕的余光瞄着那鱼篓。
那提鱼篓的却发现了,一把把那鱼篓提过头顶,用力拍了拍,惊得那鱼儿奋力摆动,大声笑着开始说道:“都别藏着了!你们眼睛都快穿进鱼篓里啦!”那提鱼篓的又拍了拍胸口。
旁边的一个带着不服气说道:“你只是运气好,那鱼刚好在石洞里出不去,才让你捡了便宜!”
“哼!”那提鱼篓的说道,“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胆小吗!我早和你们说了那水下洞里有鱼,是你们自己不敢下去,才被我抓了。”
旁边的那个被这一说,一时就哑了嘴巴不再说话,撇撇嘴认了下来。
几个人又跳入溪中,溅起的水花打在河石上,让四周的小鱼惊逃。过会儿,那提鱼篓的走上岸来,站在岸边开始打量着这山里的一切,他的眼睛扫过溪水里的卵石和水草,几条淡水石斑飞速穿过了河石间的缝隙,上游漂下了几片竹叶。这些大山里,最不缺的就是漫山的竹林,在风里不停摇曳。还有那梯田样的茶山一座又一座,和竹海相映着。
等天气再冷上一些的时候,山上那竹林里便长出了最早的冬笋。幺婆婆便会带着他上山,他扛着锄头,幺婆婆提着袋子,从屋后的那条小路走进去。
幺婆婆说她从山里出生到现在几十年了,那时候寨子和外面相连的只有一条小土路,跟着那溪水蜿蜒向远方。寨子像是天生地养的一般,立在这林海山间。她没有想过有人会直接离开,离开得比那些溪水还要快,顺流而下,打起一点浪头后就没有再回头。她常常站立在屋前,看着黄昏落过山头,茶山又发出新芽,竹林一片片结出果实,她用山泉煮起数年的炊烟。
很长时间以后,她的木屋多出了一个人,拍打着木门,叫着她婆婆。她牵起他的手,他说她的手怎么那么干枯,又用脸贴着她的手背。于是土地开始裂开,冒出稚嫩的笋尖,青青绿绿的,藏在漫山的竹林里,被温暖的人发现。
幺婆婆觉得老天就是这样无情又多情,又要下雨又要人间布满阳光,直叫人在里面彷徨得出不来。她在屋子的老灶里生起了火,冒出一叠叠的烟雾,火星也溅射出来几颗,幺婆婆的脸变得通红,火光在她的脸上跳跃。靠窗的木橱台上两个牙杯依靠在一起,从前是两个,现在也是两个。幺婆婆在锅里下了油,油开始升温,刚倒下的青菜热出一阵白气,还有一种香味充满整个屋子,一切都被禁锢在这几十年的屋子里。
在溪水旁,那提鱼篓的刚穿上鞋子,耳边就听到了一阵从山腰那传来的声音。
“树小子——”幺婆婆站在那屋前终于叫唤起了她的孙子。
这一声从山腰那传来,在山间回荡了几回,最后高高地传入天空中。树小子抬头看着那山腰,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人影。他张开手用力挥了挥,大声地回应着那个人影。
天边开始出现一朵云,没有人知道山的外边有什么,让那人把他送入山后又离去。幺婆婆说她像是棵竹子般,扎根在这大山里,养育出一根竹鞭后,那竹鞭便直直地探索到外面,长成了另一棵竹。所幸这里从来不会下雪,她还能立在这几年,可以盼到竹笋长大。
在那山脚下,树小子提起鱼篓在土路上跑动起来,身后的几人也跟着跑动起来,土路上扬起一阵尘土。追逐声在寨子里响起,每过一段路后就小上一点,幺婆婆在屋子里听着动静,把瓷碗摆上方桌。土灶冒着余烟,外面的黄昏已经消失,树小子也在这时候出现在屋子外,扬着一张笑着的脸,捧起胸前的鱼篓。一点水渍落下,鱼儿在鱼篓摇摆起来,幺婆婆也看着他笑了起来。
责任编辑 王娜
作者简介
陈金斌,2003年生,福建仙游人,仰恩大学2022级汉语言文学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