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 笼
初冬的草原上死了不少牲畜,有牧人饲养的牛羊,有旅人的马匹,甚至还有不少独行的孤狼。无论几时,只要你站在高山之上向草原眺望,总能看见一些冒着热气的动物尸体被秃鹫或鹰啃食着。总有些牧民男孩三五成群,拿杆子捅着那些尸体,揪下羊毛,割下牛角,拔掉狼牙。唯有鹰,没有人在草原上见过鹰的尸体,一个也没有。
艾羝从床上苏醒,从老而破旧的床头柜前站起来。当他睁开眼的一刻,他的世界顿时就无比明亮而且充满希望了。他亲吻了放在柜子上母亲的照片,在盥洗池旁捧起清水洗了把脸后,就挺着他那像竹竿一样的高大身躯,拉开蒙古包的帘布,到旁边的饲舍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的饲舍与常人的不同。他养鹰。准确来说是帮人养鹰,每天他都要去看那些他所豢养的鹰隼们,照料它们,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十二月的风在无垠的草尖上呼啸,发出刺耳的嚎叫,是那样的无所畏惧,将每一个牧民的脸冻得通红,仿佛要把他们的耳朵冻掉。艾羝能够感觉到风的那种阴森与冰冷,每每掠过他的时候,仿佛灵魂在耳边轻语:“救救我吧,艾羝,把我从这样的生活里救赎出去。”他低头看这片杂草都有些稀疏的土地。这还是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吗?但是无所谓了,等他把这一笼笼鹰隼完璧归赵,就可以拿着钱买去其他城市生活的车票。艾羝自认为是个与众不同且高傲的人,他的父亲抛弃了这里的生活,同时也抛弃了他。离开前,艾羝的父亲告诉他,只有牛羊才一起行动,雄鹰永远都是单独翱翔的。他想做雄鹰,要远离这个只有膻味和奶味的地方,远离这种只有牛羊做伴的孤独生活。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要去大城市读书,学习知识。他渴望一切新鲜事物。他渴望自由。
艾羝的鹰舍中,每只鹰都被关在鹰笼里。鹰笼的设计很精妙,分为三层,最内层是简单的麻雀笼,木制,方便人来喂养生肉以及让鹰来取水,维持基本的生存;中层是其他鹰的羽毛,其一帮鹰保暖,其二用来“麻痹”鹰,让它不再孤单;最外层是最难突破的一层,用铁制成,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只留一个小窗让鹰呼吸与探出头来。如果有哪只鹰想要挣脱束缚,它即使咬断了一层的牢笼,但也绝对不可能突破所有阻碍飞出去。所以艾羝每天都可以放心地睡个好觉。
艾羝到了鹰舍里,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又抖搂了一遍,然后用惺忪的睡眼重复着一年来每天一样的操作:数鹰,数二十七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像往常一样一只一只地数着那些用利刃般的眼注视着自己的鹰隼们。
二十五。
少了两只。
艾羝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但马上恢复镇定,又一次从上往下按列来数。二十五只。从左到右按排来算,还是二十五只。
有两只鹰丢了。
艾羝站在鹰笼旁,直直地向里面看。鹰笼里狭窄,拥挤。粪便的臭味以及生肉的血腥味不停地冲击着艾羝的鼻腔,鼻子根部的红与苍白的鼻尖形成鲜明对比。眼睑周围感觉到一种异常的干燥,头和身子似乎像醉汉一样不受控制,十分沉重。他被迫张开嘴呼吸,急促,脸色苍白。他定下神来看究竟少了哪两只。其中一只是一只最小的雪鸮,通体雪白,黑喙,极美,也最稀少,价格昂贵;另一只倒并不是很贵,只是一只常见的普通鵟。
他踹醒了旁边懒洋洋趴着睡觉的牧羊犬。狗用温顺的眼神看着他,他却用凶狠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狗。随后他查看鹰舍内是否有什么蛛丝马迹,能让他知道鹰究竟是怎样从这里消失的。搜寻了半天,始终无果。
一切都结束了。艾羝想。之前做的一切难道都是徒劳吗?这些鹰他是跟雇主签过合同的,少了两只,不但薪水要打水漂,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如果买两只混进去呢?不可能的,这些鹰每一只都有编号,在领走它们之前早就拍过一次照片了,更何况那只雪鸮根本找不出第二只。他把这些鹰养得比自己的父母还要好,每天带给它们最好的鲜肉,它们啄到他的手时都不驱赶,所以雇主才会放心把这么多鹰隼交给他,给他那么丰厚的报酬。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他在艰苦困难中跌跌撞撞,离他的振翅就差那么一小步。他还这么年轻,难道又要为别人养一辈子的鹰?究竟是谁,是谁偷走了我的鹰,是谁偷走了我的未来?
他那高挺的鼻翼开始缓缓收紧,咄咄逼人的目光四处张望,握紧的拳头仿佛要把指甲嵌入掌心。他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无论能否找得到鹰,无论用什么方法。
他给仅剩的二十五只鹰喂好了鲜肉,再次检查每一个笼子,锁好;又回到屋内给牧羊犬喂了两块羊内脏,让狗吃了个痛快。他抚摸着狗头又絮絮叨叨地嘱咐了几句,就踏上了寻鹰之路。
鹰丢了,自然要向雇主汇报,他先要去的,是他的雇主买合买提家。
艾羝的鹰舍距离买合买提家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大概几公里。但毫无疑问,这条路是漫长的。抬眼望去,无数雄鹰傲然翱翔在这片旷野上。离草原是那么近,又那么远。这里的一阵风就可以将无数洁白的云朵吹向别处,露出那如湖水一般湛蓝无比的天空。空中无数只鹰眼俯瞰着无法起飞的渺小的艾羝,与草原上的青草和牛羊融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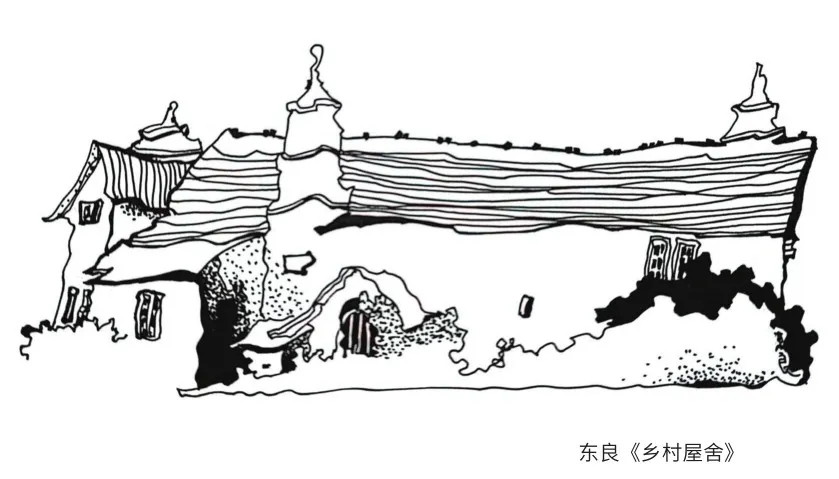
买合买提的家并非传统的蒙古包,而是白房子,像别墅一样的白房子。他与艾羝讲过,他不喜欢住在草原,他的归属永远和新时代的上流社会一致,他觉得自己本就是上流社会的人。这是艾羝第二次来到这里,艾羝不是个熟悉这种地方的人,对着门上的指纹锁摆弄了半天,直到指纹锁上沾满指纹后报警发出滴滴的声响方才作罢。屋内的人闻声而动,开门的是一个打扮秀丽、穿着潮流的女人。与面颊绯红的蒙古女人们不同,她脸上的粉遮住了大部分的红晕,又有着令人艳羡的高鼻梁,若是放在平原城市,定是吸引众人的焦点。
“Sainu①,您是?”女人倚着门边询问艾羝。
“Sainu,我叫艾羝,是和买合买提先生合作的。鹰的事有一些问题,我要向他汇报。”艾羝说。
女人不再说话,对艾羝报以一个微笑,做了个手势表示稍等,弯腰,缓缓将门关上,门后传来极其轻微噔噔哒哒上楼梯的声音。没过一会儿,女人再次下来,依然是半弯着腰,微笑着说:“我丈夫说邀请您上去聊。”她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艾羝也弯着腰进了屋子,等艾羝进门后,女人就轻轻把门关上了。
买合买提正在办公室里用手机刷着财务报表,一边往下翻,一边嘴角不住上扬。见到艾羝进来,便招呼着他快到自己旁边,一起来看。艾羝完全无心屏幕上的那些表格和数字,丢失的两只鹰仿佛变成了一块果核,哽在他的嗓子里面,快要把他憋死了。他攥紧拳头,用一种极其质朴的方式掩饰着自己的恐慌,终于在咽下两大口口水后,对着买合买提耳边轻声说了一句:“鹰丢了。”
买合买提的笑容凝固在了一瞬间,眼神立刻变得尖厉。他推了艾羝一把,顺势将自己的座椅向后移动保持距离,但似乎早有准备一样和艾羝说了一大串话:“什么?丢了?丢了几只?你放宽心就好,一只普通的鹰也就是你小一年薪水的事儿,咱们是签过合同的,这就没办法付你工钱了,要不你再给我养几个月的鹰?丢鹰的事哥就不计较了,我知道你着急去外面闯荡,但你相信哥,外面没啥好的,再过几个月,过几个月再去。你还年轻,到时候哥再给你买车票。”他快速地说完,完全没给艾羝一点插话的机会,随后急促地喝了一口水,用脚勾开抽屉,拿出一份打印好的合同,扔在桌子上。
“鹰虽然很贵,但是不要你赔钱了,我知道你辛苦,尽心竭力都是为了养好鹰。签字吧,Bayal②。”
艾羝依旧愣在原地,但手被买合买提紧紧握住。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他那双大手,上面无数的蓝宝石、绿宝石闪烁着璀璨而夺目的光辉。艾羝只是愣愣地说:“丢了两只。”
买合买提几乎是在霎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的,他对艾羝的这个回答感到很意外:“什么?两只?还丢了什么鹰?”艾羝听到买合买提说出“还”的时候感到很诧异,但是来不及思考,现在就必须回答买合买提的问题。“两只,一只普通鵟,还有……还有一只雪鸮。”艾羝从喉咙里硬生生吐出了那两个字。
“雪鸮,雪鸮!”买合买提的眼睛几乎凸出来大半,他拿起了桌子上拟好的合同又看了看,重重地砸在桌上,“怎么会丢两只?而且还是雪鸮?你知不知道那只雪鸮有多贵?你个混蛋,还买车票,下辈子再买吧。”
“我会想办法的。”艾羝很倔,他对买合买提说。
“那好,那好,既然如此,我拟定的合同是你丢一只鹰的情况,雪鸮你自己给我找回来,不然的话,你就在这给我养半辈子鹰吧。”买合买提又重新用他的大手抓起合同,把合同拿给艾羝签字。艾羝看也没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艾羝是直着腰离开买合买提的办公室的。买合买提一直看他不爽,但他还是直着腰出来了,买合买提的妻子以一副端庄的姿态送走艾羝。关上门后艾羝在门前站了许久,始终低着头,他依稀听见了门内买合买提的奸笑声、夫妻二人的打趣声、女子的娇嗔声,就连排风口都是数钞机哗啦哗啦的响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愤怒的火苗,但是转瞬就熄灭了,他叹着气,用手指不停按压着自己的眼睛,嘴唇上的死皮不停被上牙撕咬着。
他拨通了电话,打给女友古丽。她和大多数沉浸在恋爱中的少女一样,经常和他说如果不开心,一定要找她倾诉。艾羝平时是不会把生活上的不顺传递给自己的爱人的,但现在他实在是太苦闷了。
“来找我吧,不要让你爸爸知道,偷偷出来,来我家。”艾羝说。
电话的那一边传来了细语:“好,晚上见。”
艾羝这才轻舒了一口气。
夜深人静,回到家的艾羝失眠了。今时不同往日,以前的生活十分简单且规律,养鹰,恋爱,吃饭睡觉,攒钱。丢鹰的事儿打破了他的一切计划。吹过青草穿过蒙古包帘帐的风声平时是他悦耳的助眠曲,如今竟成了恐怖的呼号。他感到无比焦躁不安,心想着与其自己躺在床上难受,不如在蒙古包前等着古丽。一刻见不到她,艾羝就心慌一刻。他打开床头柜拿出手电筒,披上厚实的棉服,进入了黑暗。他一个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远远地看着外面任何一点能看得到的光点,希望它们由远及近,最后投入他的怀抱。
如他所愿,终于有一点亮光飞奔着投入了他的怀抱,寒风中的两颗心紧紧贴合在了一起。此刻的艾羝是无比欢愉的,那股草原女孩所独有的香味让他沉醉,与只有相爱之人才能懂得的那种气味交织在一起,古丽成了他灰暗世界里的一道光。艾羝激动地把古丽抱了起来,用公主抱的方式把她抱到了自己的床上,轻轻吻了一下后,拉过旁边的羊皮椅坐了下来。
古丽呼出了几口冷气后缓了缓呼吸,用一种小女孩特有的娇气劲儿问艾羝:“有什么不开心的都有我陪着你,你说吧,我在听。”艾羝把大致的事情讲给了古丽,古丽一开始还饶有兴趣,听到艾羝会一直留在草原时甚至有些窃喜,但直到听到买合买提不给工资还要再让艾羝白干半年的时候,她的神情就彻底变了。她开始跷起二郎腿,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眉头紧锁,撇起嘴来。但这一切艾羝都没注意到,他看着母亲的照片和床头柜出神,直到古丽叫他的名字,他才回过神来。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艾羝,你想好了没有?你以后怎么娶我?说好的生活呢?和买合买提家一样的白房子呢?”古丽说。
“我没有办法,那只普通鵟我可以赔,至于雪鸮,我也没有头绪。结婚的话,我想先出去闯闯,你是知道的。”艾羝摸着脑袋,向自己最亲近的人表现出憨憨傻傻的一面。
“去找我阿爸吧,他什么都懂,他一定能有方法找到雪鸮,但是你知道的,如果要是告诉他咱俩的事,按咱们这里的规矩,你就要留在草原娶我了,这样你还能和我阿爸一起养羊,我们一起赚钱。”古丽的脸逐渐起了红晕,害羞地说。
“那我的理想怎么办?如果现在就去见你阿爸,那不就是坏了规矩吗?我就只能娶你,之后在草原上和你的家人住在一起,在草原上和羊打一辈子交道了。你阿爸一定不会放我走的,一定不会!”艾羝气得站了起来,甚至哭了出来。这个强壮而高大的草原汉子流下了不甘的泪水,泪珠挂在他的胡茬还有棉服的绒毛尖尖上。他看着他的爱人,这时才注意到古丽的那副姿态,他感到无比震惊,他几乎不认得她了,那个可爱单纯的古丽,给他带来过无数次希望的古丽,一提到结婚和钱就仿佛换了一个人。
“艾羝,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去给买合买提那个老狐狸打半辈子工,赚到的钱一辈子娶不到老婆,三四十再去大城市;要么去见我阿爸,娶我,留在草原有自己的事业。这都不会选择吗,艾羝?你傻吗?”古丽起身把艾羝的身子重新压到椅子上,顺手给他捏起了肩,将朱唇靠近他的耳边,又轻声说:“我一直期待着你娶我。”艾羝只感觉身子有一股电流经过,耳朵红了,抬头看到女孩脸上的红晕。
次日的清晨,艾羝照顾好鹰就和古丽一起乘车去了她父亲的羊厂。他在路上看到羊厂里的人愁眉苦脸,到处都是羊咩声、磨刀声以及机器轮轴转动的响声。艾羝不喜欢这里的感觉,他又一次闻到了和买合买提家排气管里一样的钞票味道。古丽在车上也一直在给自己的父亲发消息,努力向父亲介绍,艾羝是一个多么能干、多么勤劳并且正直的小伙子。原本老古丽是不同意的,但是听说他给买合买提这只老狐狸养鹰都能养那么久,而且对自己的女儿真心的情况下,才想和艾羝好好见一面。
刚进门的艾羝让老古丽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艾羝被一种难闻的羊膻味覆盖着。老古丽毕竟是老江湖了,看到艾羝的满脸胡茬和乌青的眼袋,就知道一定是遇到了困难。听完艾羝的讲述后,老古丽内心暗自骂买合买提阴险,又佩服艾羝的敢作敢当。看着艾羝憨厚老实的模样,他内心暗暗想着,这个女婿他是认定了。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女婿”,艾羝不经意地应了一声,老古丽当即大笑了起来,紧接着说道:“买合买提就是个老狐狸,想让你给他白干活,依我看的话,那只普通鵟就是他自己偷走的。但是吧,那只雪鸮,可能是真丢了。”
艾羝愣了半晌,然后点了点头,他眼里的那道光逐渐黯淡下去。古丽父女原本期待着艾羝开口说几句话,诸如大骂买合买提又或者大哭一场,可是艾羝没有,他只是杵在那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气氛逐渐降到冰点,还是老古丽继续开口了:“Zalu①,别难受,这笔账我替你去和买合买提算。我也老了,如果你不嫌弃,这批鹰你交还给买合买提后,就来接我的班吧。这羊厂,都是你的。”老古丽并没有说来给自己干活,他对艾羝说的是“接班”,他渴望让艾羝来羊厂工作,毕竟,“准”女婿是不会找老丈人要工资的。
艾羝谢绝了老古丽的好意,告诉他自己还是想出去走走,看看不同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这可惹得老古丽不高兴了。他紧皱着眉头,回过头与女儿对视了两秒,女儿用唇语说着“我管不了,你来”,同时不停地摆手。老古丽也用唇语说“我也不会”,同时对着女儿富含爱意地笑着。但是马上,老古丽就回头,摆出一副犹豫不决的神态,对艾羝说:“那不好意思,先生,我对大城市的外乡人就爱莫能助了,虽然我知道雪鸮在哪儿,但我相信,雪鸮也不会希望自己被外乡人找到的。”
此时此刻的艾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想到自己每个寒风凛冽的晚上都是靠着那一条条关于城市的科技资讯的消息度过的。那简直和科幻小说里描写的一模一样,他想知道VR是什么,磁悬浮列车是什么,为什么几百头牛都拉不动的东西,可以自己飘浮在空中以几百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运行。那才是他想居住的地方和想了解的事物,但现在,无论是给买合买提打工还是给老古丽养羊,梦想都永远破灭了。艾羝又看向自己的爱人,古丽也在微笑着看着自己,时不时还指向老古丽的方向暗示艾羝同意,这样至少还能得到她。
艾羝点了点头。
次日,艾羝和古丽顺便叫上了羊厂的几个伙计,向老古丽讲的地方出发了。那是一处山峰,悬崖峭壁是这里的代名词。离开前,老古丽嘱咐道:“这座山上有不少鹰,如果有鹰的尸体,务必带下来给我,我去找买家。如果有活鹰,就抓回来,再也不放走了。”说这话时他和善而面带微笑。不过艾羝只听到了最后一句“再也不放走了”。
艾羝和古丽嘱咐伙计们在山下等着,把装备穿戴好,开始登山。两个人沿着崖边向上攀登,他们一边爬,艾羝一边吹着平时训鹰时口哨,呼唤那只丢失的鹰。他们呼唤了许久,直到正午时候才终于发现了一只鹰,是尸体,看上去无比年老,死在了半山腰处。这是艾羝和古丽第一次发现鹰的尸体。他们不再吹口哨,而是仔细地端详着那只死鹰。
“这只鹰看来是老死在这里的。”古丽说,“鹰的尸体可真不好找,为什么不死在草原呢,多此一举。”
古丽说这话时站在一旁,眺望着她所生活的草原。艾羝则单膝跪了下来,还是在看鹰,看那早已腐烂的皮与所剩无几的鹰毛,和那因为撞击几近碎裂的鹰喙;还有鹰眼,那和自己一样的眼神,如此熟悉。“他不是老死的。”艾羝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奇怪的颤抖。
古丽从身后把母亲缝制的布包拿出来,二话没说就把死鹰塞了进去。鹰并不小,翅膀残缺不全地裸露在外面。古丽果断扯断了它的双翼,以一种极其粗鲁的方式打包好,又给布包打上了死结。艾羝站在那里,垂着双臂痴痴地看着全过程,古丽两眼放光地对艾羝笑着说:“要不要看看,我们一共能抓多少只死鹰,猜猜能卖多少钱?一定可以买很多的小羊羔,买到小羊羔后我们又能赚好多好多钱。”
“那赚完钱之后呢?”艾羝问。
“给我阿爸阿妈买新房子、新衣裳,然后继续买小羊羔,我们还可以生小艾羝。”古丽说完咧着嘴,露出她那看起来无比清纯美丽的酒窝。
“我以为你不是那种普通的女孩。”艾羝说。
“我当然不普通,我未来的丈夫是有高薪工作的养鹰人。我未来会有很多钱,我会是高贵的草原女人,和买合买提夫人一样。”
艾羝沉默了半晌,对古丽说:“我们接着向上爬吧,还不够高。”古丽在后面跟着他,越爬越高,其他人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他们越向上,周围鹰的尸体就越多,但大多是骨骸,能让古丽看得上眼的极少。古丽看到的尸体越多,就越兴奋,腿脚也越来越轻快,艾羝根本追不上她,只能看着她不断翻拨着每一具鹰骸,找寻对她来说最有价值的;那些她看不上眼的,都会在失望的叹气后被扔下山崖,只留下羽毛在空中凌乱。
艾羝逐渐停下脚步,小声自言自语道:“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他双手合十,不停地念叨着。而古丽满脑子想的都是鹰,催促着艾羝:“别站着不动,过来扔鹰,扔这些不值钱的破鹰。”
他只好捡起一只鹰的骨头,走到悬崖边。冷风再次掠过,发出刺耳的嚎叫,依然是那样的阴森和冰冷,他又听到了灵魂那阵熟悉的轻语:“救救我吧,艾羝,把我从这样的生活里救赎出去。”是那样清晰,那样准确。他还记得要远离这个血腥寒冷的地方,他要自由。
可是古丽还是在不停地捡拾着鹰的骸骨,对艾羝说着“扔啊,扔啊”,艾羝犹豫片刻后将鹰骨放了下来,以一种平静温柔的语气说:“这点骨头买小羊羔可不够,我们再向上去看看吧。”说完拉着古丽继续向上爬。
两人卖力向上攀登,艾羝的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向上看去,甚至隐隐约约看到了高楼大厦,看到太阳逐渐变红向山下走去,落日把整个山照了个遍,像是漂浮在草原之上,与陆地隔着好远。他不觉得自己在爬山,而是在爬一个爬不完的天梯。
他们向山顶爬上去,随着海拔的提升,古丽感觉到寒冷,她拽着艾羝的袖口,艰难地向上,不停和艾羝说要不就到这吧,太冷了。可艾羝还是一言不发,自顾自地往上爬,直到被古丽死死拉住,才脱口一句“我们到山顶再说”。
山顶的最中心,是一只雪鸮,以一种挺拔骄傲的姿势直立着,活像一尊雕塑。
看到雪鸮的一瞬间,艾羝的反应先是一愣。像,实在是太像了。艾羝在心中不断期盼着,这就是自己丢失的那只雪鸮。他吹起熟悉的口哨,同时冲了上去,像饿狼一样冲了上去。他想具体仔细地观察那只雪鸮,不想再迟缓一秒。
是的,是他丢失的那只!它是那样雪白!那样美丽!
可是它为什么一动不动呢?死了?艾羝不可置信地看向雪鸮的眼睛,平时傲视一切的鹰眼此时早已晦暗无光了。他颤抖着伸出手去摸鹰,又哆哆嗦嗦地把手收了回来。他随着雪鸮眼神的方向望去,是悬崖,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
古丽发现了瘫软在地的艾羝,也看到了那只雪鸮,还以为是艾羝看到鹰失而复得而缓不过来情绪,还在旁边摸着他的头,帮他平复心态。
“鹰死了。”艾羝说。
“死了?没事的,死了就死了,死鹰又不是不能卖钱,除了内脏啊,心什么的不能卖以外,躯干还是很值钱的。你看,这皮毛,多好看啊。”古丽把雪鸮拿起来,掰开鹰的两只腿来回查看,生怕有一点残缺。
“能不能不把它带下去?”艾羝问。
“为什么?”古丽说。
“就是不想,我觉得它有尊严,待在山顶更好。”艾羝木然地说。
“但是你还欠着钱,不然你怎么交代?雪鸮很值钱,它有尊严了,你就没尊严了。”古丽瞪着艾羝。
“我现在很没尊严吗?”艾羝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天空。他一直仰着头。
“你甚至不如你养的那些鹰。”古丽笑着说,用肩膀和艾羝碰了一下打趣。
“你说得对,下山吧。”艾羝说。
古丽在前,艾羝在后,两人下了山。古丽的袋子不知何时漏了一个洞,可能是被鹰的尖喙划开的。洞在爬山的过程中越漏越大,直到那只死去的雪鸮不知什么时候被遗失在了山上。她想要回去找它,把它带下山去,艾羝对古丽说:“我去找吧,你先下山,一会儿我就去找你。”古丽本来也想一起去的,但无奈袋子上的洞容易让其他鹰的尸体也漏掉,她只好以一种极其奇怪的姿势抓住缺口托着袋子,下山去了。下山的过程中,她感觉到不对,回过头看着艾羝,说了一声“要不然一起去吧”。艾羝没有回答她,而是头也不回地向上爬着,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漫长的几个小时过去了,风带着鹰击长空的破风声,传入每一个在山下等待的人的耳中。古丽看到山下的点点亮光后,就飞奔着向山下跑去,直到踏上那片绿茵,才彻底放下心来,将袋子卸下,向父亲和同伴展示成果。
直到众人对古丽夸赞个够后,才有人问道:“艾羝呢?”古丽这时候才发现,距离自己下山已经半个小时了,艾羝没有跟着下山来。这未免也太久了吧。又过了一个小时,艾羝还是没有下来。大家实在是太困了,但又怕艾羝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危险,索性轮流守夜,确保艾羝下山能有人来接应。但几天几夜过去了,艾羝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古丽和买合买提也派人上去找过艾羝,始终一无所获。
艾羝的下落成了草原上的一个谜,就像迄今为止没人知道那只能够穿越三层障碍成功脱逃的雪鸮是怎么死的,还有它的尸体去了哪儿一样。人们也会在闲时议论,有人说在其他城市见过艾羝,艾羝对他说,他从山的另一端来到了这里,这里的天空更广阔,水更甘甜,他过上了幸福无比的生活,像逃出牢笼的孩子一样快乐;也有人说他早已死去,和大部分的鹰一样,将尸骨留在了高山之上。谁知道呢?但比起他所养的那些混吃等死的囚鹰,他可以选择有尊严地活,大不了,有尊严地死。
责任编辑 猫十三
作者简介
李紫杨,2004年生,北京人,北京联合大学202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有作品见于《胶东文学》等。
① Sainu:蒙古语,意为“你好”。
② Bayal:蒙古语,意为“兄弟”。
① Zalu:蒙古语,意为“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