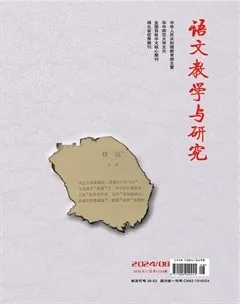从整本书阅读到整合式研读
摘要:《乡土中国》与《红楼梦》存在“互释”的空间。《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可以解读《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的定义,《乡土中国》相关理论能够分析《红楼梦》中的丧葬文化。《乡土中国》与《红楼梦》互释,既从理论层面深入理解文学作品,又结合小说情境进一步辨识《乡土中国》的核心概念,是整本书阅读走向“整合式研读”的路径。
关键词:乡土中国;红楼梦;差序格局;亲疏;文本互释
“整本书阅读”作为一种阅读实践活动,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初中阶段的“名著导读”,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消除经典作品的隔膜,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类经典著作的阅读经验。到了高中阶段,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将《乡土中国》《红楼梦》纳入到课程体系的“整本书阅读”单元。以往学生阅读的大体上是文学性作品。高中阶段除了延续这一传统外,还增加了强调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学术论著。学术著作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与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它强调的是思考和分析。可以说,这一学习任务的设计紧扣课标精神,通过阅读实践活动提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思维品质的提升。费孝通在论著中多次引证《红楼梦》的例子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教学用书》在“整本书阅读”单元“编写意图”中也提及两部书之间存在“互释”的可能。[1]本文用《红楼梦》的人物关系解读《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的定义,同时借《乡土中国》相关理论分析《红楼梦》的传统文化现象,探索整本书阅读走向“整合式研读”的路径。
一、《乡土中国》与经典文本互释
《乡土中国》作为研究中国农村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重要论著,对于现当代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来说,它是一把联读的秘钥。因此,有学者用《乡土中国》理论分析鲁迅乡土小说《故乡》《祝福》和《阿Q正传》相关情节;或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素材,解读《乡土中国》“礼治秩序和无为政治的四种权力”,进一步辨析“家族”等概念。[2]无论是原创试题还是教学设计,都在这一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祝福》和《阿Q正传》是选入统编教材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新教材的选文通过联读《乡土中国》可以进一步理解文本内涵。例如结合《乡土中国》的相关论述,我们能够进一步剖析《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婚姻悲剧”的社会原因。当妻子刘兰芝和焦母发生矛盾时,焦仲卿在焦母面前先为妻子抱不平,后自称“薄禄相”,还坚定地表示和妻子“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乡土中国》提出传统社会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两轴都会因事业的需要而排斥普通的感情。无论大户人家还是乡村,男女的隔离、夫妇感情的淡漠应是日常可见的。[3]刘兰芝与丈夫“相见常日稀”而独守空房屡生怨言。在焦母看来,儿子对爱情婚姻的满足影响了“事业”(仕途)的追求。所以在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里,为维护家庭秩序稳定的焦母坚决地拆散焦、刘二人。
《红楼梦》是古代经典章回体小说,编织了一张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既呈现了贵族世家的生活日常,又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艺术资源。《乡土中国》是社会学经典论著,提出了“差序格局”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既反映中国实际状况,又具有理论深度。这两部作品,一部是从微观视角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则从宏观层面探讨中国社会结构。
事实上,《乡土中国》和《红楼梦》互释方面的研究内容也屡见不鲜。例如:用《乡土中国》阐释《红楼梦》的居处布局[4];用“宝玉挨打”的情节解读《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和私人道德”[5];用《乡土中国》“感情定向”理论和“男女有别”相关论述分析“宝黛爱情”悲剧的原因等。值得注意的是,多个地市的考试试题也有意将两部著作整合考查[6],试图引导学生用“差序格局”的概念理解《红楼梦》中传统文化内涵。正如张冠生所言:“在《乡土中国》中,知人善任的费先生,请来《红楼梦》中人,演出了‘差序格局’的典型场景。”[7]因此,两部书之间自然存在着更多的“互释”空间。
二、《红楼梦》中的“亲疏有别”
《乡土中国》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即“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以自己为中心,以亲属、地缘等关系为主轴的亲疏有别、可伸可缩的人际关系格局。”[8]《红楼梦》的贾家,虽然不是乡土社会的某个村落,但本质上仍是依照差序格局的原则利用亲属的伦常组织的社群,是一个恪守传统礼治秩序的“小家族”。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而从“差序格局”的定义出发,这种人际关系格局其中一大特点便是“亲疏有别”。
《红楼梦》中宝、钗、黛三人的关系,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宝玉与钗、黛孰更亲?实际上,在原著中宝玉曾对这个问题毫不避讳地做过正面的回应。儒家讲究人伦,所谓“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贾宝玉对于三者的关系提到“亲不间疏”,这里的“亲疏”是指有差等的次序。宝玉说“论亲戚,他比你要疏远”,“亲戚”在《古代汉语词典》中释义为“内外亲属”。“内外”分别对应着“亲”和“戚”。其中“亲”,即“内亲”,一般指的是父亲那一边的亲属;“戚”,抑或“外戚”,通常指母亲那一边的亲属。《乡土中国》在“家族”一章提到“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9]。因此,以宝玉为中心,母亲那一脉的亲戚“宝钗”比父亲这一脉的亲属“黛玉”要疏远。
即便作为家族中的权威核心“贾母”也严格遵守这一秩序。《红楼梦》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贾母为黛玉的离世伤心不已,但又惦记着宝玉,两头难顾。最后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并让王夫人带话给黛玉的阴灵“并不是不忍心不来送你,只为有个亲疏。你是我的外孙女儿,是亲的了,若与宝玉比起来,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倘宝玉有些不好,我怎么见他父亲呢”[10]。《乡土中国》“家族”一章提到“中国式家族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11]。因此,以贾母为中心,儿子贾政之子宝玉比女儿贾敏之女黛玉自然要亲。
贾府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以己为中心,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络。一个人出生依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判定人伦关系的亲疏。《荀子·礼论》有云“事死如事生”。同样,一个人死亡,人们也会按照和死者亲疏远近关系来服丧。它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丧礼中的“五服”。此五服,别亲疏。
《红楼梦》第九十二回,贾琏提到“贾雨村又升官了”,冯紫英便问贾政“贾雨村是贵本家不是?”贾政回复“是。”这里的“本家”意思是“贾雨村”和贾家同姓氏。后面冯紫英接着问道“是有服的还是无服的?”[12]这句话意在进一步探悉贾雨村和贾家的亲疏关系。“服”即是“丧服”。旧时按照宗族关系的亲疏远近,规定了五种不同的丧服形式。《三字经》曰:“斩齐衰,大小功,至缌麻,五服终。”它们在服装的样式和时间的长短上都有明确的规制。《红楼梦》第九十五回元妃薨逝,宝玉应照为出嫁的姐姐穿“九个月的功服”,即五服中的大功服。第一一0回贾母寿终,贾府上下人等登时成服。成服,就是人们按照与死者辈分远近亲疏关系穿上不同的孝服。[13]而“五服”之外的人大多已于己没什么血缘关系,无需服丧。所以凡在五服以内的亲属叫“有服”,在五服以外的叫“无服”。夫礼者,所以定亲疏。而丧礼上服饰的形式更直观地表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三、从丧礼看《红楼梦》人际关系格局的“伸缩”
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每个人是其社会影响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在某时某地所动用的关系不同。前文中提到的“贾雨村”,贾政认可他是贾家“本家”。从亲缘关系看,贾雨村属于“五服”之外,甚至称亲属也都勉强,但依旧被纳入贾家的“自家人”范围。费孝通指出:“为经营各种事业,中国的‘家’的结构不能仅限亲子的小组合,必须沿父系加以扩大。使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质。而且凡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都得是长期绵续性。”[14]贾雨村利用同姓与贾家攀上关系,经过贾政荐推,官复原职。贾府与他也一直联系不断,多次请贾雨村帮助处理荣宁二府的官司纠纷。正如“差序格局”一章提到“‘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15]。再好比刘姥姥,利用祖上连宗过王家和王夫人攀上关系,最后又成了王熙凤之女“巧姐”的干妈,使得“自家人”范围逐渐扩大到贾府。
无论是亲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它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大小的变化依据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穷苦的人家,家庭可以很小,可到有钱有权的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如费孝通在书中举例“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的上亲戚的,都包容的下,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16],这都显示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另一大特点——可伸可缩。
诚如上文,丧服的形式是人物关系亲疏的标尺。其实《红楼梦》中关于丧礼的不同呈现,我们更能从中窥见其人际关系格局的“伸缩”。《红楼梦》中关于丧葬仪式的描写层出叠现,其中着墨最多,并对全书艺术结构起着关键作用的丧礼活动有三次:秦可卿仙逝、贾敬宾天、史太君寿终。[17]
宁国府主持的第一场葬礼就是秦可卿去世。这场葬礼场面甚是壮观。从一开始贾珍就恣意奢华,先不顾贾政劝阻,摒弃杉木板,从薛蟠处要了上等樯木做了棺材。随后又花了一千五百两银子让秦氏按五品龙禁尉受封赠。丧礼一夜灯明火彩,客送官迎。彼时官客送殡的,来的都是“八公”“四王”,王孙公子不可枚数。宁府送殡一路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
贾敬去世时,宁国府主持了府中第二场葬礼。棺材用的是贾敬生前备好的。虽说丧仪焜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但作者并没用大篇幅去写宏大的场面。反而细细写了一笔数额为六百零十两银子的欠款。最后经过几番周折,才勉强补上。宁府银钱支配上已露出入不敷出的迹象。
小说临近结束,贾府中的核心人物贾母寿终。此时贾府势败,贾政主张丧礼从简,一是丧与其易,宁戚,只要悲切才是真孝,不必靡费图好看;二是刚经历过抄家的贾府也怕招摇。只将贾母留下的银子在祖坟上盖房子,买祭田。没有银子支持,主持丧礼的凤姐也百般掣肘,先是能差使的仆人仅有三十多人,继而银钱吝啬,谁肯踊跃,不过草草了事。家人们各处报丧。众亲友知贾府势败,但见圣恩隆重才来探丧。
这三场葬礼逝者的身份渐次尊显,丧仪的场面和人气反而每况愈下。它们对应着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贾府盛极一时,丧仪焜耀,宾客如云;及其衰也,人走茶凉,门可罗雀。费孝通说:“中国人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是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18]
整本书阅读区别于单篇阅读的特点在于一个“整”字。首先是“整本”,即通读全书。其次是“整体”。文学作品要求整体把握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学术著作须要分析整体框架,构建知识体系。这都是阅读过程中必备的一种整体意识。而将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的研读,能够从抽象概念的术语体系中找到一个切入点,通过互释与贯连完成具体真实情境的构建。这不仅使得抽象的学术理论更加具象化,而且拓展了教学实践的空间。《乡土中国》与《红楼梦》互释,既能从理论层面深入理解文学作品,又能进一步辨识《乡土中国》的核心概念。帮助积累整本书之间互相印证、阐释的阅读经验,也有助于学生提升整本书阅读综合分析的能力,这无疑是一条整本书阅读走向整合式研读的路径。
注释: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50.
[2]刘智清,王锡婷主编.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与研习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20:74-85.
[3][9][11][14][15][16][18]费孝通著.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7,64,64,65,41,43,43.
[4]宋百灵.以《乡土中国》阐释《红楼梦》的居处布局原则[J].文教资料,2015(22):11—13.
[5]王紫涵.差序格局下的“玫瑰花”——“整本书阅读6课型”之人物专题[J].中学语文(上):56—59.
[6]金中,费斌妍.整本书阅读怎么考更好——兼评浙江省各地市高一期末调研卷中的《红楼梦》阅读试题[J].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参考),2022(05):60—65.
[7]张冠生.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5.
[8]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组织编写.整本书阅读“学教评”《乡土中国》《红楼梦》教师用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14.
[10][12][13]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1352,1281,1476.
[17]刘相雨.论红楼梦中的丧葬习俗[J].红楼梦学刊(第一辑):23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