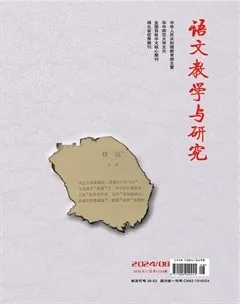当“文学”遇到“科学”: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中的知识争议问题
摘要: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出现一些知识争议问题。过去,语文教学中往往注重文学的审美和意义的阐发,相对忽视知识表达的科学严谨性。但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公众对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出异议,由此导致语文教科书的科技争议问题备受关注。本研究认为文学与科学属于不同的知识场域,语文教科书并不能完全按照科学知识规则予以规训,否则便会限制语文的艺术性与想象力,影响中小学生阅读体悟的审美能力。
关键词:语文教科书;编辑出版;知识争议;公共参与
2017年3月24日,《北京日报》刊载文章《为人教社倒掉假“鸡汤”叫个好》,指出诸如《爱迪生救妈妈》等语文课文是“虚构的‘鸡汤’”,并指出编选教材者的初心是“以伟大人物的童年故事鼓励今天的孩子们要勇于思考”,但“好的愿望还应该用更严谨、科学的手段来实现”。[1]一时之间,报刊、网络等媒体关于语文教科书编选中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各种争论。其实,文学与科学二者之间的差异、冲突并非始自今日,回望五四时期,科学引入中国,当时《新青年》杂志倡导文学革命,力促中国语言文学从“想象”转向“科学”,《科学》杂志倡导科学救国,也力推中国学术思想从“文学”转向“科学”,两方力量共同促成了中国知识传播中一场文学与科学旷日持久的紧张关系。纵观100年语文教科书编写史,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却有着从隐而不彰到剑拔弩张的历史变化。互联网媒介的崛起,促成了普通民众科学意识的提升和公共参与的兴起,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围绕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知识争议引发的社会讨论便体现了此一问题。本文希望以语文教科书中的知识争议为切口,深入探讨在知识传播中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
一、科学与文学的龃龉:以中小学语文的知识争议为对象
作为语文课程的学习对象,课文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呈现方式,同时也是知识传播的文本载体。知识的准确性与严谨性是教科书的生命,但语文教学往往注重艺术的审美、故事的讲述和意义的阐发,相对忽视知识表达的科学严谨性。近年来语文教科书出现的诸多知识争议问题引发公众的关注与讨论,甚至引起教科书的删文现象。客观来说,语文教科书会根据时代变化和教学需要进行一定的课文增删,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编辑出版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有相当部分删文是因为涉及到科学争议问题。前文提到的《爱迪生救妈妈》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讲述了7岁的爱迪生因妈妈突发阑尾炎,限于条件只能让医生来昏暗的家中做手术。爱迪生利用多面镜子以消除阴影的办法来解决照明问题从而让手术顺利完成。[2]这篇课文引领小学生了解发明家爱迪生的童年故事,同时能够激发少年儿童的创新发明精神。但这篇课文因为存在知识争议后来被删除,因为爱迪生发明手术灯时(1854年)的阑尾手术和现实世界中第一台阑尾手术时间(1886年)存在时间偏误,课文所述内容有揣测编造的成分。再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三年级《语文》有一篇课文《长城砖》,文中记述了宇航员的一段话:“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3]课文中这种说法能够满足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但经不住科学的审视。中国的万里长城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但它是狭长的建筑,穿越在崇山峻岭之中,树木掩映两侧。据专家评估判断,在60千米高空俯视,长城便已不见踪迹,而宇航员的离地高度400千米以上,更不可能看见长城。因此可以说,这篇课文中的宇航员的叙述缺少科学依据,经不起科学验证,很容易给中小学生提供错误的知识认知。除此之外,还有人质疑语文课文《寒号鸟》的故事叙述有违动物本性,因为寒号鸟不是鸟,不垒窝而寻找山洞缝隙居住是其生活习性;还有人质疑语文课文《鹬蚌相争》中鹬蚌相互夹住又如何开口说话,有违生活常识;另语文课文《云雀的心愿》中有鸟儿擦汗的描写,熟悉鸟儿生理知识的人提出“鸟类没有汗腺,何来汗水”的质疑。这些社会争议让我们看到了语文教科书课文中文学与科学之间的种种矛盾。
作为规范化、标准化的教学文本,语文教科书为中小学生提供语文读写知识,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对其内容严谨性、真实性要求很高,一旦出现了这种知识争议问题,往往会被全民瞩目,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少年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知识启蒙的关键阶段,而教科书则是他们提高知识素养、养成价值认知的重要媒介,不允许出现错误的、不健康的、争议性的知识。纵览中国历年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都不同程度地蕴含了知识传播的元素,这是因为在语文课堂中渗透科学教育是语文课标明确提出的具体要求。2011年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4]可见,中小学语文教学标准中既提到了“人文素养”,也强调了“科学素养”。语文教科书的选文要自觉容纳科学知识元素,将科学素养教育渗透到语文教学实践中,借助语文完成科学普及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语文教科书中的知识争议问题,教育管理部门和教材编写人员都高度重视,编纂教科书的专家们不但积极回应《寒号鸟》《鹬蚌相争》中的知识争议,而且在教科书修订时本着严谨的态度删除了《长城砖》《爱迪生救妈妈》等存在知识争议性的课文。
二、过去与现在的参照:从“隐而不彰”到“剑拔弩张”
通过上节的论述,我们了解到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因为科学争议问题删除了一些课文,也凸显了科学与文学的冲突。但这些语文课文存在已久,为什么只是在近些年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话题呢?这要追溯到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渊源。客观地来说,文学与科学应该各负其责、和谐相处:缪斯女神守护着人类的文化精神领域,而赛因斯先生则负责技术生产领域。科学以“分科之学”的名义将知识门类不断细化,致使科学和文学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近些年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也都曾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如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越来越被要求具有科学性。在此种语境之下,神话传说等非科学文本能否进教材需要讨论,“鸟言兽语”的文学叙述也成为争议的所在。[5]从之前的众多案例来看,近些年的这些争议主要产生在教科书编写者与作者群体中,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对此并无太多关注,也缺少在大众媒介上发表质疑的讨论机会,因此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文学与科学之间的矛盾隐而不彰,二者还能相安共处。
当代中国,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坐在电脑面前,或手持智能手机,随时随地检索、阅读着各类专业知识。在知识的“供给”与“获取”方面,互联网为普通大众提供了诸多便捷,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知识民主”时代,很多科学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科学知识逐渐走向社会大众。普通大众不但可以更便捷地获取科学知识,而且还能借助新媒体话语赋权,逐渐参与到具体的科学讨论中来。公众参与科学使原本属于小众的科学知识逐渐走向民主化、大众化。[6]这激发了中小学生与普通大众对语文课文知识讲述的批判反思意识,并开始对很多语文课文上的科学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前中小学生和普通大众缺乏知识辨识能力,不具有批判反思的媒介权利,即使个别人对此有认识、有批判,因为不能公开讨论,也便没有成为社会公共议题。而现在借助网络媒介的知识习得和话语赋权,人们从科学知识的角度重新审视语文教材,诸如爱迪生母亲做手术、太空中看见长城等一些以前人们未曾关注的话题也开始被提出。尽管很多时候质疑声音只是个别的、偶然的,但是一经网络发酵便成为社会公开讨论的问题。这些公共讨论让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日渐剑拔弩张。
三、场域与规则的移位:化解科学与文学的紧张
承上所论,普通大众和中小学生借助互联网媒介不但提升了科学知识素养,也具有了提出质疑的机会,由此引发诸多关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知识争议现象。作为标准生产的语文教材,编写教科书时需要精心选文,核实相关资料,细心编辑加工文字,为中小学生提供没有争议的学习文本。同时,作者与编辑也有责任和义务去纠正文本中存在的知识争议问题。但想要厘清中小学教科书中文学与科学之间复杂缠绕的关系,并非易事。依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人类社会由大大小小不同的知识场域组成,每个场域都有每个场域的话语规则。[7]本文提及的文学和科学属于不同的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话语规则,文学关注人、艺术、情感,而科学关注自然、逻辑、理性。科学揭示事物运行的规律,遵从客观性原则,而文学直指人性的本质,遵循艺术想象的原则。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上,常常出现小草会说话、小花会唱歌的课文,这些都是有违科学的,但在文学领域是可以理解的。再看围绕寒号鸟是否垒窝、鸟类无汗腺如何擦汗等问题引发的争议,其实,这些都属于寓言或者童话,作者将动物进行了拟人化描写,所以读者不能完全从科学规则的角度进行批判。在少年儿童的语文教育中,编者选择童话是看中了它培育学生想象力的功能,而不能简单地从科学角度对其进行否定。正如有个故事提出的问题:“冰雪化了,会变成什么?”有位同学的答案是“冰雪化了,变成了春天”,而老师的标准答案是“冰雪化了,变成了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孰对孰错判断起来并不容易。科学讲究严谨性,而文学讲究艺术性。这位同学提供的答案有着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进一步说,不管是冰雪融化变成了春天,还是不垒窝的寒号鸟,抑或说话的小草,都是人们对现实事物的艺术化加工,是以赋予想象力的故事来阐明人生道理,这在文学场域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被积极提倡的。
教育部要求在编写教科书时一定要“依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进一步明确各学段、各学科具体的育人目标和任务”[8]。客观说来,人类教育过程中,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教育重点,少年儿童尚在知识萌芽阶段,适当的童话文学作品是必要的,是能够提升学习兴趣和想象力的。我们要了解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尊重少年儿童的语言学习规律,当孩子口中“冰雪化了,变成了春天”被老师以不符合标准答案予以否决时,是会扼杀孩子们想象力的。
对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知识争议问题,应区别对待。如果出现语言文字方面或事实方面的专业性错误,这是原则性问题,务必改正,而对于文学作品中诸如鸟言兽语类艺术化表达,虽然不符合科学,但要尊重文学的艺术原则,不必吹毛求疵。例如针对有人对语文课文《鹬蚌相争》这一寓言故事提出“相互夹住又如何开口说话”的质疑,出版社的回复是,肯定孩子质疑的精神,但暂时不会更改教材。出版社认为这篇课文源自古典文献《战国策》,是以寓言的方式讲述道理,可能存在科学不严谨的问题,但并不妨碍文学阅读。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合理的。在中小学语文课文的编写与教学中,文学毕竟以审美为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让科学越俎代庖压缩审美的畛域,语文教学要注意唤起中小学生对语文课程本身的诗意想象空间,让语文教学以文学的方式向艺术审美本位复归,让语文编写从科学理性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语文是一门文学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科。语文教学中既要有“科学味儿”,也要有“人文味”,既要容纳“赛因斯先生”,也要容纳“缪斯女神”。科学与文学之间既有差异、矛盾和冲突,也有共性、交叠与融合。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中,我们要将科学素养教育与文学素养教育有机结合,让科学与文学有机融合,增加内容的生动性与可读性,让语文教科书呈现文质兼美的特点。我们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阅读习得中提升科学知识素养的同时,也应该尊重文学艺术的审美原则。
注释:
[1]牛春梅.为人教社倒掉假“鸡汤”叫个好[N].北京日报,2017-3-24.
[2]佚名.爱迪生救妈妈[A].小学语文:第3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37-139.
[3]刘厚明.长城砖[A].小学语文:第7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04-106.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5]邰爽秋.对于神话教材之怀疑[J].中华教育界,1921(7):1-18.
[6]简·格雷戈里,史蒂夫·米勒编.科学与公众:传播、文化与可信性[M].江晓川等译.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
[7]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3-134.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D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1404/t20140408_1672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