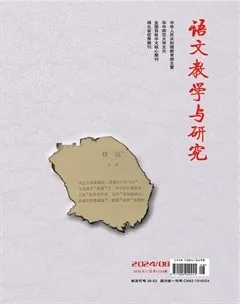从“逻辑缝隙”解读《马说》
摘要:基于“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马说》实际教学,学生可发现“逻辑缝隙”。把“千马里”比喻成“人才”存在“逻辑缝隙”,从背景还原、知人论世的角度可以理解其合理性;“伯乐相马”故事的“伯乐”与文中“伯乐”的寓意存在“逻辑缝隙”,可以还原写作意图的角度理解其内在意义;“反面论证”“论述结构”存在“逻辑缝隙”,可以从文本言语分析中理解其高超的论证艺术。
关键词:思辨性阅读与表达;逻辑缝隙;还原;喻意;马说
《马说》是韩愈所写的千古名篇,作者借“千里马”难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表现怀才不遇的强烈情感。文章先明确“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观点,进一步说明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通过对比突出伯乐对千里马的重要性。再从反面写在没有伯乐的情况下奴隶人迫害千里马,用事例论证伯乐对千里马命运的决定性作用。接下来揭示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是“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最后揭示食马者在“策之”“食之”“鸣之”时都不得法,并责怪“天下无马”,突出其愚妄无知,表现了强烈的讽刺意味。从论述逻辑来看,这篇论述层次清晰,一气呵成,情感浓烈,无懈可击。但基于“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实际教学中,不少学生似乎看到了其中的“逻辑缝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为此作出以下解读。
一、爱国精神:“千里马”喻意的背后
“文章借伯乐与千里马的传说,把人才比作为千里马”[1],教学参考用书的这种解读,是得到各方认同的。但在教学中,聪明的学生就发现,这个隐喻的背后有“逻辑缝隙”:“千里马”是动物,而“人才”是“人”,动物和人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吃、住都得靠人,是被动者;而后者则不同,人才是有思想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如果被鞭打,可以反抗,如果吃不饱,可以主动沟通;如果得不到重用,可以另择贤主,或退隐山林,或自主为王成为主人。人才通过这样的选择,可以不“辱于奴隶人之手”,不“死于槽枥之间”,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然而,把“千里马”比喻成“人才”为什么又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这需要知人论世,还原历史真相。其一,时代限制了“人才”选择的可能性。《马说》所写的“千里马”,实质是作者的自况。作品写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间,这时唐朝虽因“安史之乱”由盛转衰,但还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韩愈不可能像韩信一样另择贤主,因为他没得选择;也不可能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因为他25岁就中了进士,年轻气盛,正想一展抱负。他也不可能像朱元璋、刘邦、李渊、赵匡胤等做开国帝王,因为他深受封建统治思想的束缚,况且不合时宜。其二,“人才”的选择只能是忠君报国。韩愈是一位想报效国家的人,他初登仕途,三次上书希望得到重用,但待命40多天不被任用,仍声称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愿归隐山林。后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以待时机。《马说》就大约写在这时,表达了一位爱国青年的怀才不遇。可见,《马说》是爱国青年报国无门的情感抒发。其三,韩愈是一位爱国者。他维护儒家思想,忠言直谏,多次被贬,即使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也毫无怨言,还通过“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不畏艰难、勇于献身的忠君爱国精神。这样看来,把“千里马”比喻成“人才”是合乎作者当时处境的。
综上所述,把“千里马”比喻成“人才”,是在特定时代下的合理产物。时代限制了人才的选择性,使“人才”如“千里马”一样在封建的枷锁之下,成为被动之物,只有忠君报国才是唯一出路。因此,《马说》的隐喻背后是韩愈的“爱国精神”,是一位年轻爱国者报国无门时的情感宣泄。
二、理想统治者:“伯乐”非“伯乐”
《马说》的论点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因果的逻辑关系,即因为有了伯乐,所以才有千里马,突出了伯乐对千里马的决定性作用。而接下来作者论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似乎有“逻辑缝隙”。“千里马常有”,就是承认了“千里马”是本来就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为伯乐之后才存在的,这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因果逻辑是有“矛盾”的?其实,这还得还原到“千里马”最初的状态,“千里马”没有被发现前,还算不上“千里马”。作者这样论述,只是给它一个定性,为了突出后一句“伯乐不常有”,从而承接了上一句伯乐对千里马起着重要作用的论述。其内在的含义是指千里马是需要有伯乐发现、培养,才能算得上“千里马”。
“伯乐相马”的故事是《马说》的主要论述来源,原故事里指伯乐相中了一匹被用来拉盐车的“千里马”,解救了它,用心地培养它,并把它推荐给了楚王,使它得到了重用,这才让它成为了能够体现价值的“千里马”。如果说“发现”是伯乐对千里马所做的第一步,那么“培养”就是伯乐对千里马所做的第二步。只是“发现”与“培养”还不能让“千里马”成为真正的“千里马”,它还需要有一个人给它以展示才能的机会。故事中重用它的人是楚王,而不是伯乐。如果楚王不给机会,“千里马”的才能也还是得不到施展,也不能成为有用之马。《马说》这篇文章与故事不一样,它把“伯乐”与“楚王”的作用都赋予了“伯乐”,“伯乐”已经不是“伯乐相马”故事里的“伯乐”,而是故事里“伯乐+楚王”的化身。他不仅成了发现与培养人才的人,还是赏识与重用人才的人。作者经过这样的艺术处理,一方面意在突出“伯乐”对“千里马”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为了将“伯乐”定义为真正可以左右人才成长的理想的统治者。当然,作者眼中理想的统治者并非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某一个掌权的群体,一个可以使人才得以被发现、培养、赏识和重用的封建统治群体。
《马说》作为一篇“正能量不足”的“抱怨性”文章,却能够得到人们的共鸣,笔者认为这与人们离不开工作,有不同的职场际遇有关。鉴于“伯乐不常有”的情况,行行都有可能埋没行业“千里马”的可能,有些可能是“伯乐”根本不识马,有些可能是有意打压。不管什么情况,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它已经超越了封建统治的历史枷锁,一直勃发出永恒的生命力。
三、高超技巧:“反面论证”的艺术
《马说》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中心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第二部分揭示“千里马”被埋灭的原因;第三部分讽刺“食马者”的无知。第一,从内容上看,全文论述着力于从反面角度,先述“千里马”的悲惨遭遇,接着论述“食马者”不会食马;最后讽刺“食马者”不懂马、不识马。以上全是从“食马者”对待“千里马”的角度来展开论证的。第二,从言语形式上看,全文共152个字,表示否定的“不”有11个,尽显作者“不平”之意;文章用了5个“也”,采用不同的句式,表达了不同的情感。第三,从情感表达上看,这篇文章是作者“不平则鸣”之作,文章中充满愤懑、嘲讽、谴责、遗憾、无奈、抱怨、同情、惋惜等多种情感,看似情绪大于理性。第四,从文章结构特点看,文章采用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结构,并没有“解决问题”的结构部分,也即没有指出应该怎样对待千里马。因此,本文论述上只从“反面论述”,没有“解决问题”的部分,看似具有“逻辑缝隙”。
其实,作者全文从反面来论述,若从正面来反推,则刚好就是“解决问题”的内容,这正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论证艺术。“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论述的是从“千里马”的悲惨遭遇,论述了“伯乐”决定“千里马”的命运。从正面来看,这可得到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食马者”要以“千里称也”为标准来培养马。“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论述的是“食马者”不知道“千里马”的基本特征,所以才致使它“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从而埋没了它的才能。从正面来看,这可得到第二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食马者”要知道“千里马”的基本特征,用正确的培养方式才能养成“千里马”。“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用了三个“不”的排比句,论述了“食马者”不懂马的可悲之处,表达了作者的悲愤之情。从正面来看,这可得到第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食马者”要懂得“千里马”的习性,用正确的方法使用“千里马”,要满足“千里马”的需求,多主动与“千里马”沟通。所以,作者把“解决问题”的方法隐藏在分析问题之中,显现出高超的论述技巧。
《马说》是一篇议论性质的文章,教学中可以“逻辑缝隙”为切入点,从而拓宽学生思维,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思辨性阅读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文章从“千里马”与其喻意“人才”的区别,进一步理解作者报国无门的境地;从伯乐、“楚王”、“食马者”之间的实意与喻意的比较,理解“伯乐”的内在涵义;从“反面论述”的角度切入,理解作者把“解决问题”的结构内容包含在分析问题之中的高超艺术。汲安庆教授说:“个性化深度解读文本,还可以从缝隙入手,一窥作者的言语表现堂奥。”[2]在教学中设计“思辩性阅读与表达”任务,可以引导学生多角度,多层次挖掘文本,理清文本内在的逻辑关系,质疑其中的“逻辑缝隙”,才能达到深度理解文本内容的目的。
注释: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八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239.
[2]汲安庆.中学语文名篇新读[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