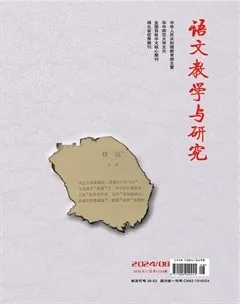从符号到意义:“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育人转向
摘要:新课标继承了语文课程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传统,整体上引领语文学科育人的价值取向。但教学一直广受工具理性、技术旨趣的影响,使教学的育人价值取向偏离本真,特别是“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更容易走向“实用”,抽离知识的文化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中,挖掘与释放知识的文化意义,以“德性之知”的激活来实现该任务群“以文化人”的价值,在积极语用体验之中以语文学科本体特有的方式实现德性之知的转“化”之用。
关键词:符号;意义;“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育人转向
新一轮改革下的语文课程内容改革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题与载体形式,继承“‘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传统”[1],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聚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由此,积极的文化精神是学习任务群具体实施的价值引领与行动指向。但是,我们既往广受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使教学偏向工具理性和技术旨趣,剥离了知识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实用”之名加上教师教学惯性就更容易导致这种偏离继续发生,“以文化人”的学科育人指向也会随之偏离。我们要在教学中回正这种偏离,就需要释放语文知识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该任务群才会实现育人指向。
一、符号表征:“实用性阅读与交流”的教学异化
传统的教学,受表征主义知识观的影响,认为教学就是让学生掌握既定知识的过程,知识被“视为个人对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reality)、外在世界的准确如实映现与表征”[3]。这种表征与映现不以教师、学生等意志为转移,成为一种外在于世界,带有预设性、客观性的独立实体存在。这些作为表征与映现的知识,在进入学校课堂场域中,是已经由课程、学科等诸多专家开发设计组织既定现成的固定静态的东西。这些既有的知识要教给学生,教学便无可避免地呈现出知识的线性传递和知识本位的模态,致使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学习的过程也彰显出工具理性和技术旨趣。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学知识观和教学行为的双重惯性会使课堂教学仍然以知识为中心,抽离知识的创造生成功能和文化意义,师生也往往以占有、表征、旁观的态度对待知识,彼此成为单向度的“知识人”而非“文化人”。“知识与产生知识的主体、过程、情境、价值之间处于分离乃至对立关系之中”[4]。这种知识观,致使承载着大量知识信息的“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在进行教学实施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异化:第一,“去主体性”。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习只是去掌握知识,从而关注的是学生掌握知识符号的情况,忽视学生作为文化学习、继承者的主体性;第二,价值无涉。教师重视知识作为事实性的存在与教授,而忽视背后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意愿,师生较少有心灵和精神的付出,教学偏向“物质”“事实”而削弱“精神”与“价值”;第三,去情境性。教师习惯性地将知识符号化,把学生的学习也“定格在符号化和确定性的‘书本世界’中”[5],丰富灵动充满境遇性的教学过程因追求结论的确定性而封闭、僵化。
长时间的思维惯性,也导致了知识固化与错位现象的出现。在知识固化上,如说明文中说明对象、说明方法、说明顺序等已成为固定结构化的教学内容,并已成为/ftwyh4ozqTp1p6P5DZaJQ==“符号”形式存在,每一次教学基本上是以追求这些知识的清晰掌握为目的,课堂从而“是封闭的、固化的、与生成无关,甚至与‘人’无关……将主体、情感、过程与个性统统拒之‘知识’的门外”[6];在知识错位上,教师把教学的重心放在文章知识或语言所承载的知识上,忽视了文本是如何将知识原理或真理事实说明、论证、叙述清楚及组织起来的,导致文本作者背后的价值信念从而被遮蔽。
二、德性之知:育人指向下知识的意义之维
知识是文化的一种呈现,它由表征符号、逻辑形式和意义组成。“知识教学的实践包括符号掌握和意义生成两个任务,掌握符号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意义。”[7]所谓意义,“指向的是人类在不同实践领域处事的态度和实践的倾向性,其属于价值观层面的东西。”[8]知识的教学,固然要掌握符号,但要透过知识的表面,在关注事实性与概念性知识的基础上,深入到知识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思想、情感与态度,即德性之知。也就是说,知识的掌握要由内容、能力之维上升到德性之维,进而实现知识的价值立场和文化倾向性。[9]德性之知源自《礼记·大学》中的“明明德”,由北宋张载提出,主要内容是天理或良知。[10]它是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珍藏,有信念功能,能给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从“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具体实施来看,获得意义的过程必然是理解并运用语文知识,提升语文能力,展开学习过程习得思维方法,提升情感与价值观层次的过程。语文素养,是在复杂情境中道德性知识运用的实践中建构、生成的。“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尽管冠以“实用性”之名,但其背后是一定文化心理的呈现。如,说明文是作者对说明对象所蕴涵的特定文化元素和某种情感心理的投射,新闻是新闻工作者秉持真理之心与社会责任感作的信息传播,等等。在教学中,要由惯性的对实用类文本所蕴含知识的辨认分析,上升到对知识运用主体的心理情感、意志品格以及知识运用所创造的精神价值的感悟,换句话说,教学要“从意义着手,以特定的意义的实现进行教学,使符号成为意义的要素构成”[11]。
德性之知,即知识的意义之维,吁求着课堂释放其创造生成的价值,学生得以在积极开放而充满可能的课堂生态环境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思维方式和视角,获得知识对人生存意义的价值感,语文课堂教学走向全人的教育,“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就实现了育人功能。
例如,肖培东《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的教学给人以启发,主要环节如下:
一、理解标题冒号作用,为“青蒿素”下定义
二、“一小步”内涵理解
1.“一小步”在文中指哪些?
2.“一小步”是( )的进程?
3.具体梳理“一小步”的历程。
4.从“小”我们可以读出什么?
三、从别的角度再拟一个标题——青蒿素:
四、作为听众,你还想理解什么?(屠为何没有说这些?)
五、与《居里夫人》相比,两篇文章语言有何不同?我们可以用什么标点结束本堂课的学习?
整个教学,是以学生对文本整体意义感的获得来达到学习完整意义感的建构,进而形成整体的价值感。教学环节在整体上形成了清晰的意义结构,即学生通过经历特定的言语实践等学习活动体验在内心构筑的整体价值系统,不同的学习活动结构会构筑不同的意义。知识符号的学习被言语实践活动转化成了意义。本文所涉及到的知识有:标题中冒号的作用,列数据的方法,演讲词要注意场合对象与表达需要,首尾呼应的特点,语言风格以及文本主旨即科学精神的理解。每个环节,既指向这些知识的掌握,又发挥了其创造性,增深了动态理解,释放出了其背后的精神意义。“列数据”的方法通过被转化为“过程漫长而艰难”“不舍不弃攀登的科学精神”的意义理解,学生体味到了作者演讲现场的心灵况味;第一、二环节的学习体验,学生增深了对“青蒿素”的理解,也理解了这一科学名词符号包含的科学家们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增深了对之的感情,冒号就在第三环节的迁移应用中进一步激发了价值感、自豪感,文本公共理解转向了个人理解即自我意义的建构,抽象的符号,在具体的言语实践语境中得以发挥价值功能;演讲词要注意场合对象与表达需要这一程序性知识被嵌入在了学生作为“读者”的期待中,演讲词的语篇交际功能在具身体验中实现;语言风格是人文胸怀——民族的自豪与担当、使命的表征,“首尾呼应”(蕴含在“‘一小步’在文中指哪些?”之中)在此时结合着有感情朗读意义化为情感的反复,是“屠呦呦们”在强调所做的研究之“小”与科学研究的任重道远,其谦逊与担当可见一斑;最后,“科学精神”以一个“标点”来蕴含,心灵领悟的价值引领替代了符号性的理性概括与认知。
三、积极语用:“实用性阅读与交流”育人转向的实施路径
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必须以“语言运用”为基础。由此,积极语用便是指向语言运用实现培育语文核心素养的关键路径。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富于创造活力的、主动完整的表现性语用行为”[12]。“听说读写视思评”七字能力构成了全语用系统。其中“思”为内语用,其余归属外语用。“视听读”又作为输入性语用,“说写评”作为输出性语用,形成了“以‘思’为中枢、以‘视’‘听’‘读’为语用基础、以‘说’‘写’‘评’为表达形式的完整语用系统”[13]。七字能力构成的全语用系统,诉诸学生在特定语境中综合性语用的实践行为来实现语文课程的“化”人功能。“以文化人”之“化”,为转化、建构生成,是通过学生积极自主参与性的“听说读写视思评”学习实践,与学习环境产生交互作用,展开分析、综合、推理、想象、判断、改造等活动,将学习所得纳入自己的认知结构,即产生同化和顺应的心理运作过程。学生在言语实践活动中,具身参与“听说读写视思评”等学习活动,充分调动感官,感受学习历程,思想力与表达力得到充分锻炼。在学习主体上由追求同质学习结果的“类主体”向个人生命激情和言语智慧的“个人主体”转变,学生作为更具体的文化主体身份去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在真实的情境中形成自我价值判断,实现公共知识到个人知识的文化生活意义建构,学生的文本理解也由“公共理解”转换为“个人理解”,知情意行有机统一,基于德性之知的实用性文本的以文化人功能进而得以实现。在课堂教学中,需要我们基于积极语用做好言语实践活动设计,且采用指向学生的意义理解的教学方式,即以意义的理解生成来引领符号的掌握。
我们再回观上述课例,每一个教学环节,基于言语实践活动,充满了思维的张力,符号的掌握被嵌入在意义理解之中。“思”字为首,且与“读”(不同形式)伴随着师生、生生互动而贯穿始终:第一环节,学生以“说”的方式来表达读思结果,“听”取且“评”价彼此的回答,形成互动;第二环节,学生在整体上“读”取且“思”考研发“青蒿素”过程的文字,转换为自己的理解与概括表达,这是“评”“说”,随之的“梳理‘一小步’的历程”,又融入有要求的“写”,最后以“评”来表达自己的感悟;第三环节,另拟标题,是“写”,也是对“青蒿素”丰富内涵的“评”价、释意;第四环节,是用“听众”置身现场还想“听”到的内容这一方式来理解演讲须注意场合与受众对象来确定演讲内容的知识,这是指向真实心灵感受的内需之“听”,具有深刻的学习意义;最后一环节,阅读电子媒介上的信息,是“视”,比较是“评”,借用一种标点表达学习的意义感,也是以“评”的方式呈现整堂课“听说读写视思评”的语用体验带来的意义增值,通过语文的方式达到育人之效。
总之,“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实施需要在达到“实用”之用的基础上育人之功,需要释放知识背后的文化意义,激活德性之知,在积极语用体验之中以语文学科本体特有的方式实现德性之知的转“化”之用。
注释:
[1]郑国民.以文化人,建设素养型语文课程标准[J].基础教育课程,2022(05):3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5.
[3]张良.课程知识观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3.
[4][6]黄耀红.现代知识观转向与说明文教学的问题审思[J].课程·教材·教法,2021(08):80,79.
[5]姚林群,向野.“教知识的符号”转向教知识的意义——兼论知识教学中情意目标的达成[J].中国教育学刊,2018(07):59,57.
[7][11]王永亮.从符号到意义:课堂知识教学的本性回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28):56,57-58.
[8]郭元祥.论深度教学:源起、基础与理念[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3):1-11.
[9]张茂译.论德性之知[J].孔子研究,2019(06):111-119.
[10]张良,王永强.化知识为素养的教学机理、过程与要求[J].课程·教材·教法,2022(06):66,67.
[12]潘涌.积极语用:语文教育和评价的应然之道[J].中国考试,2022(08):23.
[13]潘涌.积极语用:促进母语教育范式的蜕变[J].语文世界(教师之窗),2014(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