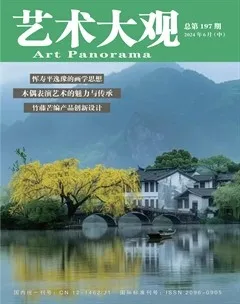困境的再剖析与新中国献礼剧的创新实践

摘 要:《窝头会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大作,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讲述了在北平的一个大杂院内底层人民的困难生活。不同于高歌主旋律的其他献礼作品,刘恒创新式地讲述了几个处于生存困境的小人物的悲惨故事,但这种在主旋律上的新的探索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剧塑造了一个个处在多重困境下的小市民形象,让观众为之动容的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与思考。
关键词:《窝头会馆》;主旋律;国庆献礼;生存困境
2009年9月,《窝头会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剧,首次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亮相。首演结束后就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次年便荣登第一期《人民文学》的头版位置,堪称戏剧行业的“新气象”,作家刘恒也因此获得了中国话剧界的认可。然而,与其他献礼作直接的“高歌新时代,弘扬主旋律”不同的是,《窝头会馆》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定在了一个看起来“永远也不可能有起色”的北平大杂院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几户生活穷困人家的描写刻画,展现了生存困境背景下不同人物的闪光点和阴暗面,从而打开了对新主旋律探索的大门。作为当代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这部话剧从小处落笔,展现出了一个大时代的悲哀与希望,是献礼作史上不可忽视的“复兴”之剧(见图1)[1]。
一、一场金钱与欲望的考验
纵观全剧不难发现,窝头会馆中的每一个人都对金钱有着极其强烈的追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处在对生命都难以把握的未知与恐惧中,钱是普通老百姓唯一可以摆脱自身困境的钥匙。窝头会馆中的人更不例外,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稳定的工作提供收入来源,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作为经济支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贪官污吏从自己的身上剥夺仅有的口粮。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人的本性也会产生巨大的扭曲,这种扭曲,是底层老百姓为了生存的挣扎。在刘恒看来,描写一个人物的某种性格时,“只有往狠里写,才能表现出人物的邪乎劲儿”[2],因此在对窝头会馆中人物的贪欲进行刻画时,一种极其夸张的效果从字里行间迸发出来。比如,故事的主角苑国钟,作为房东的他,每天的活动就是卖酒和咸菜,到了收租金的日子,他也会在院子里嚷嚷着向租客“讨饭钱”;被周玉浦问到信仰一栏要填写的内容时,他给出的答案也是“钱”。住在西厢房的田翠兰,没日没夜地洗猪肠子炒猪肝子,甚至还做过“暗门子”的生意,而这些都只为了挣那几碎银钱。东厢房的金穆蓉为了钱在外面接私活帮人接生,为此还闯了大祸。而会馆的前房东古月宗,终日以斗蛐蛐为生,惦记着他那一口棺材。他和苑国钟签了协议,赖在窝头会馆不交房租也不搬走,这一赖就是二十多年。保长肖启山为了钱没完没了地催街坊邻居交那些压根儿不存在的捐税,他惦记着窝头会馆,妄想有一天能把这儿据为己有。剧中的人物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绞尽脑汁地为金钱四处奔波。
但值得一提的是,苑国钟的儿子苑江淼和金穆蓉的女儿周子萍,接受了民主教育后,他们对钱的态度与众人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作为旧时代激进的大学生,他们对救国的远大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实现的追求远远重要于对于金钱的执拗,因此在剧中,哪怕是用来治病救命的钱,苑江淼也不愿意收下。但现实往往很残酷: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再光明的理想也必须同现实进行持续的斗争。
二、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抛开金钱不谈,窝头会馆中每个人面对的与即将面对的话题便是死亡。现实生活中,死亡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在剧中,这种沉重的情绪却被巧妙地隐藏起来。说到死亡,从年龄上来说,首当其冲的便是古月宗。作为清朝的举人,他一身“遗老”的做派,终日闲荡无所事事,没事就躺在棺材里看窝头会馆发生的一切。[3]古月宗仿佛是一个一心求死的人,他总是对其他人调侃着自己的死亡,也笑脸接受他人对自己将死的表述,但他真心想死吗?或许不是。他对死亡的向往不妨看成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他过过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对那种终日好吃懒做、以剥削百姓为乐的生活充满了怀念与依恋。然而美梦破灭,面临严峻现实,他只能以死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那苑国钟呢,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疼爱的儿子,他也会选择以自杀结束这场闹剧。但一个父亲的本能和一个中国传统男性的刚毅让他选择了面对惨状。在旧时代的中国,致使苑江淼日夜咳血的痨病,就是那令无数百姓折戟的肺结核,是骇人听闻的不治之症。面对儿子日益虚弱的身体,作为父亲,苑国钟拼了命攒钱求方为儿子治病,但苑江淼自身却不为所动。他一心读书救国,认为父亲买下窝头会馆的钱是出卖之前住在会馆里的“赤党”韩先生所得,因此打心里瞧不起苑国钟,一直没能理解父亲深沉的爱。这一父子关系的矛盾的本质是生与死的较量。而在那个年代,生是一种奢望,死才是底层人物的日常。
话剧的结尾,苑国钟为了保护儿子中弹,走在了古爷前面。但剧中又有谁的结局不是死亡?田翠兰和金穆蓉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整日苟延残喘,早就被宣告了精神上灵魂上的死亡;肖启山给苑国钟发高利贷,抽走了他为人的最后一丝尊严,这也是一种死亡。面临旧社会的崩塌,苑江淼和周子萍渴望寻找新的社会为人民开启“新生”,而这将是一条不可预知的漫长之路。但是田翠兰孙子的啼哭也能给观众答案:新的时代终会到来,笼罩在窝头会馆中每一个人身上的死亡的阴霾也终会散去。
三、一场困境与人性的探索
如果强行认为《窝头会馆》是一部悲剧的话,那剧中人物中的善良,就是这场悲剧中仅有的温存。在那个“战前能买一头牛,战后只能买俩鸡蛋”的环境里,人人都处于钱和死亡的生存困境中,但也看到不少令人暖心的画面,这些都源于中国人骨子里对人情世故的默许和“性本善”的人性光辉。说到善,剧中第一个直扑而来的便是二苑父子间的亲情。对于儿子的不治之症,苑国钟想尽一切方法要带儿子治病,在他看来,他“得变着法儿让他(儿子)高兴”。而从人性的角度剖析,苑江淼也并非一个与父为敌、因为读了些书就心高气傲的书呆子,他的背后是无产阶级,因此他不能轻易妥协。而这一场父子的矛盾,不过是怀有救国理想的无产阶级代表与为了生活而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的小市民之间的观念差异,二人并无直接意义上的利益纠葛与情感冲突。[4]田翠兰作为我国传统封建社会家庭妇女的代表,身上也有着善良、刀子嘴豆腐心的品质。看到二苑之间的尴尬关系,她一面批评父亲苑国钟“满世界就没您这么惯儿子的”,另一面又时时刻刻关心小淼子的身体健康,她也真心实意地想要他们父子关系和谐。对于金钱的执拗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心底的善良,从苑国钟催租的情节就不难看出:剧的开头就提到,金穆蓉一家“大暑一笔,芒种一笔”,加上处暑又一笔,已经欠了一季的房钱没有交,这就与剧里塑造的苑国钟爱钱爱财的形象相矛盾。他明白租客的困难,因此所谓的催租,不过是尝试要一些房钱。人家要是深陷泥沼真不给,他也不会把租客逼到绝境中去,这是中国人本性中的厚道。
面对油嘴滑舌、不交租还强占一间房的古月宗,苑国钟碍于人情没有驱离他,反而在古月宗怕和自己儿子苑江淼共用一处楼梯会传染疾病时,还亲手又为他搭建了新的梯子;面对强行收捐税的肖启山,明知“马干差价”的荒谬与无理,迫于面子与巨大的社会压力,众人也是垫齐了钱。底层人民的本分也在这一困境中凸显出来。
四、一场信仰与精神的碰撞
“信仰”一词的释义是:人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其相信和尊敬。而窝头会馆中的每一户都有着自己的信仰。在话剧中出现了极为有趣的一幕,在一个寒冬的夜晚,田翠兰和金穆蓉又拌嘴吵起架来,她们一个端出弥勒佛,一个供起耶稣像。而苑国钟的出场为这啼笑皆非的一幕画上了句号,他抱起一尊巨大的关老爷放在了院子里。弥勒、耶稣和关公,看起来三个人对于各自精神的寄托有着不同的去处。但这种底层人民的信仰,更像是穷困大众在艰难的日子里给自己找的一丝慰藉罢了。封建妇女田翠兰供奉的弥勒佛,体现了知足常乐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恰是她面对无力改变的现状而不得不煎熬下去的动力;清朝格格金穆蓉虽然沦落到了如此地步,但她心高气傲,看不起普通市民的选择,因而研习圣经做礼拜,信奉耶稣只是她不愿承认自己落魄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苑国钟选择的关公,也体现着他对关老爷手中的刀和元宝的向往——刀代表着权力与地位,元宝代表着财富与价值。而苑江淼和周子萍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们相信的是马克思,苑江淼整日读书写宣传标语,周子萍与进步青年分享书籍和个人见解。在小小的窝头会馆里,不同的灵魂之间相互碰撞,它们都是那个时代以及处在那个时代下的人民冲出精神枷锁的唯一途径。这些信仰大多是模糊的,是盲目的,但也是无奈的[5]。
五、一部献礼的佳作
回归正题,我们就必须探讨《窝头会馆》这部话剧是如何用一个悲哀的结局,成为国庆献礼史上的经典的。首先令人不解的便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即对会馆这样一个特殊环境的塑造。刘恒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纪念,或者说作为一种民族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时刻非常值得咀嚼和剖析”。因此,他通过描写窝头会馆这样一个小的环境,从而映射出一个大的时代。表面上在写窝头会馆,而重点却在会馆以外,他在尝试用一个会馆里房客的艰难残喘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北平城老百姓的悲惨命运,进而使观众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对新主旋律叙事的探索。《窝头会馆》在立足戏剧本体的基础上,将政治元素自然地过渡到人物角色中,使主旋律的特点合理地融入人物的性格。同时,这部话剧对焦底层百姓的生活,力求刻画底层人民最真实的生活[6]。剧中的人物,看似整日忙碌于发生在身边的那些小事: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每天睁开眼都必须考虑的人生大事。
小人物是历史的讲述者,为了更好地把这段故事讲给观众听,刘恒在语言上也大量使用带有地方特色的“京味儿”土语,力求构建一个最真实的场面。通过小人物的表现,地域方言也成了展现大时代最真实的声音[7]。而到现场观看的观众,无一不也是与剧中小人物相同的小人物。通俗的表达、真实的历史和象征性的艺术运用,在使话剧更有说服力的同时,也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代入感。如此一来,话剧方能赢得好口碑。
话剧的最后,苑国钟死了,乍一看是令人惋惜与痛苦的,但对于苑国钟自己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中弹成了他逃离这个可怕现实的最佳方式。此时父子关系的矛盾已然化解,他与田翠兰的“奸情”也天下大白,肖启山想要私吞窝头会馆的阴谋也被戳穿,他死而无憾。如果说苑国钟的死象征着旧时代的结束,那最后一声婴儿的啼哭便是对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宣告。人物的悲剧正如这个时代的悲剧,人物的新生也是这个时代的新生。窝头会馆的众人也从苑国钟的死中学到了如何走出困境,他们也必将继续奋斗,就如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一切都是欣欣向荣。也许《窝头会馆》的话剧本身就是一只吹不完的口琴,这口琴代表着中国的不屈不挠,证明了那句“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道理。[8]在充满美好与希望的今天,我们仍需要像《窝头会馆》这样的新主旋律话剧,让当下的人们重新回到那个战争年代的不安与揣测中,并在这种消极情绪中寻找现实生活的光明未来。
参考文献:
[1]胡鹏林.《窝头会馆》:话剧的回归[J].文艺争鸣,2010(10):54-55.
[2]花曼娟.《窝头会馆》:新主旋律叙事[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04):79-81.
[3]周菊芹.北京人艺话剧《窝头会馆》中小人物生存困境解析[J].戏剧文学,2018(03):87-90.
[4]李永亮.阐释学视域下的戏剧表征与革命建构——以《窝头会馆》为例[J].当代戏剧,2018(04):9-11.
[5]底洁璇.论刘恒《窝头会馆》中的三重生存困境[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25(04):110-112.
[6]宗世龙,台梦雅.从《窝头会馆》看主旋律话剧的继承与发展[J].当代戏剧,2021(02):24-27.
[7]王笑寒.以史为鉴,史中觅诗——浅谈《窝头会馆》的艺术精神[J].戏剧文学,2018(07):67-70.
[8]王璐瑶.永恒闪耀的中国梦——论话剧《窝头会馆》与电影《钱学森》的主旋律之“魂”[J].戏剧之家,2018(06):29-30.
作者简介:刘佳朔(2005-),男,河南开封人,本科,从事戏剧影视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