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活着”叫大叶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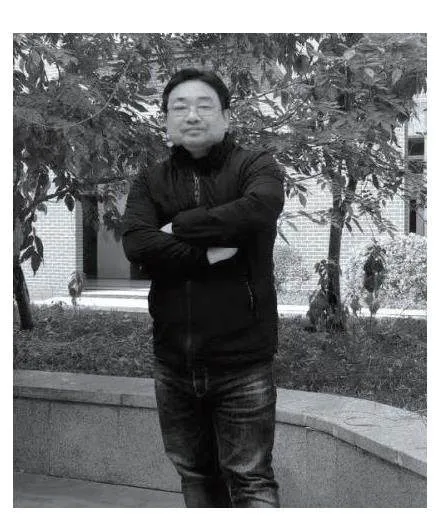
一
在乡村里,大叶杨是一种不同于檩树、柳树、槐树等树种。它远不像那些树种一样,东一棵西一棵,很随性地生长在乡村大地上。它们更像是一支正规军,排列整齐,使命感极强。它们正常出现在河堤上,而且是那种新挖的大河的河堤上,一般的小河,还不需要它们的出场。近来在我老家旁边新建了一条省道,省道要经过北面的江界河,这是一条相对比较深而宽的河流,河岸的一侧多年前种植的大叶杨,随着这条路蓦然出现我们的视线中,每次开车从旁边经过时,总有瞬间时空错乱之感。恍然重新回到三十多年前和父亲一起在海滨的日子。
和家乡难得见到大片大叶杨不同的是,在农场这些大叶杨则是随处可见,只要有堤坝就有树,只要有树基本就是这种大叶杨。每当步入一片大叶杨的领地时,总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它们那一个个笔直的站姿就让你不得不顿生景仰之心,甚至你会觉得连那树下的杂草、灌木也是笔直的。这是不是传说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东倒西歪的树干、横七竖八的枝条、肆意纵横的藤蔓在这里是很少的。树林整体是有序齐整的,即使那些鸟鹊们在树枝上做的窝也都是有点儿气派的豪宅。因为大叶杨枝头较高,它的枝丫一律向上,而不是张牙舞爪一般,向四处伸展。所以鸟鹊们要想做窝,只能做在很高的枝头,而枝头上的空间也不是很大,这就增加了做窝的难度,所以一般小的鸟雀不会选择在那儿做窝的,太费劲了。所有的树林都是“横柯上蔽、在昼如昏”的,大叶杨树林自然也不例外,但还是有些不同,因为树干整体的高度高于其他树种,所以树林里光线就优于其他树林,这便少却了很多压抑甚至阴森感。再加上大叶杨光滑而银灰色的树皮,使得在这样的树林里,即使在黄昏之时,也仍然会透出丝丝光亮,这一点似有若无的光亮,对于在树林里行走的人而言,不啻于指路的火炬。
事实上,即使“月上柳梢头”,在那人烟稀少的海滨,在寂静的树林里你仍然会碰到“人约黄昏后——那三三两两扛着农具回家的农民们。他们刚从田里归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属于陶渊明的浪漫,对他们而言只是生活的常态。大字不识一个的他们自然没有欣赏这种美景的心态。虽然他们扛着锄头,拎着铲锹,佝偻但不失挺拔的身躯,疲惫但并不失干劲的状态,应该是这清风明月下最美的风景。但他们的审美还停留在那被反复侍弄的禾苗身上,那是他们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生活审美。这时鸟儿们早已归巢,对于这些不速之客,鸟儿们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有些短暂地表示不满之后,便又很快地进入梦乡,其余的则不予理睬,树林里还是一片木讷的平静。远处农场队部次第的灯火,如一条隐隐约约的丝缕,在夜风中飘舞着,模糊而又清晰。那里是他们温暖的期待,也是他们期待的港湾。老婆和孩子们是他们对抗生活这块盐碱地最好的养分。
这些人其实并不是农场的职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来自附近乡镇以及盐城北三县也就是滨海、阜宁、响水的人比较多,也有来自连云港的,甚至还有更远处省份山东、河南的。这些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都是来“讨生活”的。他们中的大部分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条件好的谁愿意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吃这狗不嚼的苦呢。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生的孩子比较多而活不下去了,在计划生育抓得很紧的年代里,超生带来的次生灾难是一个家庭远远无法承受的。一句“讨生活”道出他们内心多少无奈和辛酸。
从某种角度上,这黄海之滨的农场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和庇护所。在上个世纪末很多人南下广东做“淘金者”,其实还有这么一些人东下海滨“讨生活”。这些人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大部分人最后也脱贫致富了,毕竟种上百亩田,利润还是可观的。他们中有一些头脑比较活泛的混成老板,甚至富甲一方的也有,当时就有一位职业和我一样做老师的,因为超生被开除公职,然后包农场的鱼塘,一步步做大,成了当时四岔河镇一带有名的老板。“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在这“山穷水尽”之地,他们最后“柳暗花明”。岂不奇哉、乐哉,生活就是这样的有趣,前脚给你一个耳光,后脚又赏了你一块糖。
大叶杨是一种耐寒、耐盐碱、快速生长的杨树品种。这大概也是它们被选择大规模种植在黄海之滨的重要原因吧。它们脚下的土地,准确地说是人类从龙王爷嘴里夺下来的骨头。因为在多年之前这块土地还是汪洋大海,后来由人工围海造田得来的。虽说现在有了挖掘机这样的大型机械,在围海造田工程中便利不少,但其实这其中的风险一般人未必知晓。我曾听人说,涨潮时那几十台挖掘机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如果跑得慢自然早就下海去陪龙王爷了。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驱龙入海,围堤成形,也还要防止龙王爷不甘心,凶猛反扑。海水暴涨之时,完全有可能功亏一篑,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大叶杨正是这样应运而出。它们是护堤固坝的好手,正好帮助这些滨海生民们维护来之不易的家园。这些还远远不够,它们脚下的土壤其实是极其不易种植庄稼的。泡在海水中亿万年的土壤已经是每根血脉都充满了盐分了,这种盐碱地要经过几代人的改良才能成为良田。而在这之前大叶杨则承担了改良土壤的重任,而且还把这些转变成自己的养分,让自己长得更加粗壮高大,顶天立地成为海滨一道道海风无法越过的屏障。龙王最后不得不退避三舍让出自己地盘,这些名叫大叶杨的勇士功不可没。
很多年前有一个少年骑着一辆幸福125的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行于大叶杨林中那高低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午日的阳光透过丰茂的枝叶投射到他的身上,外面暑气四溢,而这里却清凉如秋,少年哼着不成调的歌,手里拧着油门,马达发出舒畅的声音轰鸣着。在他的面前,不断有鸟雀被惊起,从草丛里直窜向树顶,两侧的灌木丛被车子分开着又合拢上,鼠尾草、延龄草,争相拍打着车轮和消音器,似在驱赶又似在挽留,很快摩托车开到树林的尽头,少年用脚撑着地面,看着面前突然断了的路,那如犬牙交错般的大圩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失去大叶杨遮蔽的阳光突然又肆无忌惮、火力全开地直射向他,他不得不手搭凉棚看着前方,思索着前方的路在哪里?
二
指着我家门前公路两侧的大叶杨,走亲戚的小姑丈说了一个生财之道:“你们晚上用透明胶带反过来缠在树干上,到了第二天早上,每棵大叶杨上可以抓到几十只蝉,我们那儿靠这个一个夏天能卖大好几千呢?”大家赶紧附和说:“你们海里的人真是想法赚钱……”当然也没人当回事,原因有很多:我们这里大叶杨很少,没有人专门收蝉。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这里的人赚钱思路比较窄,没有他们活泛。他们是谁呢?其实可以理解为第二代移民。从方位上来讲,他们是邻近海边的几个乡镇的农民,但大都是从西边乡镇移民过去的。他们的上一代,其实也是移民,虽然他们移的距离也就十几里路,有的范围只是在本乡内,但终归也是为改善生活,举家搬迁。移民唯一的好处就是田多,越往东田越多,小姑丈家的田是我们这里人两倍还要多,田在农业社会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就能够理解,一代代移民们为了田地如同候鸟一样不断迁徙,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垒灶砌房,开垦挖掘讨生活了。
无论哪一代移民们都是极其能吃苦的。我家到我小姑丈家有四五十里路。在交通工具极为发达的今天,驱车时间二十分钟左右;而这个距离在自行车的时代需要至少二三个小时。我小时候和我小姑最亲,父亲、母亲整天忙于生计,就把我扔给小姑,是小姑把我带大的,所以我人生最初的痛苦来自于小姑的出嫁,我的痛苦来自于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将不能常见小姑了,而小姑的痛苦则来自于她更清楚地知道,她将不能常回家。因为她即将去的新家是一个在那个时代极为遥远的地方。遥远到那里是真正意义的海边,遥远到很多年以后,那里成了麋鹿的家乡。我们现在需要花门票看的珍稀动物,他们每天干农活抬头便可以看到。
那里不仅遥远,而且极为荒凉,我上五年级的那个暑假便是住在小姑家的,对于我这个大侄子,小姑是极为亲近的,她当年对我年幼的表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将来有你军哥哥养,不要你养。”小时候表妹比较顽劣,小姑说的当然是气话。那个暑假我亲眼见证了什么叫荒芜人烟。以至于多年之后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首先是连个像样的路都没有,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竟然是从沟渠里走的。今年的暑假我因为办老家的房产证,阴差阳错地开着汽车又走到了那一段路程。那一段沟渠现在是麋鹿路的一段,省道标准,标准的柏油马路。然后是住户很少,几幢低矮的茅草屋散落在田野中间,小姑丈家兄弟比较多,三幢丁头府一字排开,小姑家是最里面一间。站在门口的晒谷场四望是天地相连,一眼看去除了田野还是田野,这就是《勅勒歌》中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风吹草低见牛羊”倒是没见到,但对小姑家养的几只绵羊印象特别深刻,那几只弯着角,卷着毛的绵羊“咩咩”地叫着,构成我童年时代对“海里”最新奇而清晰的记忆。而这一切在短暂的三十多年之后都消失了,在我奔驰着的汽车两边有很多别墅,即使瓦房也是气宇轩昂的。当年小姑家的老屋现在已是庄稼地了,他们也早搬到北边的农庄线了,在和小姑丈的交谈中我惊奇地知道,现在连他们当年赖以发家的田地都已经租给别人种西瓜了,当然是以比较高的价格了,而他们也成为新的打工族:有的帮助管理西瓜,有的到保护区打工,也有的到外地打工。当年穷得只剩下田的人们现在也不需要种田了,但田给他们的巨大财富仍然持续着。这大概也是这里的人们都普通富裕的原因之一吧,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以前他们是整天在田里忙碌,而现在他们是整天在外面赚钱,小姑丈每次通电话都是在工作中,今天挖树、明天在林场干活,大后天被保护区叫去埋打架死亡的麋鹿尸体,反正没个停歇的时候。就像一只麻雀一样一年四季忙着啄食。在离他们不远的几条大圩上都是成排的大叶杨,它们就像小姑丈一样笔直,朴实而扎实。那儿是我童年时最喜欢去的地方,那时候这些树比我高不了多少,在海滨呼啸的风中东倒西歪,看起来是那样的弱不禁风,但是因为沿着大圩密密麻麻地种植着这些大叶杨,所以看起来还是颇有气势的,想不到多年之后,它们都已经成了气候,当年的孩童现在已年近半百,而这些大叶杨大概还算是少年吧,这是不是“出走半生,归来你还是少年”呢。大叶杨自是默默,而我也在凌乱的风中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在离大叶杨不远的地方则是小姑的坟冢,在我上高二的时候,在他们全家筹备新房子的时候,小姑不幸去世,而在她去世前我还在酝酿写一封信寄给她,信永远停留在那个秋季,得知消息的那个晚上我彻夜难眠,冥冥之中小姑就默默地站在我身旁。这是一定的,我们是心灵相通的。我把灯关上,把手伸在空中,感受到那个世界的温度。我额头的伤疤在那个夜里隐隐作痛,我知道那个世界的小姑哭泣了,我额头的伤疤是她一次感冒后,让我坐在一位邻居自行车的前杠上而出的事故,在王港河桥上她自责地准备跳河自杀。死亡就这样以一种极为猝不及防的方式在我人生记忆最为清晰之时、情感最为敏感丰富之时烙上我的心坎,从此以后,只要相关的人和事被提及,我的泪腺便会立即被拉开闸门,毫无办法,伤痛在这件事上我完全失去免疫能力。小姑坟前那片大叶杨是我每次经过时必注视的地方,在我进城工作、去苏南生活、甚至有一次交了女朋友,我也把她拉到小姑坟前,那位姑娘当时没有惊愕反而安慰我,至今让我想起仍然十分感动。我在注视着那个世界的她,她也一定在注视着这个世界的亲人们,不知她看到曾经贫穷的家乡现在如此富裕,看到她的女儿现在嫁到城里,一家人幸福美满,会作何感想。想到她临死前还在四处奔波,为她的新房子筹钱、购物。劳碌而好强的性格是她的优点,也是她的弱点。唉,恰如这树林中的一些大叶杨,它们没有迎来最后灿烂的朝阳,在某一个寒风凄厉、风雨交加的夜晚,折了。但它们仍是这个大圩上不可或缺的一员。在移民的路途上,那些过早离开的人们,足印依旧填满了那泥泞的道路,不应忘记,也不会被忘记。
“一定的!”你听,那是大叶杨们集体的回答!
三
大叶杨注定是一种和檩树、柳树、槐树不一样的树种,檩树可能是由于一棵檩树果的机缘,而在陌不相识的土地上安家立业,柳树则也会因为一次偶然的插枝而生根发芽。但大叶杨一定是群体性搬迁。从这个角度,苏北地区有很多家族也算是大叶杨一般的家族,都是从远方迁徙而来,这是一个异常漫长的过程。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叫洪武驱散。现今大多数苏北人都把睡觉戏称为去“苏州”,一念成梦,梦里一念成真,无论现实如何残酷,总不能不让人做梦吧,现实中也许可以阻止回故乡的步伐,但梦里任谁也不可以,一个流传至今的戏言,流淌的是数百年来多少代移民们最大的心愿。
为什么会发生洪武驱散,一个在我儿时仍然流行的词语也许可窥一斑。我们小时候如果有小孩子尿床,便被大人戏称为“洪水漫天”,而且小时候每当发大水,大人总会说洪泽湖水要漫过来了,要灭朝了。当时就很奇怪,印象中洪泽湖离我们很远,我们为什么如此地恐惧它,还有,无缘无故一个大湖的水怎么可能就漫过来呢?这种恐惧其实是缘于发生在明朝初年的一次真实事件,当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在泰州城和张士诚手下大将吕珍交战,泰州城久攻不克,结果朱元璋用了一个毒计,就是挖开湖底要高出附近淮、扬、泰、高、宝、兴、盐、东台、海安等地三丈有余的洪泽湖东坝,这场洪祸的结果是泰州城尸横遍野,吕珍的军队几无生还。这就是“洪水漫天”的由来。而这场洪水之后,则又出现新的问题,那就是苏北人少了。人少了,自然赋税也就少了,而苏北作为产粮造盐的主要地区,也是朱元璋称王的主要根据地,这样肯定不行,怎么办呢?朱元璋把目光转向了富庶的、人多地少的江南。这块张士诚的地盘让朱元璋在攻打苏州时吃够了苦头,那就把这些当年支持张士诚的江南百姓们送到苏北开荒种地,造盐经商,这样一箭双雕,既瓦解了江南的“拥张”势力,巩固了朝廷在苏南的统治,又开启了苏北的重建工程,保证了苏北对朝廷的税供。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迁徙——“洪武驱散”。
一代代传递危险的信息,这是动物的本能,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一种灭老鼠的药,倒下第一批后,之后的老鼠就不会再中毒。人类也不例外,手口相传的也往往是那些对种族的生存具有威胁的人、事、物。正如我的祖先口里的“洪水”。但是奇怪的是在我的家乡对于“洪武驱散”的始作俑者朱元璋,人们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怨恨,反而是流传了很多神奇的谚语。比如说“朱洪武扫地——各登原位。”“朱洪武火烧庆功楼——一窝端”等。这些谚语反而更多地是对朱元璋神化的赞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对于迁徙这件事,其实历朝历代都有。历史上的五胡乱中华、安史之乱,都使得战乱中的北方人大规模自主迁徙到南方。清代著名的的湖广填四川,以及后来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也是有名的移民潮,大部分的移民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出于谋生的目的而迁徙。即使是洪武驱散,也是有一定的政策扶持,在其后期政策也相对温和得多,老百姓有条件的是可以回去祭祖的。
移民们也许在当时会对朝廷有些怨言,但最终这一切都会随着生活的安定而渐渐消失。“铁打的土地,流水的人”“树挪死,人挪活”这些朴素的道理老百姓还是懂的,迁徙的过程,背井离乡固然很痛苦,但是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尤其对于贫穷者而言,重新洗牌,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如那些大叶杨,当它们被移植到一个新的土地上,土地固然贫脊,但阳光、空间、水源却都是成倍于从前的。
在苏北这块土地上,与“海龙王”相伴的地方,数百年前,这些从南方富庶之地移民过来的人们,带来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理念,雄厚的财富,这些都给这块土地注入巨大的生机,也使得这块土地拥有了和龙王一争高下的实力。
就如那些长在河岸边的大叶杨一样,它们有群体的力量,有着笔直挺高的基因,也有着耐低温、喜水、喜光照的特点,这些和苏北的自然环境很契合,自然发挥了成长较快的特点,它们在海风中不屈地生长,它们拥有比其他杨树都宽大的叶片,它们近乎贪婪地吸收着阳光雨水,拼命地向蓝天、大地伸展。而那些迁徙而来的生民们很快地在这块土地上扎根,繁衍发展,他们的勤劳、智慧、吃苦耐劳使得他们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建立了新的村落,甚至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的祖辈们继续趁胜追击,继续向东发展移民,向“海龙王”要土地。在今天盐城是江苏最大的一个市,但有谁知道这个“大”其实更多的是先民们战天斗地,几代人、数百年如一日地开垦拓荒和“海龙王”长期拉锯战的结果。
移民们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劳劳碌碌一辈子,白手起家,万事艰难。在社会地位上要低于原著民,在情感上长期处于无所归依的状态,痛苦和煎熬是他们日日夜夜进补的中药。勤劳和低调是他们时时刻刻谨记的立身之本,脚下的土地从他们踏上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和他们血脉相连、荣辱与共,他们看似在选择,但其实这种选择本就无法选择的选择。当然如果从一个家族的长期繁衍发展来看,他们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基因,在家族中刻入了勤奋、吃苦、韧性、谦卑的优良基因,而这些最终会使他们的后代中人才辈出。就像大叶杨其实也是一种由小叶杨改良过来的树种,它只有在人工的干预下才有了大叶杨。大叶杨的叶阔枝长、主干粗壮,也正是在一代代的向天争、与地要的过程中奋斗出来的,是啊!这世上哪有轻轻松松的成功,所谓的闲庭信步又有哪个不是风雨中熬过来的。年末的一个夜晚我驱车回老家,再次从那片大叶杨树林身边经过,在226省道如同白昼的路灯照耀下,那些大叶杨们依然是那么的精神、斗志昂扬。这条省道从我的故乡穿过,乡村的宁静被打破,这块土地在国道、省道、高速的加持下,未来可期。岁月静好之下,遥望大叶杨树林的尽头,那些在泥泞土地上艰难跋涉的先民们,在漫长的黑夜里终于为我们守候来了黎明。
四
在江南道绝少“大叶杨”,满目苍翠的绿林中有出身高贵的银杏树,也有名声不凡的梧桐树,它们作为行道树装点着繁华的都市,犹如灯塔般的存在,照亮了这片大地,为繁华的都市增添了别样的魅力。它们姿态不凡,本身也自带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成为城市的一张张名片。
无数个白昼它们提供荫凉给从树下开着车一闪而过的都市人,即使人们很忙,忙着赶路、忙着赚钱、忙着生计。当日暮低垂,人们匆忙地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时,这些行道树上斑驳的树影,就是他们疲惫生活中的一丝宁静之源。在这些行道树之下,孤独的孩子们找到了他们的避风港,迷茫的年轻人找到了解惑之道。这种善解人意的行道树,自然是我向往和喜爱的。可是我仍然依恋和怀念着我那海边的大叶杨。
那在海边和海风鏖战着的大叶杨,它们对城市的繁华没有任何概念,因为太遥远。离它们最近的是和它们共存共生的,却无边无际的大海。海龙王对它失去的土地一直是不甘心的,日夜想要夺回来,而这一排排的大叶杨则是它要突破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看起来弱不禁风,但却难以逾越,而且它们的成长速度很快,越来越像一座绿山,问题是如果是山,海龙王还就真的可以淹没它,但是对于这些以站桩著称的大叶杨,却是束手无策。
“你想淹就淹吧,可是你走了,我还在。”
那些大叶杨仿佛在嘲笑海龙王的无能,又好像在对着大海宣誓:“绝不离开阵地,阵地在、树就在;树在,阵地就在。”这大概是我一直对大叶杨碎碎念的原因吧。
若干年前我有个发小说过让我当时感到无比绝望的一句话“三代修不到一个城旮旯”,那时我还是一所农村初中的老师,和很多老师一样渴望调到城里去,也为之付出很多努力,但似乎都徒劳无功。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会想,我大概会在这里工作到退休吧,最为孤独和寂寞之时,便会抬头看看屋后窗外的一棵大叶杨。宿舍边上竟然长了一棵孤零零的大叶杨,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它和周围的那些树格格不入,开始不显山不露水,在那些乡里肆意横生的树木之间,显得那么的文弱。但它那笔直的干却是乡间的树所缺少的,乡间的树没有大叶杨这么自律,总是长得歪歪扭扭,粗壮倒是挺粗壮,但是不高、不直,不合乎匠人们的用料要求。这棵大叶杨渐渐地长成了气候,在那片小树林里显得有些出类拔萃。每当我的目光游离到那些绿叶之间,大叶杨总是向我招手,而我便能够安然自己的心绪,坐下来做自己喜欢的动画课件,备自己的公开课。
数年之后,刚过年不久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教研员的电话,说实验初中想借调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就这样多少老师梦寐以求的进城梦,毫无征兆地砸在了我的头上。这时我才知道,所有的夜以继日、“焚膏油以继晷”,其实都是有回报的,我这才明白,大叶杨一次次用它那宽大的叶子安慰我那颗浮躁而功利的心是有目的的。走的时候,天气已经转暖,大叶杨长得更粗更直了,我离开的时候强忍再去看它的欲望,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它送的第一个,更不会是它送的最后一个。
在江南富丽堂皇的城市中,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仿佛是从古老神话中走出来的巨象,傲然独立于天地间。当黑暗降临,忙碌的人们踏月归家时,唯有梧桐树悄无声息地守护在路边,默默地承担着那份沉甸甸的深情。无数个黑夜它们陪伴着那些孤独的、迷茫的城市游子们,我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十多年前初到江南,阴差阳错,我调到了一所农村初中,从苏北到江南,从城里又回到了乡下,兜兜转转又回来了。虽然江南的繁华近在咫尺,但城乡的差距永远都是存在的。我有时候也很惊诧于自己的折腾劲儿,“三代修不到一个城旮旯”你这一代就到了城里了,怎么又折腾到江南呢?这里当然没有大叶杨,但是故乡的大叶杨的影子总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会进入我的脑海里,这时那在海风中挥舞着叶子的大叶杨仿佛在告诉我,我的血脉里流淌的就是奔波、奔腾的基因,我的先祖们当年出发的地方,他们做梦都想回来的地方,我没有理由不为他们圆这个梦。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第一天到了江南,睡在那个老旧的宿舍楼里时是那样的安详,因为这里才是我祖先的根,我的血脉和这里的山山水水是相通的。
没有大叶杨的日子里真得很孤单,江南的夜,总是那么静谧,那么深邃。每当夜幕降临,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灯火阑珊,听着夜莺的歌唱,在繁华中感受着一份落寞和寂寥。校园是一所历史相当久远的寺庙衍变而来,自然是有树的,而且都是历尽沧桑的老人,数百多年的银杏就有两棵,操场边上长了很多檩树,每棵都有两三人合抱那么粗。在这样的树面前,人往往不得不低眉敛目、内视自己,审视自己到每根纤毫。
现在想来在那段没有大叶杨的日子里,确实是我人生中最为失意、孤独、郁闷的一段时间,我像一棵被移植到异地他乡的大叶杨,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我所依仗的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我所擅长的这里没有人欣赏,我所不会、不屑的这里大行其道。我再一次回到了当年在农村初中的那段冰河期。屋后的那棵大叶杨再次莅临我的梦乡,给我以指点。我瞬间明白一个道理:与其回避莫过于迎难而上。当我闷着头创作时,写论文、写散文、小说时,当我在这座曾经让我无比郁闷的老镇身上寻找到无数的素材时,我才恍然大悟:所有出现在我们生活的痛苦,其实都是带着考验使命的。
今年过年时,我带着我的女儿,踏上了去往江界河畔大叶杨树林的旅程。只见芜杂的226省道上车水马龙,繁华非凡。一如既往。大叶杨树林中的寂静无声,而在一旁的羊圈中,几头山羊发出“咩咩”的叫声,犹如对我们到访的不解和疑虑。我缓缓地摩挲着那光滑如玉、青白相间的树干,抬头凝视着那高耸入云的枝干,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远隔万水千山的海边时光。那时每当我躺在一棵大叶杨下,都会感受到无比的安全与宁静。在这里,阳光透过柔软的树冠洒落下来,如同天使挥舞的羽翼,为整个世界带来温暖与希望。一层一层的金色光斑环绕在河流之上,如同将点点星光洒落在大地上。此时此刻,一切喧嚣与纷扰皆已远离,只剩下内心深处的宁静。平原上的昏黄光线,仿佛在渐渐褪去,只留下一片平坦的夕阳余晖,让人心生感慨。
今天是大年初七,人日,也被称为“人胜节”“人庆节”“人七日”等。传说女娲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今天一年天气晴朗,预示着这一年人口平安,出入顺利。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哪一年在老家呆过这么长时间,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厚实的安宁,我知道这份异常的安详既来自于这故乡的大叶杨,更来自于我日趋成熟的内心,那是我在没有大叶杨的日子里所炼就的。
远处夕阳打来一圈圈光晕,传来了宇宙的寥阔和空寂。如同河里的涟漪。洗涤了尘埃,送来了温馨,带来安实。
作者简介:
陈继军,笔名,枫叶秋魂。苏州市作协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有散文集《千思锦挹》《岁月沉锚》出版。 在《散文选刊》《苏州杂志》《海外文摘》《小小说大世界》《小小说月刊》《奔流》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曾获“首届汩罗江文学奖”“中国西部最佳美文奖”“首届华章杯原创文学奖”“首届文心雕龙杯全国教师文学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