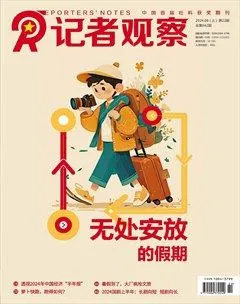我的底色是军绿


我是在军号和军歌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直到现在,年过半百的我只要听到集结号或是军歌都会驻足向往且热泪盈眶。
上世纪70年代,年幼的我跟随当兵的父亲生活在汾西县武装部的家属大院里。我记得汾西县武装部坐落在县政府东边长约千米的狭长地带。中间被一道坡分成两段,坡下是武装部的办公场所,一排一排的办公室门窗都是军绿色的。坡上是参差不齐的排房,住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军属。住在军属区的大人们操着一口浓重的家乡方言,小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刚刚开启,大部分就都会说三种话:在家和父母说家乡话,在外和当地小朋友说汾西话,在此基础上为了交流方便都会说各种腔调的普通话。这种环境培养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分辨方言的能力,我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各种特色的发音。
武装部的大门很高,一米多的台阶上还有净高六米的两扇木门,大门敞开时,时有部队的军车进进出出,台阶两边留有站岗的位置,站岗的士兵总是神情庄重。右边的一扇门上留出了—个约两米高的小门供单人出入。军绿色的大门配上硕大的门牌,再加上东西两边长约五十米和大门等高的围墙,令人心生敬畏。
虽说武装部戒备森严,但对我来说这里是我童年时代的温馨家园。绿门、绿窗、绿车加上时时能看到的绿军装,我儿时的记忆是由那一抹抹军绿色组成的。我记得每当晨起的军号响起,父亲便迅速穿好军装去操场跑步,无论冬夏;还有每天上午的打靶训练结束,饥肠辘辘的士兵闻着诱人的饭菜香味儿列队高歌,群情振奋。那些看似寻常的一朝一夕,一事一景,都浓缩镌刻在我的梦萦。
印象中,武装部办公区大院里的树木总是郁郁葱葱。第一排是一棵棵挺拔的杨树,就像军歌《小白杨》唱的那样:“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栽下它,就当故乡在身旁。”从第二排起,树种就丰富了,除了杨树、柳树、椿树、梧桐树等不结果的,我和家属大院里的其他小伙伴更多关注的是杏树、槐树、李子树、苹果树、核桃树、沙果树、皂角树、黑枣树以及最后一排的几棵花椒树,因为它们关乎着我们的味蕾。
每年结果最多的是部长家院里的沙果树,伞一样的树冠几乎遮盖了他家一半的菜地,枝繁叶茂,每个树枝伸出若干树杈,每枝树杈又支出好几簇树茎,每簇树茎顶端都结三五个果子。从入伏天我们—群小伙伴就去树底下假装数果子,部长爱人早猜透我们的小心思,也就假装在密密的树叶中找哪个熟了,然后装作很费劲的样子摘下几个分给我们,看着我们被涩得吐舌头的囧样,她就在旁边念叨:“告诉你们不熟呢,就嘴馋,这下信了吧?”事实上,部长爱人很是和善,每到果子成熟时,她都会挨家挨户通知,示意各家的大人拿上自家的篮子去她家院子里摘果子。家属院的二十多户都能品尝到,孩子多的可以去摘好几次,直至吃到中秋节后初霜降临、树叶落尽。
每年春天,当大院里槐树半开花时,就有身姿敏捷的男同志身揣斧头爬上树砍下来硕大的枝条,女人和孩子们则搬上小板凳坐在树下,把将开未开的槐花撸进菜盆里,然后那几天的早饭和晚饭就都是槐花炒不烂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左侧的一棵皂角树,长得像龙爪槐,低矮的树干支起很粗的树枝,树枝的顶端长一圈叶子,叶质肥厚。开的花和青茎的颜色一样,不引人注意,结的皂角都在顶端,像槐角一样一串一串的,个头有三个槐角大,且皮质又厚又硬。我闲来无事时常爬上树坐在分枝的地方,把它的角一层一层剥开来,看哪一层能产生皂液,还拿剥开的切面在衣服上、手绢上搓,看有什么变化。甚至掰开舔它的汁液,观察切面的纹理。皂角的纤维又粗又硬,也不像豆角脆嫩,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皂角。但我在反复剥离皂角的过程中找到了专属于我的“美味”:掰开皂角,中间躺着五六颗青豆,再剥开青豆,在青豆的皮和内核中间有两片包住核的白膜,像凉粉一样透明洁净,咬在嘴里,像肉一样筋道.又有微微的回甘。这一发现拉近了我和皂角树的亲密度,奇怪的是,当我分享给其他小伙伴时,他们却不以为然。这正合我意,我独自守着和这棵皂角树的秘密,不再分享。后来搬离家属院后,我再没见过另外一棵让我倍感亲切的皂角树了。
记忆里武装部的菜园也是独有的风景。办公区对应的菜园和猪圈都归后勤科的灶房管。家属区的菜园就是各家屋前的空地,只要不影响大家通行,自己围栏划定即可。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这些菜园能满足大家除冬季储菜以外的日常食用。家属院住的是当地的平顶窑洞,大多是内外两间。每排三家共种一大块菜地,邻里关系很和谐,中间都不用木杆隔开,只是用田畦划分。浇地时把长五十米的软管一头固定在水龙头上,一头由人工引向每一畦,日间阳光充足,晚上水量灌饱,菜自然长得旺盛。西红柿、豆角、韭菜、茴香、大葱、黄瓜、茄子、洋姜等是大家普遍都种的。地边再围种一圈向日葵,足够我们看公演电影时嗑瓜子了。午休起来上学时顺便再去地里摘个黄瓜或西红柿,一路吃着走到学校,既美味可口又清爽下火。
武装部的花也很多。天然的野花有牵牛花、万寿菊、打碗花、小白菊、蒲公英等。采种的有木槿、蔷薇、鸡冠花、西番莲、满天星等。办公区的台阶下面种着一丛丛的“地雷花”,红的、紫的、白的、黄的、橙的……是我见过色彩最丰富的花种。之所以被叫作“地雷花”,是因为它花落后结的籽是黑的、硬的,形状像极了地雷。家属院里还有很多人种“指甲花”,爱美的女孩们把花摘下捣烂成泥,互相涂在指甲上,拿豆角叶子裹住捆紧,睡一觉起来指甲就染红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种花的学名叫海娜花,被广泛用作遮盖白发的天然染料。
武装部不仅景色很美,发生在这里的趣事也很多。我记得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军属,想多喂几只鸡补贴家用,苦于没有落窝孵蛋的母鸡,她就尝试把新鲜鸡蛋用旧棉袄包好,白天放灶洞旁,晚上放炕洞上,一闲下来就搂在怀中,最后竟成功孵出了六只小鸡!因此被大家称作“孵蛋妈妈”。还有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趣事。十来个小朋友捉迷藏,一队去藏,另一队捂住眼睛,等听到“藏好了”的声音再去找。当时已近黄昏,我迅速爬到菜地边的苹果树上紧紧贴住树干,静静地看他们一个个被找到,就剩我一个人,大家都一起找我,怎么也找不到。听着一家家的大人叫孩子们回家吃饭,天已经很黑了,再没人执意来找我,我也只好悻悻地回家了。在我看来自己取得了捉迷藏的绝对胜利,事后竟再没人提起,对游戏结果不了了之!现在想起来,或许是我太认真了。
武装部的军民共建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与当地的生产生活积极融合。正月十五闹元宵时,部队会一边派工作人员执勤,一边出军车和彩车与人们一起游行。春秋季的运动会,武装部会组队参加。还有乡村共建联系点,士兵们和当地老百姓一起劳动生活,麦收季节按政府统一安排参加抢收,处处体现军民鱼水隋。军属之间也非常融洽,我母亲跟一位山东老太太学会了做糖醋带鱼,跟当地居民学会了包竹针粽子,跟河南的大姐学会了用包装袋编篮子。我们这些小孩子则满院撒欢地玩耍,犄角旮旯都不放过。
上世纪80年代后,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武装部的人员也发生着很大变化。有部队转业举家调走的,有携家返乡的,还有新搬进来的。当时十来岁的我对这应接不暇的迎来送往很不理解。每天一起上学的同伴说走就走了,从河北保定回来的一家五口变成了新邻居……偶尔听大人们一起聊天说谁回到老家转业到什么单位了,我便用笔悄悄记下了通讯地址。当时,我和同伴刚学会写简单的书信,来回邮寄几次后也慢慢断掉了。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告别总是f肖无声息又刻骨铭心。
如今,我那魂牵梦萦的童年乐园已经变了模样,物是人非,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花以及那棵我心心念念的皂角树也不见了踪迹,但唯有那一抹军绿色成为我记忆中的底色,永远被珍藏、被铭记。
作者单位:长治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