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单亲母亲”的多重困境与救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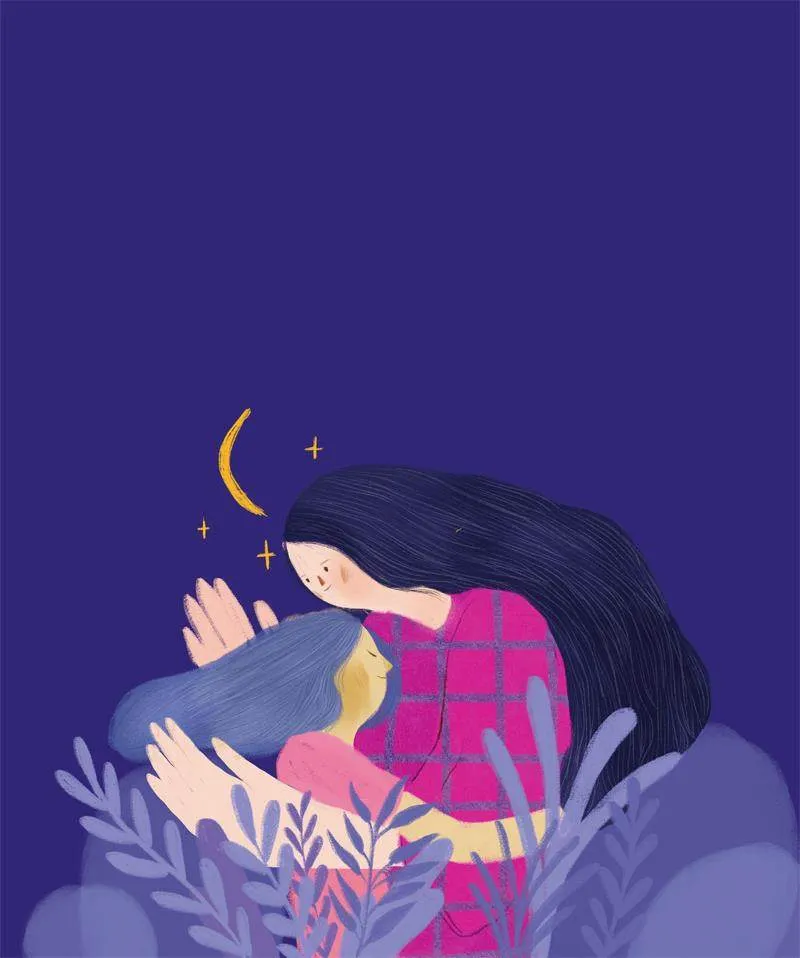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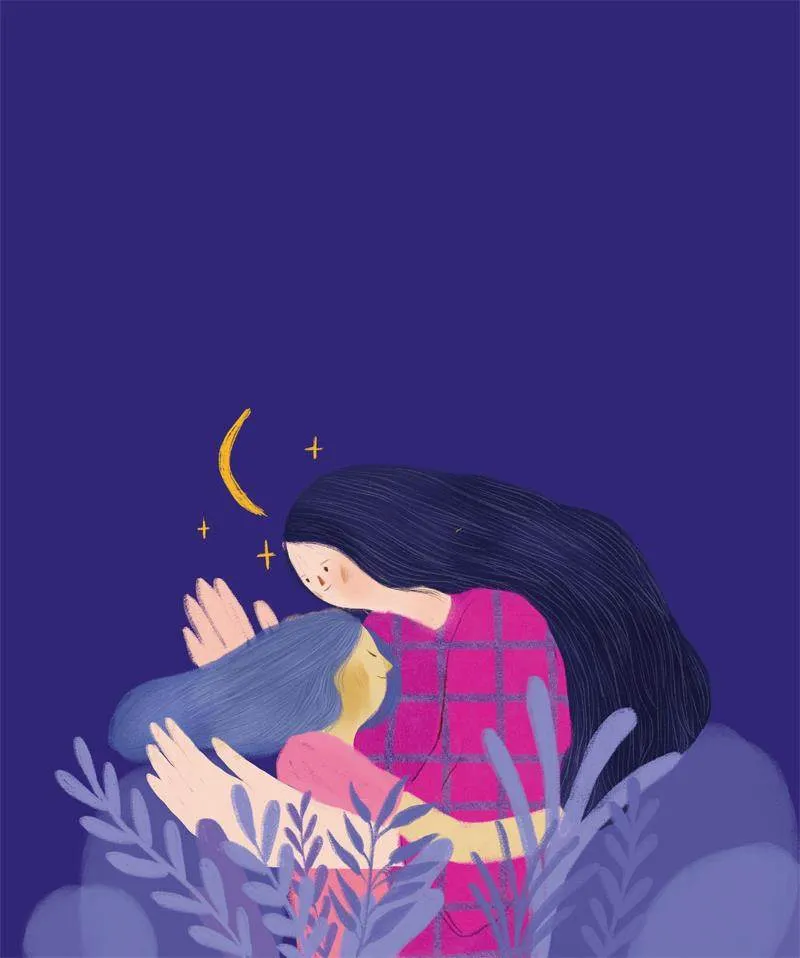
据2021年公开数据,我国单亲母亲数量超过3000万,其中83%是由女方抚养孩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100多对离婚夫妻进行追踪调查,发现离婚后5年内,男方再婚率高达80%以上,而女方只有22%。
而在这些数据之外,还隐藏着一个没有被统计进来的人群,那就是“事实单亲母亲”。这些人指的那些在法律上仍处于婚姻关系中,但因丈夫几乎没有承担任何家庭责任,实际上只能独自抚养孩子,挑起家庭的重担,又因种种原因没有收入,生活也因此陷入贫困的群体。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们发现,由于政策上的空白和认识上的不足,这种“事实单亲母亲”现象往往更为隐蔽,难以被外界察觉。往往是检察官在办理司法案件,深入实地走访调查时,才能真切了解到这些处于孤独角落中的母亲所承受的压力和艰辛。而在此之前,她们的婚姻大多处于不正常存续的状态中,丈夫可能长期实施家暴、在外组建家庭或犯罪入狱,孩子则成为她们无法解脱婚姻关系的羁绊,她们面临着诸多困境。
极大的经济压力和更为迫切的就业需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事实单亲母亲”可以看成是隐性单亲(父母中的一方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过程中,在家庭角色上有着事实性的缺失)的一种,不过它描述的是一种更为极端和迫切的情况。例如,父亲因犯罪入狱、在外组建新的家庭,或涉及家庭暴力、婚内强奸等严重问题,这种情形会使得夫妻婚姻处于不正常存续期间,父亲几乎完全不履行家庭责任,从而将养育子女的重担交给另一方。
由于“事实单亲母亲”们肩负着繁重的育儿工作,她们中的很多人往往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就业困难、晋升受阻以及不得不放弃职业追求等,这往往导致她们更容易陷于经济困境。根据《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需求调研报告》,单亲母亲家庭贫困化非常普遍。在被调查的单亲母亲中,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的占34.3%,月收入在2001元至4000元的占29.2%,这包括除抚养费以外的所有收入来源,如工资收入、奖金、福利以及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等。以一线城市低保标准来看,如果单亲母亲不能拿到孩子的抚养费,那么至少有25.6%的单亲母亲处于低保水平以下。因此,单亲妈妈群体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压力和更为迫切的就业需求。
此外,很多“事实单亲母亲”面临着家庭暴力、离婚困境以及抚养权等问题的重压,这让她们深感孤立无援。根据《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需求调研报告》的调查结果,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与辅导是单亲母亲最为迫切的社会服务需求之一,其中抚养权归属纠纷、财产分配、自我价值的受挫是这些母亲最大的困扰。
当然,孩子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城镇中25岁至34岁、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为79.7%,比同龄无子女的女性低10.9%,且有18.9%的在业母亲有时或经常为了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会。
当《方圆》记者在对各地检察院调查“事实单亲母亲”的现状时,很多检察官表示,他们往往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才会发现背后隐藏的“事实单亲母亲”的境遇。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抑郁和自杀倾向、抚养权和抚养费,是检察官们频频提到的关键词。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检察官何艳曾办理过一起未成年少女被猥亵案,小女孩在社区滑梯玩耍时,被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年人猥亵。案发时,因为母亲忙于工作,仅短暂地让小女孩独处,便发生了这种事。武汉市洪山区检察官易柔池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案子,一个小女孩在电梯里多次被小区的一名邻居猥亵。这位女孩的母亲是盲人且患有严重疾病,她经营着一家生意惨淡的盲人按摩店,家里主要靠低保维持生活。双亲育儿都会有疏忽的时候,更何况是忙于生计的“事实单亲母亲”。
两起案件相同点都是“缺位的父亲”。何艳记得,这起案件中的父亲,长时间都不跟家里联系,甚至从案件开庭到宣判都没出现一次。她感叹道:“自己的孩子被猥亵了,连出个面也不想。”而在何艳办理的另一起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中,被害人的父亲仅仅在问“对方能赔多少钱”时出现过一次,在确认对方无力赔偿后便再也没出现过。
多重困境
对于“事实单亲母亲”而言,生活上的困难仅仅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她们往往还面临着三重困境:维护权益难、获得支持难、申请保障难。
很多女性在正式离婚之前,可能已经长时间处于“事实单亲母亲”状态。由于离婚冷静期的存在和离婚诉讼流程的耗时性,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这些“事实单亲母亲”同单亲母亲一样,都得不到丈夫的支持。然而,由于其身份问题,她们在寻求民政补助(如申请低保、困境儿童援助)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障碍和困难。
浙江省安吉县检察院检察官李慧在对一起婚内强奸案的被害人苏拂晓进行司法救助的时候发现,在双方正式离婚前,苏拂晓是无法申领低保救助金的。因为根据民政部门相关规定,这段婚姻关系尚且存在,男方收入仍应纳入家庭收入之中,尽管男方在婚内从未尽过抚养孩子义务。


这仅是一个侧面。检察官们还提到另一种“事实单亲”的情形:男子因犯罪入狱,既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又拒绝离婚。而对另一方而言,除了面临生活与育儿上的双重压力外,她们还因其犯罪人员亲属的身份而遭受社会的标签化和污名化。
武汉市洪山区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他们在办理一些组织卖淫案、介绍卖淫案的时候发现,嫌疑人中有部分是“事实单亲母亲”,她们因价值观念偏差、经济困难等因素走上犯罪道路,甚至有的组织卖淫者、介绍卖淫者就是她们的“男友”。还有些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选择怀孕生子,最终面临刑罚时,这些孩子便成为亟待解决安置的社会难题。
地处沿海省份的一位检察官曾办理过一起案件,父亲因制毒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管母亲辛勤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可受其父亲的影响,他们相继走上犯罪道路,小儿子从小到大盗窃、聚众斗殴就没停过,最后进了监狱。这位检察官表示,办案的这些年来,她见过不少女孩年仅18岁却未婚生子,有的把孩子生下后就卖了或者遗弃了。这些年轻女孩本是受害者,但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性教育的缺失和社会救助的缺位,从受害者变成了犯罪者。
李慧从办案经历出发,进一步表示:“其实很多‘事实单亲母亲’在主观上会觉得维权这件事很难,她们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无论是打离婚官司还是争夺抚养权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这个事做不了也做不成,所以‘事实单亲母亲’们在主观上会有一个畏难的情绪。”离婚诉讼需要支付相应的诉讼费用,具备基础的法律知识。同时,离婚过程中往往涉及财产分配的问题,很多单亲母亲缺乏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检察院检察官曾办理过一起支持听障人士起诉离婚的案件。当事人小静幼时因重病失聪,由于家庭原因也没有接受特殊教育,她既没有掌握手语也不会健听人的语言。成年后,小静跟丈夫相亲结婚,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却频繁对她使用暴力,对孩子也漠不关心。多年的忍耐和默默承受,使小静的生活充满了痛苦。
小静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因为证据不足,法院没有支持她的诉求。第二次起诉,检察机关参与了进来,不仅帮助她顺利起诉离婚,还为她提供了一笔司法救助金。同时,检察官们也注意到,虽然小静走出了被家暴的阴影,但她和女儿的生活依然艰难。
原来,小静作为听障人士,在婚前本可以享有残疾人补助和低保。但婚后,由于丈夫的收入被计入家庭人均收入,她的低保被取消,这一状况延续到小静离婚后,她并不清楚自己该如何拿回这笔本属于自己的低保金。后来,在吴兴区检察院的努力下,小静的低保救助才恢复。该院还通过残联为她找了一家工厂打工,确保了母女俩的基本生活需求。
对于这些“事实单亲母亲”来说,最困难也是最难克服的一点是:她们很难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受“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认为照顾孩子是母亲的天职,并把母亲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如果单亲母亲没能照顾好孩子,可能会受到邻里和亲戚的歧视和污名化。同时,很多“事实单亲母亲”尤其是在农村的妇女,自身也受到传统思想的桎梏,认为“家丑不能外扬”“日子能过且过,为了孩子忍一忍”。
在李慧办理的一起救助“事实单亲母亲”的案子中,男方常年在外,从不履行抚养义务。可左邻右舍非但不认为他有问题,还觉得是女方“ 没有用,管不住自己的丈夫”。在办理苏拂晓案时,也有“这是夫妻间床头打架床尾和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它上升到一个刑事犯罪的高度去”的言论。
“事实单亲母亲”的存在往往具有隐蔽性。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有些女性在离婚前已经是事实上的“单亲母亲”了。也正是一些问题在离婚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才导致离婚后家庭陷入困境、孩子遭受侵害等情况的出现。如果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些“事实单亲母亲”的困境,或许她们的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司法救助联动社会救助
那么,检察机关能为这些“事实单亲母亲”做些什么?
2024年2月至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将持续深入推进司法救助工作,进一步兜牢民生底线;大力做好社会保险领域检察监督工作;深化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作为专项行动重点。在检察官们看来,很多“事实单亲母亲”之所以能被检察机关看到,往往因为她们是一些司法案件的当事人。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当遇到因案致贫、致困的当事人,可以结合她们受害的程度和家庭的困难程度,通过联合残联、妇联,同时县级、市级、省级检察院联动,扩大对“事实单亲母亲”的救助范围。
同时,针对“事实单亲母亲”维护权益难、获得支持难、申请保障难的问题,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对受家暴妇女支持起诉、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进行支持起诉、对未成年人追索抚养费未果支持起诉等方式来帮助她们。这样,不仅能给这些单亲母亲提供专业的法律援助,也是在为那些觉得“离婚难”的母亲“撑腰”。
例如,在吴兴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支持受家暴的听障妇女起诉离婚案中,检察院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的同时,更是联合了当地民政、法院建立了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有效加大了救助力度。
在检察官们看来,从一个全职母亲转变为一个单亲母亲,小静的生活肯定不会容易。作为一个听障人士,她在工厂里那份2000元的工作只能解一时之困,但母女俩的房子被前夫霸占,只能蜗居在工厂宿舍里,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她的生活会更加困难。目前,检察机关正在为小静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她要回自己的房子。
在办理有关事实单亲相关的案件时,往往避不开未成年人的问题。武汉市青山区检察官吴丹丹曾办理过一起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小闻出生后就被诊断为脑瘫,其父亲多年来从未尽过抚养义务,也从未承担任何医疗费用。案件线索移交到检察院的时候,夫妻双方已经协议离婚。根据离婚协议,小闻由母亲抚养,父亲因经济困难且有犯罪记录被免除了抚养费的支付义务。可随着小闻渐渐长大,医疗需求日益增加,没有工作的小闻母亲仅凭每月180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计,显得捉襟见肘。而小闻父亲却因为房屋拆迁获得一笔79万元的房屋征收补偿费。尽管小闻母亲多次要求前夫支付抚养费,但均遭到了拒绝。
检察机关在查阅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后发现,当子女因患病等原因,致使实际需要的生活费已超过原定协议的抚养费,母亲有权要求增加抚养费。据此,武汉市青山区检察院支持起诉,帮助小闻追索抚养费。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小闻父亲需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直到小闻年满18周岁时止。
可判决生效后,小闻的父亲因犯贩卖毒品罪再次入狱,小闻一家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青山区检察院在得知情况后,对小闻和其母亲展开了司法救助,为她们申报了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资金。
除了司法救助,是否能进一步保障小闻母亲的合法权益?吴丹丹注意到拆迁所得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建议并支持小闻的母亲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在检察机关的支持和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小闻的父亲需一次性向小闻母亲支付20万元。
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朱洁在办理案件中遇到了一个患有双情感障碍且有自杀倾向的少年小凌。他的父亲沉迷酗酒且有暴力倾向,经常对小凌拳打脚踢,致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当时的工作,每天到学校陪读。
朱洁说:“我们一开始只是针对这个儿童进行了救助,但后来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对孩子的救助只是暂时的。要解决孩子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得帮助他的母亲,因为是她在照顾这个孩子。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他的父亲每个月按时支付抚养费才行,因此我们开展了民事执行活动专项监督。”

对检察机关来说,司法救助联动社会救助或许是救助的关键。司法救助的目的,最初是给被害人一笔钱,而这只能让她们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李慧告诉《方圆》记者,她现在追求的不再是个案的解决,而是尽可能向她们提供长远的综合性帮助。比如,在救助苏拂晓一家时,李慧不仅帮他们申请到各种长期保障金,同时发现了“事实单亲母亲”在申领低保金上的盲点,并顺利帮他们申请到了低保救助。
同样地,在办理未成年人被猥亵案时,武汉市洪山区检察院考虑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住在同一个小区,当犯罪者出狱后,被害人小女孩今后的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组织召开“司法救助+社会帮扶”未成年人综合保护联席会,联合武汉市检察院、洪山区妇联、区教育局、区关工委、区公安分局等,开展“爱心妈妈”帮扶工作,同时定期关注被害人的生活、学习情况;做好安保预案,针对罪犯服刑结束后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动态管控,消除被害人的顾虑。
“检察机关的工作可能到这里就停止了,但社会救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将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才能真正帮助到那些困难母亲。为此,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和当地妇联建立了一个合作机制,如果检察机关收到了妇女处于困难状况的线索,可以移交给妇联,她们能为这些母亲提供一整套的职业培训,同时检察机关也和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签订协议,可以为这些母亲和她们的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
“事实单亲母亲”的困境并不是家内事,社会照护的缺乏、互助系统的缺失、社会福利的缺位……种种原因都造成了单亲母亲需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抚养孩子,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并最终陷入一个难以挣脱的死循环。所以,帮助“事实单亲母亲”脱离困境更需要全社会从照护体系、育儿政策到社会意识层面的提高。(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