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苏拂晓”,检察官的坚持与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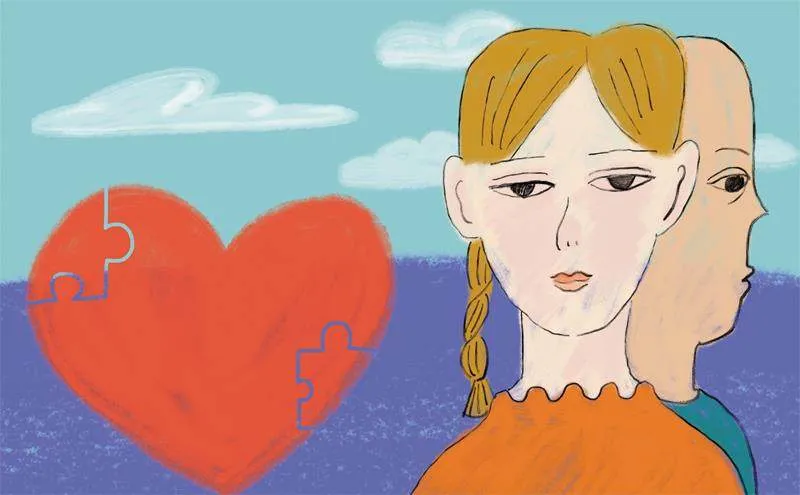

李慧说,当“事实单亲母亲”这个概念第一次在她心中萌芽的时候,她是抱着一股朴素的信念的,那就是希望这一群体的困境能在更广的意义上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如果丈夫一直不尽照顾抚养义务,导致妻子育儿负担增加,甚至生活困难时,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在单亲母亲、单亲父亲已变得常见的今天,“隐性单亲”“丧偶式育儿”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还有这样一群人,她们的困境更为严重与迫切,她们的声音更需要被听到。她们就是被浙江省安吉县检察官第六检察部主任李慧称为“事实单亲母亲”的群体。
这些母亲虽然在法律上仍处于婚姻关系中,但实际上却独自抚养孩子,挑起家庭的重担,且因种种原因没有收入,生活也因此陷入困境中。她们的婚姻大多处于不正常存续的状态中,丈夫可能长期实施家暴、在外组建家庭或犯罪入狱,孩子则成为她们无法解脱婚姻关系的羁绊。
为什么她们会被困在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里?为什么在一个家庭中,女性总是更多地承担和牺牲,而那些缺席的“丈夫”和“父亲”却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李慧的这一觉察源于其参与救助的一起婚内强奸案。在这之后,围绕“事实单亲母亲”的困境,一场更大范围的社会救助正在悄然发生。
一起婚内强奸案引发的思考
一切的开始要从2023年那个临近春节的冬天说起。
2023年1月,安吉县检察院检察官吴佩珏接手了一个案子。在离婚诉讼期间,男方把女方强奸了。男方叫许保南,是入赘到女方苏拂晓家里的。因两人的家庭条件都不算太好,在没有正式离婚前,两人只能将就着一同住在女方农村的祖宅里。苏拂晓和两个孩子睡里屋,许保南睡外屋。一天,在歹念的驱使下,许保南爬上了妻子的床并试图发生性关系。苏拂晓顽强抵抗了数十分钟后,叫喊声最终引起了小儿子的注意。在小儿子的拼命阻拦下,许保南才没有得逞。尽管如此,这次强奸未遂事件,还是给苏拂晓的隐私部位造成了长达1.nn4cjYp3wJ0a7CoB3nS4tw==5厘米的撕裂伤口。
随着办案的深入,检察官发现许保南曾经有过实施多次家庭暴力的历史——光是公安机关留存的报警记录就有8次;在两人打离婚官司期间,法院制发过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也出具过《家庭暴力告诫书》。
从时间线上来看,苏拂晓和许保南在2009年7月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因矛盾多次发生争吵,苏拂晓8次报警,公安机关向许保南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2年8月17日,苏拂晓向安吉县法院起诉离婚,12月9日,申请人身保护令。12月12日,安吉县法院民事裁定出具人身保护令。可不到一个月,许保南就再次伤害了苏拂晓。
吴佩珏觉得,如果这个案子不好好处理的话,很有可能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根据她多年的办案经验,在严重的家暴致残、致死案件发生以前,通常都会伴随着长期且多次的轻微家暴案件。这次许保南婚内强奸未遂,其实就是一种警示。

可又有一个难题摆在了吴佩珏的面前,应该给许保南定什么罪,定强奸罪吗?可在我国,婚内强奸是否入罪是个既难认定且有争议的问题。吴佩珏和检察官助理田径翻阅了过去几年的判例资料,发现仅有一起案例可供参考。此外,即便认定了强奸行为,但在事实夫妻关系中,暴力程度要达到什么情况才能达到构罪标准?
吴佩珏坚信一点,婚姻的合法性不等于性行为的合法性。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认定婚内强奸的关键是要看在实施具体性侵行为时,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是否处于正常的存续状态中。在这起案件中,两人的婚姻已经破裂,丈夫又有长期的家暴历史,所以不能仅凭一张结婚证就认为丈夫可不顾妻子意愿,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
在刚开始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吴佩珏的心中还有诸多的疑问和不确信。然而,随着深入了解和实地走访,这种不确信一点点消散,甚至成了一种使命感。田径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她记得第一次去苏拂晓家里走访的时候,检察官们都裹得严严实实,可苏拂晓的大女儿只单穿着一件毛线衣。苏拂晓所在的村子几年前已经翻新,可她的屋子砖瓦尽露,是全村最破旧的。田径觉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不去介入,不去帮助苏拂晓和她的孩子们,那么她的人生可能会不断重演相似的悲剧。
另一方面,田径对于婚内强奸具体判例之少也感到疑惑。苏拂晓的情况不会是个例,会不会是因为关于婚内强奸的判例“少而难”,所以让一些有着相似困境的女性无法被看见?或者是即便被看到了,也无法惩罚犯罪者?如果是这样的话,田径觉得或许能借由苏拂晓的这个案子,给其他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更多的内心确信。田径说,她希望当再次遇到这种妇女在婚姻不正常存续期间遭受非法侵害的情况时,检察官们可以更有底气地指控犯罪。
安吉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许保南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36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且归案后能自愿认罪认罚并获得了被害人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2023年4月28日,安吉县法院采纳了安吉县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许保南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
是特困母亲,也是“事实单亲母亲”
许保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和苏拂晓的离婚问题、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也需要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些并不是“一诉了之”就能解决的。因此,在办理婚内强奸案期间,安吉县检察院负责司法救助工作的检察官们参与了进来。
李慧是一位从事司法救助工作多年的女检察官,尽管在工作中见惯了因案致贫、致困的家庭,可苏拂晓和两个孩子的情况还是令她揪心——女儿许雨晴被诊断患有先天性的眼肌型重症肌无力,需要常年服药;儿子苏雨亮患有自闭症和多动症,需要常年照顾。可许保南不仅没有承担孩子的医药费,就连家里的日常开销,他从来没给过钱。因需要常年照顾儿子,苏拂晓无法通过工作获得收入。更难的是,她发现苏拂晓要想获得救助并不容易。这种困难,源于一种视角的缺失和对一类群体的忽视。
这个群体,被李慧称为“事实单亲母亲”,指的是在法律上仍处于婚姻关系中,但实际上因男方几乎没有承担任何家庭责任,只能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母亲”们。所谓缺失的视角,则源于因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不足,而造成的社会配套措施的不完善。此外,李慧还发现,像苏拂晓这样的“事实单亲母亲”几乎是无法申请低保或低保边缘户(以下简称“低边”)的救助的。
尽管苏拂晓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属于单亲特困母亲的标准,但由于苏拂晓和许保南尚未离婚,根据民政部门规定,许保南的收入也应纳入该户家庭总收入中,这导致算出来的人均收入高于国家规定的低保或低边救助标准,从而使得苏拂晓无法享受低保、低边等困难人群的政策性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困境儿童的补助是和低保、低边政策所挂钩的,如果无法认定为低保、低边家庭,那么苏拂晓的两个孩子也无法获得困境儿童补助。这对于家里有一个需要常年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和一个患有自闭症、多动症的儿童来说,是一种重创。
那么,检察官能为苏拂晓做什么?李慧了解到,根据民政部的社会救助规定,一个人在劳动年龄段内只要没有重病或重残的话,即使没有工作,也要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来计算个人收入。如果这个人的家中有重病或重残的人需要来照护的话,可以按照实际的收入而非最低收入来计算。在苏拂晓的案子里,因为她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符合重病或重残的JsctePZ8ZOYk/w01z7hnSynRy+r3qj5eMQ0F6w/gBFw=标准,同时她也没有工作,所以可以按照她的实际收入,也就是0来计算。也就是这样,苏拂晓可以从低保边缘户转到低保户,能拿到更高的救助金。
如此一来,通过尽快离婚便可以帮助苏拂晓尽快拿到救助金应急。在办理婚内强奸案期间,办案检察官们积极联系法院以及许保南的辩护人,向许保南释法说理,促成许保南和苏拂晓俩人达成离婚调解协议,并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时,他们要求许保南遵守取保候审规定,及时搬离苏拂晓的住所以避免再次引发冲突。

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苏拂晓和许保南于2023年3月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苏拂晓自愿谅解许保南,许保南则需要每月支付给苏拂晓1500元孩子抚养费。后来,当地民政部门依据社会救助相关规定为苏拂晓一家申请低保救助。此外,安吉县检察院联合了湖州市检察院、安吉县妇联一同为苏拂晓发放救助金。
2023年6月1日,苏拂晓的两个孩子开始享受困境儿童救助补贴,两个孩子每人每月1105元。同时,两个孩子都享受了校内营养餐费全免。苏雨亮因患有多动症、自闭症,于同年11月13日被评定为精神残疾四级,享受每月125元的残疾人补贴。2024年6月,因一直没有收到孩子抚养费,苏拂晓依法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要求许保南履行其应支付的抚养费义务。
当然,苏拂晓现在最烦心的还是孩子的读书问题。儿子苏雨亮在一次争吵中打了同学,学校便不让入校了,“除非保证他完全好转了”。但苏雨亮的症状并没有达到当地特殊学校的入学标准。这么一来,苏雨亮的上学问题陷入了两难境地。为此,检察院也联合了教育部门、民政、妇联、社工等相关方一同商讨解决办法。
救助的困境
有时候,贫困指的并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困顿,贫困更是一种身份、一种难以改变的生存状态。因为造成贫困的原因通常有很多,家暴、不幸的婚姻、患病的孩子……可有些更深的问题是躲不开的,比如信息的不对等、社会救助的难以覆盖、法律资源的缺失……这些都可能导致单亲母亲难以挣脱贫困的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在检察机关介入以前,苏拂晓几乎拿不到任何救助金。一是她不知道有哪些救助是可以申请的;二是她不知道要申请这些救助需要符合哪些条件;三是她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这些申请。
苏拂晓并不是李慧遇到的第一个“事实单亲母亲”。2022年,她从未检部门得知了一起案件线索。一对生活困难的农村母女,遇到种种现实问题。女子李小可跟她的丈夫常年两地分居,男方不愿意离婚,一直在外地,跟不同的女人生活着,不仅鲜少回家,也从不支付孩子抚养费。由于男方收入尚可,李小可一家便并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妇联和村委会只能将她们标记为困难家庭,并作为重点慰问对象,逢年过节送去一些慰问品。这样的状态持续了8年,直到检察机关的介入,母女俩才追索到了抚养费,拿到了一笔司法救助金,李小可也与前夫顺利离婚。
遗憾的是,这对母女没能申请到低保金。这件事一直像一根刺一样留在李慧的心里,直到再次遇到苏拂晓的案子,她才意识到,“事实单亲母亲”的困境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她们的难处一直没有被看到。
在办理这两起“事实单亲母亲”救助的案件以前,李慧并不知道原来申请低保是有诸多限制的。当地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杠杆的标准是硬的,符合标准才能给”。因为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各界针对因各种原因陷入生存困境的公民给予的财物接济和生活扶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是一种兜底制度。不管事实情况中丈夫有没有顾家、有没有给过抚养费,民政部门在审核时均以法律文书为准。只要婚姻关系依然存续,那么申请低保时就必须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一起申请,也必须计算家庭中所有劳动力的工资。
即便是离婚,问题也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根据相应的计算规则,民政部门在核算家庭人均收入时,会将离婚协议中规定的男方所需支付的抚养费纳入计算中。如果男方长期拒不支付抚养费,女方需将相应的法律文书经民主测评会确认,否则这笔“从未支付的抚养费”仍然会被纳入低保计算中,进而影响女方申请低保救助。并且,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的法律文书是有时间节点的,民政部每年都会对低保、低边户进行复核。也就是说,如果男方一直拒不支付抚养费,那么女方就得一直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有不断更新法律文书的时间,才能通过低保户的复核。这会耗费女方大量的心力。
有时候,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感到无奈。国家层面的救助终归是有限的,他们只能救助那些客观上短期无法脱困的人群,而像苏拂晓这样的“事实单亲母亲”,只能靠着其他的社会力量来进行救助了。

在2024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前,李慧去看望了苏拂晓和两个孩子。李慧在听苏拂晓讲述被家暴的往事时,她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事终究是有限的,“事实单亲母亲”的困境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仅靠检察机关的援助远远不够,要民政、妇联等单位参与进来,改进并制定相关的帮扶政策,同时各种社会力量也能参与进来,大家一同帮助她们改变目前的处境。
李慧说,当“事实单亲母亲”这个概念第一次在她心中萌芽的时候,她是抱着一股朴素的信念的,那就是希望这一群体的困境能在更广的意义上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如果丈夫一直不尽照顾抚养义务,导致妻子育儿负担增加,甚至生活困难时,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检察机关来说,肯定是有一个司法案件,我们才会去司法救助的。如果没有司法案件,那么检察机关也看不到‘事实单亲母亲’们,更别提去救助了。”
在司法案件以外,大量“事实单亲母亲”的困境没有被看到。就像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说:“大家救助的愿景都是美好的,但事实就是可能我们花了10分的力,但只能收到1分的成效。”提出“事实单亲母亲”仍旧是有意义的,因为“看见”总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什么才是好的救助
在个案救助后,检察官们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下一个“苏拂晓”出现时,如何在有限的职责范围内,尽全力帮助到这些身处困境中的“她”?苏拂晓案件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有没有预防的可能?
吴佩珏发现,在法院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后,苏拂晓仍多次遭受来自前夫的家庭暴力,而这一情况直到性侵案发生时,才被检察机关所了解到。可反家庭暴力法第32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居委会、村委会等为协助法院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体。公安机关的协助执行内容包括发现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将情况通报法院,法院根据情况对其处以训诫、罚款或司法拘留。若公安机关在处警中发现存在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情况但未及时通报,法院便难以掌握执行履行情况。
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检察官们发现对于很多农村的妇女来说,离婚难是她们心里的一大痛点。苏拂晓早在2022年9月就开始打离婚官司了,尽管她提供了男方多次家暴的报警记录,可直到检察机关介入时,她的离婚官司仍旧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因而,检察官们认为当遇到这样的案件时,法院应为他们的离婚诉讼开通一个绿色通道,在认定家暴情况属实后,尽早判离。
2023年8月31日,安吉县检察院、法院、教育局、公安局、司法局、卫生健康局和妇联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联动协作机制的建议》I1VYYIBtjaqozhFNP+rsmw==(以下简称《建议》)。《建议》中提出,需要建立涉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绿色通道,主动告知申请保护令的途径、检察院协助申请法律援助;同时,法院在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向当事人所在辖区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妇联送达。
在这份《建议》出来的两个月后,安吉县检察院向安吉县公安局制发了一份检察建议书,建议一是加强部门联动,因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一项社会性的工程;二是加强数字赋能,加强各部门之间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信息互通共享;三是增加在乡镇基层的重点防护,对已经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家庭进行重点走访。
在这份检察建议书的开头,吴佩珏如此写道:“本院在办理许保南涉嫌强奸案中,发现你局在涉家庭暴力投诉、求助时,转介处置工作未履行到位,需引起重视。本院在办理许保南婚内强奸案时发现,该案为离婚诉讼期间的强制性行为引发,且被害人苏拂晓曾有过多次被家暴的报警记录,在二人离婚诉讼期间,法院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此后许保南仍然存在暴力威胁行为,公安机关在处警后未将该情况通报法院,法院无法实现时刻跟踪掌握被申请人的履行情况,使人身安全保护令未落到实处,给后来‘民转刑’案件的发生留下隐患。”这意味着,未来如果还有下一个“苏拂晓”的出现,公安机关能及时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情况通报给法院,第一时间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这份检察建议书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苏拂晓的这起刑事个案如同投石入湖,引起了安吉全县各部门在反家暴工作上的震荡。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当越来越多的基层检察院在类似的案件中发现相似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解决办法,涉家暴类案件将会处理得更好。
安吉县检察院的做法并非个例。自从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全国各地的基层检察院都在积极探索一条参与治理反家暴工作的道路。自2022年3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同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专项活动;2023年12月,最高检提出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在12309检察服务大厅设置“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专用接待窗口,对于涉及侵犯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妇女平等就业等控告申诉案件要优先接收、优先移送、优先办理。李慧觉得苏拂晓正是这个专项活动的受益者,因为帮助困难妇女,仅靠经济援助只能解一时之急,更重要的是,要与她们站在一起,去共情她们的真实困境。(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