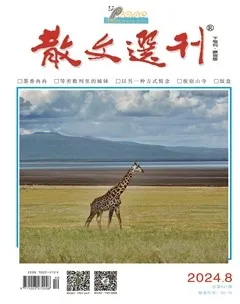已远的水乡排影

朋友送我一条挺大的“螺丝青”鱼,我不忍心吃,想起霞住在水岸边,就驾车沿龙泉溪下游开去。
霞与我已经多年没有见面,知道了我的来意,她放下手上的活儿来陪我。阳光下,水波潋滟,湖光倒影;岸处水草葱绿,微风徐来,一圈圈儿水纹荡漾;小舟叶叶漂浮水面,一幅江南水乡,如梦如幻,甚是惬意。霞说,眼前水域,曾经是排工们扎排下水的地方。
向一处码头走去,在高耸的“争当排头兵,甘做航标灯”字样下面,我想起路标上的“码头”与“渡口”,好奇地问霞,两者有什么不同?霞说:“码头是排筏与船停靠,或者上、下船的地方;渡口则是包括从此岸与彼岸的那片水域。”我笑着点点头。说着来到水边,一个个铁环桩排列着,铁绳连着水面上一条条小木船。我把鱼小心地从储物箱里抱出来,放进水浅处,它似有灵性,不愿离去,我伸手摸摸它的头,它才摇摇尾巴走了。
坐在码头的高处,我们几乎都没有说话,有一种情绪围绕着我,慢慢散开。凝眸远望,青山翠岭尽收眼底,屏息聆听,水声细细碎碎,清澈,宁静,慢慢悠悠流向远方。朦胧中,我仿佛看到一条条木排筏从这里出发,岸上是送行的亲人——母亲、儿女、妻子,挥手告别。这一刻,时间好像在倒流,历史上排帮出航的情景,在这蓝天白云的码头上,若隐若现、重重叠叠。
霞的老房子在码头对面山边,村名叫沙埠头。她邀我吃饭,路上跟我说起村子的变迁。说到放排的细节,霞知道得不多,在紧水滩水库造好之前,她爱人跟着她舅舅放排,已从徒弟成长为一个独立放排人。我有点儿期待,想知道更多当年这里放排人的生活。
到了她家,霞说:“说说你年轻时候放排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吧,我同学喜欢听。”说着自己去厨房了。
霞的爱人六十岁左右,淳厚朴实,脸上写着岁月的沧桑,当我问起放排的那些事情,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也许那段经历早已经融入他的生命里:“我们是在江中运送原木的人,排运是当时最经济适用的运输方法。”他沉浸在回忆里,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瓯江上游森林资源丰富,早年林区销往沿海各地的木材毛竹,都是扎成排筏顺流放远的。每一次发排前,舅舅去办理相应的手续,等齐全后,木材运到岸边水运站就开始扎排,这非常讲究,排扎得好就意味着此行能顺顺利利。
他给我描绘木排的结构:排头宽一米二,排尾尖,排中间最宽处八米左右,一般一节八米、一共九节,它的形状有点儿像古时村民的草鞋。先扎排头,两边延长二米,为下一节排做好包围,再用排柴和排钉固定,以此类推。节与节之间用竹篾索连接,排的正中间从头到尾用大竹篾索牵引。排上配备竹撑篙,篙长八米当动力,排头装排梢,把握这古老“航母”的方向。排帮中间一条排上搭伙凉棚,宽二米,长六米,供放排人休息和用餐,排上带米和腌肉咸菜等,沿途路过村庄亦可买点儿蔬菜之类。出排的时间,要看江水的深浅与天气情况,水路边设有联防组,负责水运安全、提供水路信息等。每次出航,舅舅都是头排,我们跟随其后,浩浩荡荡,六条排一组,也可以多些,原则上一排一人,也有师徒二人的。踏浪而行,排工像最原始的“航母”舵手。在江河里航行也很惊险,遇到险滩或者深潭,整个身体都是倾斜在排外的水面上,此时撑篙前行,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智慧。如遇排被撞散,木头被沿路村人抢走,按规矩必须拿部分钱象征性地赎回。可惜,1985 年,紧水滩大坝蓄水,木材陆地运输开放,放排这个古老的职业也就在此消失了。
霞走进来,饭菜的香味也随着她风一样的性格带了进来。我问起他们夫妻俩的生活,霞露出幸福的表情:“乡下就是偏僻点儿,其他都好,现在儿女在城市工作,三十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我衷心祝福他们,在这“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地方能长命百岁,活成一对神仙眷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