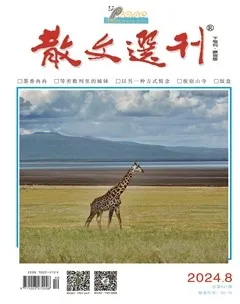赶花朝
花朝节前夕,我们慕名来访。不为别的,只为这延续近900 年的花朝节,在旧街这方僻壤的小镇,如何能经久不衰?
听过一次摄影讲座,一名摄影记者镜头里40 年的旧街花朝节。从80 年代,到2023年,那名摄影记者,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愣头青,熬成了一名退休的老人。他镜头里的花朝节,从黑白变成了彩色。主会场上的戏台,从简易到华丽。台下看戏的人,由毡帽,到草帽,再到崭新的草帽,直至花花绿绿的布帽。交通工具由“11 路车”变成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三庙河上的交通设施,由石礅子变成竹跳板,进而变成宽阔的大桥。商贩们兜售的商品,也从耕牛到小轿车再到楼盘……仅仅40 年,可以写出一部长长的花朝节变迁史。只是,唯一不变的,是那三庙河上上下下摩肩接踵的人。桥被挤垮了,人被挤得架起来了,这不是夸张的手法,这是纯纯的写实。
还是那名记者,有一年,他来了,只拍了一张照片就走了。那次拍的,是涨水后的三庙河把商贩们的摊棚淹了。按照惯例,旧街花朝节的物资交流活动,一般都在三庙河的河滩上进行。他把这张照片发到报纸上,取的标题是:《旧街花朝节“泡汤了”!》他不知道的是,那次“泡汤”的花朝节,其实还是继续进行了。只不过,商贩们把摊棚从河滩移到了河堤上而已。
“花朝节么样会‘泡汤’呢?”82 岁的左爹爹说,客早在一个月前就接了,货物也准备了差不多一年,就等这几天!
是的,旧街花朝节起源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迄今已有800 余年的历史,节期为农历二月十五前后几日,是鄂东一带最大的民间赶集大会,已被列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旧街人赶花朝节是要接客的,从前不仅车马慢,普通人家根本没有车马,电话更是没得。从正月开始,一家老小分头跑,大家靠着一双脚,不管山路水路,不管远亲近戚,一家也不能疏忽,人人都要接到:二月十五花朝日,接您一家人,哈到旧街来看花朝哈!花朝节没有接的客,那就表示这门亲戚要淡散了。
过年的鸡鸭鱼肉都要存着,留到花朝节待客。柴、米、油要提前准备充足,毕竟花朝节前后几天,旧街每户人家都要席开数桌。还有亲戚带亲戚来,吃完才认识的人也有。越是这样,越不能怠慢,顾的既是主人的面子,卖的更是亲戚的人情。
大戏唱几天,就要留客住几天。新晒的稻草铺在地上打地铺,客人不会嫌弃礼数不周。只是来客太多,铺盖被褥不够,着实让主人家又喜又愁。自家的不够,只好管住客不多的邻居借。好在大家都晓得,今年你家借我屋的,明年说不定我家就要借你屋的,自然没有不借的道理!只是年下新棉出来后,主人家又多了一项筹谋:一定要多弹几床新棉絮,免得明年花朝节再着慌!
住在大雾山深处的王老爹,每年就指着花朝节这几天,把老屋房梁上的横条拆一根下来,扛到花朝节上换一个好价钱,够几双儿女开学报名的费用。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各家儿女虽多,但旧街人尚学的风气却盛,拆屋卖房也要供子女上学。讲这段故事的王先生记得很清楚,家里原来是两间老屋,父亲就是这样一点儿一点儿拆掉了一间屋,供他们兄弟姐妹9 人长大成人、走出大山。
曾经,花朝节上的一景,是白刃闪光的犁耙,是排如士兵的靠背椅,是堆成小山的饭甑,是神气活现的水车,是红漆描金的摇篮,也是扛满那些老父亲肩头的扫把、草绳和帽箍……这些,是他们在无数个雨天、黑夜的农闲时节,编着、扎着、刨着、锯着……一点一点攒下的,是他们一年的指望。他们,有些是旧街本地的人,也有从红安、麻城、罗田、英山等外县,或是从河南、安徽、江西等外省,拉着板车凭脚力远道赶来的。所以,花朝节,用远景镜头来看,是花团锦簇的盛会,用特写镜头去推近,是无数人谋生谋爱的日子。
我对花朝节的印象,是13 岁那年的春天。在红旗中学二楼最西边那间教室,我那位黑长发白皮肤又多愁善感的漂亮女同学,站在破旧的窗前看着窗外烂漫的油菜花,笑意挤弯了眼角,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油菜花开了,花朝节要来了,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我的表哥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旧街的花朝节,而对于她那番偷偷诉诸我的话,我是多年以后才恍然大悟的:那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花朝节于她,是一种关于爱情的意象!
“树发芽,草返青,花朝赶集去相亲。”这是流传于鄂东地区的乡村小调。早春二月,麦苗青、菜花黄,戏台上,上演着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戏台下,桃红柳绿,蝶戏蜂闹,可不正是春心萌动的时候?有多少人,借着花朝赶集去见了心上人,又有多少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掩护下拉了爱人的手?爱情,与百花的生日一起发生,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遗憾都可原谅!
又到花朝节。只要生活在继续,期盼有新需求,旧街的花朝节就不会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