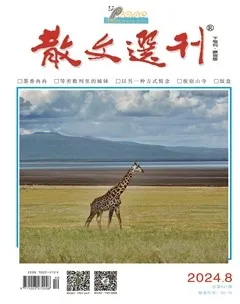祖屋记事
祖屋是一座二进二出的府第式建筑,左边还有一排偏房,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偏房一样,它有着自己的功能。进门后,院子里有两棵橘树,到了橘树挂满果实的日子,孩子们无不垂涎三尺。堂叔说,这两棵橘树是三爷爷种的。
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年代,院子成为我们童年里最好的去处。它有高大的围墙,将外界隔开,把四角天空吐露出来。尽管很早以前就知道“坐井观天”这个成语,然而在这座宅院里,人们所受到的教育也不相同,可大家的知识并不浅薄。无数个夏日,深居于此的亲人们坐在橘树下乘凉闲聊,而我们这些孩子,则围在五爷爷身边,听他讲故事,那些故事是怎么来的,无从知晓,只知道他年轻时闯荡江湖,街头卖艺。五爷爷从小跟我的曾祖父雷大山学过武术,也在余田鉴湖书院念过几年书,能文能武,阅历丰富,更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会讲《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也会讲《三国演义》里的纷争谋略。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聊斋》里的鬼狐故事。那些鬼狐妖精,让我有种“失控”的感觉——越害怕,越想听,越听越没法过瘾。就是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一日日滋养了我童年的乐趣。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那个穿越而来的蒲松龄,要不然他何以这么会讲故事呢?
五爷爷不会白白给我们讲故事,有时要我们给他捶捶背,有时要我们给他扇扇风;只要我们的小手停下来,他的故事也会停下来。不过,就算扇整整一个晚上,就算我们的小手像螃蟹的钳子折断了,那也是值得的。
一百二十多年前,在营造这座宅院时,曾祖父就不忘以农为本,耕读传家。为了突出他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他在农具的摆放位置上作了深刻的思考。从正门走进祖屋,首先看到的便是上厅,农具就摆放于此,为的是取用方便。随着家族繁衍,人丁兴旺,陆续又分出了一些新家。上厅和下厅,隔着一层砖墙和一个天井,天井很大,雨水落到天井里,顺着排水的暗沟流向外面的池塘。天井中间,放着一个很大的水缸,二爷爷时常在水缸里种荷花。荷花开的时候,祖屋就鲜活起来。二爷爷名叫雷翰,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桂阳早期的共产党员,也是著名的中医专家。1922 年,他与同学雷崇周、匡黎光等人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省立三师”)。在学校里,二爷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桂阳县农民运动的骨干。1927 年3 月的一天,他与雷崇周、匡黎光在祖屋院子里秘密商议,建立了一支30 多人的农民自卫队。4 月,他们三人组织农军数千人,配合国民革命军陈嘉佑部的一个营,兵分两路,一路经东河区的何家村、陈家村;一路经丰家圩、史家桥,到飞仙桥捣毁西河团防局,成功缴获一批武器,促进了桂阳农民运动的发展。因此,这座祖屋留下了桂阳历史的红色记忆。特殊时期,二爷爷受到冲击,他返回祖屋,在天井的水缸里种荷花,以清白明志,是有隐喻的。每当六月荷花盛开的时间,二爷爷便常吟诵“六月天气热,正是品荷时”。二爷爷的住房紧挨着天井边,每当下雨天,雨水从瓦楞上滴滴答答落下,那声音宛若音乐。此时,二爷爷在房间里写些旧体诗词,念给晚辈们听。一次,我父亲听二爷爷吟出这句“六月天气热,正是品荷时”,便问:“二伯,这句诗是品荷,而不是赏荷呢?”二爷爷答道:“品荷是一种雅趣,赏荷是一种情趣。”我父亲听后,似懂非懂。多年后,我父亲跳出农门,在县城工作,才渐渐懂得了当时二爷爷的心境。下厅比较小,也摆着饭桌,但比较阴郁。因为下厅的后面是阁楼。从我记事起,阁楼就是个可怕的地方。里面放着几口棺材和一堆干稻草,那棺材是给家族的老人准备的,油了黑漆,发亮。传闻阁楼上闹鬼,但我不知道闹什么鬼,心里感觉害怕。过年时,家族里都要用大陶缸酿水酒,酿好水酒的陶缸都会藏在阁楼里,而里面收纳的干稻草,正是覆盖陶缸之用。虽然陶缸口被稻草覆盖了,但水酒缓慢发酵时弥散出来的甜味,有着非凡的诱惑,我闻到后忍不住口水直流。有天下午,看家里人都干活儿去了,我偷偷溜进了阁楼,也仅仅偷喝了两杯,腿脚竟然不听使唤了,眼睛一片模糊,脑袋晕乎乎的,什么事儿也想不起来了。
家里人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发现我不见了。奶奶哭天喊地,大家四处寻找。后来,三爷爷到阁楼打水酒,发现我睡在干稻草上,背我下了阁楼,大家才转悲为喜。
上厅和下厅都有通向偏房的门和过道。偏房有八个房屋,分四个睡房和四个小厨房。我奶奶的厨房和二奶奶家的是挨在一起的。那个年月,大家的日子过得清苦,菜没有油,肚子很容易饿,不停地“咕噜咕噜”叫。要是闻到炸猪油的香味,口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一次,二奶奶在厨房炸猪油,我就躲在她家的厨房角落里,贪婪地呼吸着猪油的香味。二奶奶发现了瘦弱的我,她拿了一个小碗,装了半碗猪油渣,微笑说:“明崽呀,我的乖孙子,吃吧!”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半碗猪油渣的味道,这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部分,脉脉亲情,温暖地陪伴着我。后来,我身在遥远的东莞,只要在街巷里闻到一股油渣味,都会情不自禁停下脚步,仔细嗅嗅,试图从中嗅出童年的味道。二奶奶是祖屋里对我最好的长辈。其实,祖屋里的伯叔们尽管也会有矛盾,甚至是打架,但毕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矛盾化解后,也会相互照应着。谁家杀猪或者做好吃的,每家都会分到一些;谁家断粮了,也会互相接济着。因此,即便再窘迫,再寒冷,也总有温情和暖意不时在祖屋内迂回荡漾。
祖屋留给我的也有死亡的记忆,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伤痛,大伯就是在祖屋下厅的偏房里去世的。大伯走时,还不到四十岁。一个夏天的晚上,大伯不知患了什么怪病,在床上大口大口喘气,他长时间注视着我,让我感到无比害怕。那眼眶里流出浑浊的泪水,对亲人似乎有许多不舍。没过多久,大伯就咽气了。我一阵惊叫,大家闻声都赶了过来,大伯母失声痛哭,整个家族开始操办大伯的丧事。在故乡,死亡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大伯出殡前,我一直没有哭。直到下葬后,我独自来到舂陵江边,对着呜咽的江水,号啕大哭。那时,我才真正感觉大伯已经永远离我而去。
一次回乡,我带着鹏儿去看祖屋,站在我出生的那间破房屋门口,酸楚的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