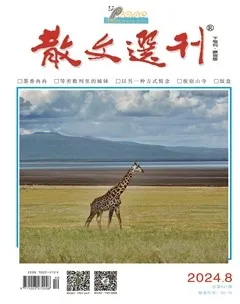我的静夜思
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第一张书桌却安放在我的大腿上。真是奇特!
这年中秋节,赏完月,我爹让我先上楼睡,他便去收拾搅拌草料,等我家的牛嚼吃了一会儿才离开。上楼的时候,我没睡着,听他轻手轻脚,恐怕是不想惊醒了我。我侧身望着,问:“爹,食喂好了?”
爹说:“嗯,它吃着,我顺势捋了捋牛毛。你咋还没睡着?”
我说:“爹,你看月亮都照进房里了,睡不着。”
爹脱掉汗袜子,往旁边的木板凳上一搭,坐在了我的脚头,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说:“月白霜清,秋夜明静。你看房外的月亮钻进我们的二楼里来了!”
这时,我也坐起来,细细一瞅,这木板楼上亮堂堂的。但不知道该怎么表示幼童娇嫩的心理,只是连连地说,爹,亮,就是亮,楼里房外一样的亮。
爹“嗯”了一声。我刚把薄床单盖在身上,爹说:“你把腿伸直,我教你背一首诗。”于是,嘴里一直念叨着,手指就在我的大腿上写,念一句,写一句。我也复念一句,在爹的大腿上复写一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补充说,“这是唐朝诗人李白的佳作《静夜思》。背会了吗?”
我更没了瞌睡,勇敢而又胆怯地说,能的,试试吧!这一表示不要紧,爹又给我加了码:“你能不能模仿《静夜思》作一首诗,明天晚上,念给我听!”
爹这么一说,我没敢推辞,便硬气地答应了,我一定好好地想!
爹这时候睡在床上,自个儿背起诗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我一听到“竹喧”和“莲动”,就联想到我家房后的大片竹林和里沟里的莲花池,就问这是啥意思?爹高兴地说,竹林里传来了洗衣女娃们回家的歌声或笑声,莲叶漂浮被小船轻犁分开,诗意浓烈。
我似懂非懂,只是“噢噢”了几声。
过了一会儿,爹悠然神往地又吟了一首: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接着又说,这诗有生活情趣,说理很强。
我问,“天心”在何处?
爹解释道,在天空中,就是天的中央。
对于我来说,简直是艰涩难懂,听起来腾云驾雾,不知所云。后来,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才知,前者是唐朝王维的诗《山居秋暝》,后者是宋朝理学家邵雍的诗《清夜吟》,更悟出些其意境的奥妙!那天的晚上,月光是明亮的,对我的诗的启蒙来说实在是朦胧的。但是,对爹的印象确实也是清晰不过的。所以,我在这天夜里的静夜思唯一想到的、看到的是我的一直追寻的父亲的勤奋、劳苦的身影。
从我记事起,父亲在种地的空闲时间里,常常翻那一口用竹篾编做的陈旧的竹箱子,不知道在里边珍藏了什么宝贝。有一次,我悄悄地跟在他屁股后边,蹬在小凳子上往里瞅,惊讶了,这箱子装着旧书。我当时想,这应是父亲的喜爱之物,难怪不让我随便乱翻。他还说,现在你还“咬不动”,等长大了,它就是你上楼的木梯子,没有它,俺们咋能上楼睡觉呢!是的,我虽然看不懂,但我的确意识到,父亲唱的,吟的,哼的那些诗文,肯定是从那里边掏出来的。
借用这种情趣解除和驱逐一天天犁地、耕种、薅草等活儿带来的疲劳和困倦。我小小的年纪,也只能是眼气罢了。
第二天晚上,月亮依然明亮,村野依旧静谧。父亲带我上楼按原位置躺定后,问,仿《静夜思》想好了吗?
我满怀信心地说,想好了。于是一边念着,一边在父亲的小腿肚子上写起来:床前月走窗,疑是油灯亮。举头念乡亲,低头写诗章。就这样,行不?
父亲没有及时表态,过了半会儿,既没赞扬,又没有指责,只温和地说,就是太仿了,要实在点儿,要含蓄点儿,太直太白都不行。
我问,啥叫含蓄?
父亲说,就是你要表达意思,不要显露出来,隐藏诗句里,让人家品味道,像品菜尝酒那样。
这解释还是使我无法理解,不知所云,只好连声道,嗯!嗯!嗯!
这时,父亲用商量的口气说,娃子,我给你改一下,或许要好一些。于是,他就念出了声:月兔爬南窗,细察北楼亮。指法画腿肚,夜作写诗章。题目叫《同是静夜思》。
我听了以后,虽然完全不了解甚意,但觉得很有滋味,不像我在那诗句里死搬硬套,而是耳目一新,鲜明亮堂。说实在的,我当时心里有所思动,可怎么折腾,总是讲不出个道道儿来。
父亲大概觉着我的难堪,便改变了口气:“实际上,你想的诗句还是蛮好的。不过,将来的话,就如同我们上楼爬梯子一样,你会走一步上一步,步步高。睡吧,明天还要起早犁地呢!”渐渐地,我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亮了。而父亲肩扛木犁,挥着草鞭,吆喝着小黄牛早上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