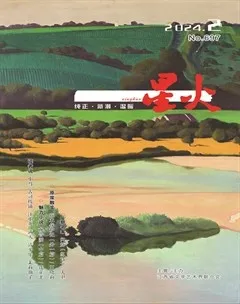迷途

1
汽车很早就奔走在平原的小路上。它们将安静的土地搅动得烟尘四起。人们一早并不在意速度这个词语。农民忙碌着农业,他们自己也像植物一样静默地生长。路对于村庄而言止于村口。长满野草的路口,是开端也是某种界限。人和狗都明白这种界限。然而人并没有狗执着。狗虽然用狂吠将自己的领地标识得很清楚,但它们出了自己心理的界限就变得胆怯—日后看来,胆怯是一种好事情。
关于踞守村庄,人们有一种显得卑微的说法:家门口蜷蜷。他们自况是虫豸。但不知道是谁带来了外面的消息。他们发现在等待草木生长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因此更多的办法到来了。首先是离开的办法。步行或者乘船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想象力。他们从学会驾驭拖拉机开始,狂奔在土灰漫天的路上。拖拉机本来是在村庄里四周打转的。它们只是比牛马结实,并没有走过什么遥远的路。后来它们被套上了车斗,装运的不只是粮食,更有像粮食一样倔强的人。从此机器有了表情,它们学会了盼望与出走,变得焦躁与不安。
本来安于土地守望的人,一旦学会奔跑与寻找,脚窝就会显得笨拙而可笑。一个人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情绪里就会产生幻觉或者危险意识。我这样说拖拉机事实上是不公允的。它曾经给过我很多帮助。我第一次离开村庄去东北乡的学校念书就是坐二姑父的拖拉机。后来母亲病重,也是坐在车斗中的穰草里奔到了外乡的医院。后来那辆拖拉机被淘汰了,就剩下一堆残骸立在路边。我有时候会伸手摸摸,似乎还能感受到一些温度。其实那种温度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许多年后感觉还是那么真实。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明白我说的那些古怪的话。较之这些生锈的废铁,她更关心水岸边的草木。
后来人们对拖拉机的速度不再满意,一种更为便捷的农用三轮车出现在乡村道路上。其时村口以外的公路逐渐变得宽阔,但颠簸依旧连接着村庄和城镇。这种叫“龙马”的车子装满了村民,车棚的后入口装扎满了自行车。捆绑的绳子构成一种艰难而可怖的意境。在抵达终点之前,人被囚禁在幽暗拥挤的空间里。厚实而阴冷的油布像是包裹着秘密与屈辱。就如人们在试图逃脱的旅程中钻进新的绝境。很少有人发出抱怨,他们的呼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宿命般的艰难气味。直到城市的中转地,自行车才被松绑,这样人们就可以骑车在街头寻找生计。从此人们更加热衷于离开村庄。车祸的消息时常传来,有些车辆甚至冲进路边的河里遭遇灭顶之灾。但从司乘人员收钱的兴奋来看,人们进城的决心无比坚定。那些沾满油污的钞票,成为人们迅速进入城市的入场券。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始终坚信“要得富,先修路”。这本来是一句响亮的口号。后来它几乎成为一种魔咒。无数的热情和体力投入到这句顺口溜般的狡黠话语中。没有人论证过它的真伪。似乎平原上从来就没有过道路,而进城才是唯一的出路。那些平时在家里摔碗骂娘的爷们,宁愿舍下村庄里的尊严与自在不顾,去做城里人眼中的“农民工”。农民工很尴尬,他们既不再是土地上的农民,也不能成为街市里真正的工人。但他们进入城市的速度和决心不断生长。这可能也因为新的车子出现在了村头。中巴在村头风尘仆仆,它们比以前的车子更加焦躁。那背着包的售票员就像是唤叫牲畜一样,将等待的人们推挤进人满为患的车厢。司机极不情愿地跳下车来,将一边的自行车挂在车后的铁架上。这些自行车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车上的一种特别意象。有了它人们在城市里就更加便利与自信。
村庄的小路与汽车的行道一下子变成冷漠的垂直关系。它们之间形成一种瞬间转换的角度,像是决裂与背叛—然而这可能不再是出路,也难以成为归路。
兔林子就死在这个路口。他属兔,身形走路也都像活蹦乱跳的兔子,两条短腿走得地上生烟。他的手巧,会编制各种柳具。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一种平柳,剪成寸段插在河岸边,秋末就能收割平直的柳条。他用这些柳条编织各种用具去集市上卖钱。他的一双儿女一聋一哑。他总是在编东西的时候反复地说:“我这好手好脚要是给子孙就好了。”柳具的生意并不怎么如人意,也可能是他编的东西太结实耐用。他家里挂满带着草木清芬的器具。
我是在城里听说了他被车撞死的消息。父亲在电话里似乎仍然心有余悸。他在描述着自己听说的各种细节。之前村里鲜有人被车撞死过。他们大多数是平庸地老病而死。固守村庄的他们连飞来横祸的机会似乎都是少有的。他们对自己的村庄了如指掌,最危险的只是饥饿和贫穷而已。人们对于大路和车辆的热情突然减少了,好像宽阔的道路上一下子生出无限的危机。这就是我们农民的情绪特征—深爱或者痛恨会像天气一样瞬息万变。或者说他们并不擅长爱恨,最终成为无奈的受害者。本来他们像是被绑在班车上的自行车,坚定地认为去城里的路是好路子。那些司机在勒绳子的时候咬紧了牙关,脸上露出狰狞的野蛮与迫切。
那自行车就像某种隐喻,被勒住脖子一样无法呼吸。
2
自行车在城乡之间的游动中也逐渐地苍老。在它们有机会进城之前,本在村庄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人们稍有空闲就会擦车上油。人们花在打理车子的时间似乎比骑车更多。自从人和自行车一起随着车子进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农村人到了城市里满眼的新奇,尽管他们的面色上满是不屑,然而这正是某种不自信。自行车和人一样,到了城里就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它们就变得慌张起来。其实城市才是自行车的故乡。彼时城市里除了品牌的专卖店之外,还有一种“车行”。这里既是修车的,也是调剂二手车的。许多人到车行里来挑一辆自行车回乡村去。破旧的自行车在城里面像个游手好闲的破落户,但到了乡村他们在城市的“劣迹”被忘却了,摇身一变成了“半新旧”的好车。那时候人们真会安慰自己,发明这个词语为一辆自行车寻找到尊严。其实这点自尊也是骑车人自己的。这就像一个外来人在老家可能是破落户,到了别人的老家却可能成为某种权威。村里人其实是懂得这些道理的。但日子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按道理来过的。面子问题在村庄里也是大事。人们擦车上油也是为了这种“尊严”。
当这些车子又回到城里谋生的时候,它们失去了在村庄的优越感,也没有了原来在城市里的归属感。它们已经有了自卑的心态,回到故乡不久,就变得破旧和懒散。不久“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地方都响”成了人们嘴边的调侃之词。
农村的身份和经历卸下了它们的锐气。它们此时已经是一辆乡下来的车子。城里人虽然多是从乡下来的,但总归学会一种城市的腔调,他们总是这种开头:乡下人……他们吐字的时候,从鼻腔流出一种怪异的调门。可是这似乎怪不了谁,农民也并没有任何抱怨。他们那么地爱慕城市。最后这些车又回到了车行,也许它们原来就出自同一家门市,但回收的时候就只是一堆堆废铁。它们和主人一样疲惫。人们焦灼于这种状况,他们不想像辆车一般回不到故乡。又因为兔林子的死,人们对于汽车及其带来的状况变得警惕起来。他们不再愿意乘坐汽车,一种新的车子出现在村庄。电瓶车其实只是加大了马力,它们奔走的方式和辛苦并没有改变。有了这种车子,人们走出村庄更加自由和方便。他们开始早出晚归于城乡之间,被阻拒的是变得越来越豪华的汽车。
电瓶车几乎成为城乡的一种灾难。它给村庄带来一种自我的狂欢。村民们开始怀疑城市的速度,他们在自己的手把上找到了控制命运的电门。他们突然在一辆车上找到一种自信。城乡一体化,可能就是在一个车轮的滚动中发生的。但世界可能关注了各种车辆的变化,却没有注意到人们心理的变化。这种变化比速度更加惊人。在越发宽阔的道路上,往返于城乡熟悉道路上的人们似乎迷路了。他们或者不再归来,或者无法回家。
我不太敢相信多年以后二叔也会死于车祸。父亲仍旧是半夜打电话给我。那次我正在微醺中大放厥词。我在城市生活了十多年,依旧改变不了自卑的脾性,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我也是一辆自卑的自行车,聒噪的铃声正是为了掩饰不安。父亲打电话给我时有一种十分不满的语气:“老二被车撞进了医院不行了,他总是瞎喝酒……”我知道二叔的酒量,但父亲不满他喝酒的方式—他总是闹酒。热闹的人也多是不自信的。但我以为他有自己的难处,只是兄弟们并不理解这一点。二叔是酒后骑电动车被汽车撞了的。除了他,这样的消息在南角墩已经不是孤例。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会想象那些熟悉面孔消失的样子。本来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的村庄,竟然成为他们的殒命之地。其实他们都盼望着叶落归根,但并不是以这种仓促的方式。
他们死在路上,这是一种悲伤的方式,是没有归途可言的离开。
村庄本来只有一条通往城市的大路,后来越来越多的内部道路出现了,似是实现了当年“要得富,先修路”的誓言。但富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太多安静美好的现实。正因为富裕像道路一样愈加宽阔,人们便把自己的村庄想象成了比城市更加辽阔的世界。过度的自信,让他们迷失了自我,觉得自己比城市更有资格狂欢。村庄甚至对城市讲究的规则和办法不屑一顾。他们按照一种情绪去生活。有时候情绪会让村庄显得很迷人,而更多失控的情绪让他们变得固执而盲目。我有一位年迈的舅母,她来城市生活没有任何胆怯,而是体现出令人震惊的自信。她骑车在城市马路的中间,用最快的速度表达她对于城市的理解甚至挑衅。她这样理解自己与城市规则的关系:“我走在大路的中间,他们还不能看见我吗?”当然较之于城市,他们在村庄更加“放肆”,会生发出更多令人费解的情绪—用父亲的话说:“世上是没有他们走的路了……”
村庄越发快速地生长起来,人们的日子有了更多的出路—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在路上走失了。
3
我一早就开始观察城市的道路。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并不熟悉那些城市道路的渊源。光那些复杂的路名就会让我眩晕。我们在村庄里并不按名字去区别或走过一条路。我们看着天上的日色,按照东南西北的方向去走路。这种办法很有效,为数不多的路走得明确与踏实。除了熟悉的路,人们并不轻易去走其他的路。村庄外出的路口是通道,也是一个族群的界址和禁地。人们早就习惯了不越雷池半步的格局。远行被认为是忤逆甚至叛逃。我在成人之前有过几次去其他村的经历,那里的屋舍与脸色似乎都是陌生的。我们将离开村庄当作冒险。这往往收获父亲带来的皮肉之苦。我们生长的范围应该是父亲的吼叫声能够到达的地方。除此之外则由树枝或者拳脚圈定。这和牲畜的待遇是一样的。人们生怕在轻车熟路的路途上走失。因此,在南角墩这样的村庄,丢失或者失窃是难得的事件,因为土地确实贫瘠得没有多余的物件可以被盗。
老人也并不认识很多的路。尽管他们经常声称—我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多,但这大多是因为人们走过的路程不大可观。当人们离开村庄的时候,子孙们会在陌生的路途上,举行一种很古老的仪式。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过死亡之后的这条漫长的路,他们很多人只是听说过作为终点的火葬场。当然他们闭上眼睛之后,将无从再见识这一段遥远的路程。后人心里恐惧日后自己无路可走或者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便在路上不断撒下“路钱”或者设“路祭”。至亲的人们还要揣上一些硬币丢在陌生的路口。这些都只是活人害怕以后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人一辈子在村庄回环往复地走路,最后出殡的时候还不能走回头路—等到人生成为过去,他们要最后一次从不同的路口回到村庄。
人们还害怕迷路,尽管他们并没有走过多少路。
二叔作为村庄的一名底层干部,因为一丁点的权力,人们将他与本分的农民对立起来,认为他尖聪,促狭,甚至有通天PDgmOhFnvNYJwD2f28eHq0rL2DZ3lFfsBUYCyBoKmZc=的本事。但这些似乎只局限于南角墩大队第五生产组三十多户的范围。离开村庄之后他就变得很笨拙。他们弟兄几个中,只有他不认识城里的路,一下车他总要闹迷路的笑话。对此父亲经常报以不屑。有一次他们弟兄几个喝多了,都找不到路,急急地打电话向我求助。见到他们时,我看到他们满脸的迷茫和无助。年长的父亲似乎更多些认路的经验,他总是埋怨二叔吃多了酒。如此二叔似乎也就有了像样的借口,每次进城来都会喝得酩酊大醉,从而让人们忘记了他是真的会迷路。
他最终殒命于村庄的道路上。据说那天他是喝了很多酒回家的。没有人料到他会在路上遭祸。他们每一个人对那些路都了然于胸。即便是后来出现新路,人们依旧非常地自信,因为它们并没有超出村庄的范围,土地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多了一些宽阔而陌生的出口。这本应该是给村庄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然而这些并不复杂的出口,让土地面对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这些与草木和庄稼并不匹配,最终人们在家门口走错了路。
二叔被用古老的方法送出了村庄,最终又回到了村庄的某个角落。这件事情引发了一些震动,但此后不久人们依旧茫然地颠簸在路上。我并没有去送他最后一程,但是记得人们向我描述的那个路口。日后我几次刻意开车从那边经过,那里的血泊已经被尘土覆盖,只有冷漠的车辆依旧在坚硬的道路上呼啸而过。大概一年不到的样子,我走在北国陌生的道路上,按照城市的规则走一个农民后代的路。我知道只要按照它们的规则来往,那些速度和危险就会在划定的线条之外。尽管这些路都是我们的父辈们在城里建起来的,但他们一辈子没有了解其中的道理和秘密。我再次接到父亲的电话,他悲伤地告诉我一位表姐车祸身亡的消息。我知道人们都会离开村庄以及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突然在自认为熟悉的路途意外地离开依旧令人心悸。
我的这位表姐有些笨拙。她原来和我母亲一样只会走路,后来嫁到离姨娘家不远的另外一个村庄,只有几里路的路程,无非是依着河流来往,不至于迷路。后来她学会了骑电动车,那时候村庄又多了许多便捷的路。他们后来说,她还有几步路就到工作的地方,若不是中途折一下给姨娘送点零用钱,应该能够顺利到达那个现代化的工厂。她一生不识字,本没有想过可以去这家工厂打扫卫生。她如果一生只蜷在自己的村庄,一定不会走上这段令人心碎的迷途。
周荣池,1983年生于江苏高邮。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单厍》《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草木故园》《村庄对我守口如瓶》等十多部,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