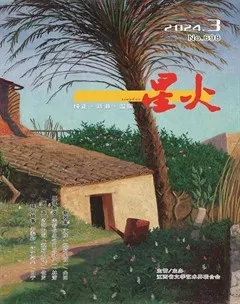远行(短篇)

凛冬,野外,疾风呼啸,暴雪纷飞。迷茫的原野里,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在雪地里跋涉,向前方城市的方向艰难迈步。身影十五六岁的模样,身材瘦弱,衣衫单薄,步伐无力,每走一步都摇晃。他停住,裹紧了身上单薄的棉衣,抬脚看了一眼鞋。鞋底前掌磨出了一个大洞。他坐在雪地上,脱下鞋,把鞋壳里的雪和冰抠出来,重新穿好鞋,站起身,继续顶着风走,又紧裹了裹身上的衣服。
当父亲说起他十六岁那年的这个经历时,我的脑海里总是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先如电影的远景镜头,再慢慢拉近。
每当此时,父亲都会停顿一会,愣在那里,一张不悲不喜的脸,吸着烟陷入回想。
有一次,我故意用很随意的口气试探着问:“要不,咱去庆城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家人了。”
我看到父亲有些慌乱,手里正燃着的烟掉了。片刻之后,他说:“找不到了,六十年了,都变样了,地方,人,都变样了。”父亲的语气中透着无限的苍凉与无奈。虽然这样说,可之后他还是会时不时又提起来。我也知道,这是父亲的一个心结,甚至可以说是父亲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心结。我的心里也徒然生出些悲凉来。
带上父亲去一趟庆城的念头,是我在看《内布拉斯加》这个电影时产生的。看电影的那个晚上,室内和室外都很安静,容易让人怀旧和感伤。
对我的这个想法,妻子杨静表现得很积极,说只当去旅游,母亲模棱两可,父亲一副不太情愿的样子。杨静连珠炮样一通说道,父亲和母亲才勉强上了车。
高速公路上的车挨挨挤挤,我们的车混迹其间。假期里的高速路,快是真快,慢也是真慢。杨静坐前排,与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嗑,母亲搭话多,父亲几乎不言语,偶尔蹦出来一句话,也是极不情愿似的。
母亲提了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上车后一直抱着。杨静让她放下,说抱着多累。母亲没有放下,反而说:“不累,坐车,还累啥。”杨静锲而不舍再三劝说,母亲才把布袋子放在了自己的脚边,手抓着布袋子的两根系绳。
堵车了。摇下车窗,能够听到旁边车道司机发泄的咒骂,气息粗重,声音尖利。我伸出头去,盯着那个同样伸出来的脑袋,想对他说,要不要喝点水,瞅到那凶神恶煞的面孔,我忍住了善意的提醒。
一会的功夫,杨静也不耐烦起来,低声嘟囔着:“导航提示了,说这条路堵,你不改道,偏走这条路。到庆城,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你就是认死理,一条道跑到黑的主。”她埋怨人,总能够切中要害。
对于这趟去庆城的远行,从父亲的神情中,我分辨不出,是“近乡情更怯”的那种怯懦,是不愿走近伤感之地的心理抗拒,还是欣喜却又努力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揣摩不透父亲的心思,他真的想去庆城吗?仔细想想,我觉得自己有点武断了。通过后视镜看父亲,他扭头盯着车窗外,看不到他的脸色。可是现在,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回不了头了。
从车窗看出去,公路边的土地和家乡的土地一般无二,但又有些新奇的风景,或许,这就是距离产生出的美。我无声远望,我的沉默没有影响到杨静。
“元旦放假,有时间,高速公路不收费。看看,多好。”
母亲却说:“庆城在哪儿?有啥好看的。”
“庆城,就在庆城,还能是哪。”父亲急吼吼地说。
父亲的一句话打断了杨静的聒噪,她也陷入了沉默。轮到父亲没话找话,“这个还能知道,哪里堵车,哪里不堵?”
“导航是用卫星定位,大数据分析,当然知道。导航能知道距离,能规划路线,知道哪个服务区有加油站,导航还知道哪条路堵,哪条不堵。”说话间,杨静白了我一眼,借以表达对我的不满。
“车是动着的,现在堵了,一会不堵了,也说不定。”
“导航显示的实时状况,说的就是眼下。”
“眼下,眼前的事,不管它以后咋样。”
“对,爸你说得对,只管眼下,不管以后。爸,你这话有哲理。”
“人都是要讲道理。”父亲说。
路在这个时候识时务地通了,我们的车子随着车流缓缓滑动,我清楚地听到父亲细微的喘息声。
冬日的暖阳,车内的空调,容易让人心浮气躁,我也开始没话找话说:“前面服务区,吃点饭吧。”
“有馒头,有鸡蛋,还有饼干。”母亲抢着说。从眼睛的余光中,我看到母亲的手伸到布袋里。“煮好的鸡蛋,还有牛奶,我预备着路上吃的。”
“谁出门还带馒头鸡蛋,又不是古时候行军打仗,带着干粮。”说完我就后悔了,这时我才觉悟,现在的我,已经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对母亲信口开河,没心没肺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
“能省几个钱。”
我能够从语气中听出母亲的唯唯诺诺,像做错了事情的小学生一样。我心里更加后悔。
“不饿,庄户人家,吃饭晚,没有个准点。”
“你不饿,余良饿。他从小胃不好,不能饿,你不知道吗?”母亲抢白了父亲一句。
我赶忙递上了一句:“妈,给我掰块馒头,吃两口垫垫,再过两个服务区,咱吃饭。”
母亲拿出来鸡蛋。我坚持说:“半块馒头。”我是故意的,想借此找回一点童年的时光。
母亲掰了半块馒头递过来,杨静接了过去,掰成小块,一点点塞到我嘴里。嚼着馒头,我紧盯着前方,头一动不动。
车出服务区,拐上高速,车里又陷入沉默,车窗外冬天的太阳异常亲切。我想打开车窗,让太阳的光直照到身上,又怕无孔不入的冷风趁机扑进来。猛地,父亲开了口,语调低沉舒缓。
那一年十六岁,正是饭量大的时候,正是长个的时候,遭了天灾,吃不上饭,就听人说,江南鱼米之乡,有饭吃,自个从家里偷跑出来,跟着庄上的人,后来就走散了。那天,风也大,雪也大,雪半尺多深,我的棉袄,又薄又破,不挡风不挡寒。那天清早吃了一个杂面馒头,晌午,半个菜团子,到了天黑,觉着天黑了,就奔着庆城走,又饿又冷。一双棉鞋,有一只鞋帮和鞋跟裂开了,还断了一半,趿拉着,一个脚鞋底磨了个大窟窿,鞋里都是雪。估摸着天快黑了,没有劲了,也得走,不走,停下,再想走就走不动了,自己也知道,也害怕,咬着牙走。
说到这里,父亲猛然收住了话,嘎嘣脆的就没有了下文。我接不上话,不知道该劝慰,还是应和,好像都不合时宜。车子终于跑进了庆城的地界。我才说了一句,到庆城了,父亲接了一句,到庆城了,言语中没有多少欣喜,也没有多少悲凉,显得平静。
车子停在城北的一家宾馆。杨静问为何选择这里,我说以前出差的时候住过一次,干净,也清净。我走到父亲身边,低声说,我查找资料,专门研究了这一块的历史,照你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不是这里,也是这附近。父亲面无表情,好大一会,还是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还能够再说点什么,只好拿身份证去办理入住,在柜台前等候时回头看了一眼,看到杨静背着小包,手里扶着行李箱的拉杆,母亲的手里还抓着那个布袋,父亲的手里拿着一包烟,烟瘾很大的父亲却没有取出烟。
放好行李箱,与杨静相互瞥了一眼,几乎同时迈出房间,一起走进父亲母亲的房间。父亲和母亲不知所措地站在床和长条桌中间的空地上,母亲手里还抓着她的那个布袋。我把母亲手中的袋子放到桌上,随手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顺势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晚上吃啥?”
“吃啥都中。”
“你们想吃啥?”杨静说出的也是我想问b8JF+myU6cfLCS3IDv2oxQ==的话。
“吃啥都中。”父亲依然低声说。我的心里又是一沉。当父母亲面对儿女们变得怯懦而小心翼翼的时候,他们是真的老了。我在心里叹息时间的流逝,同时说了一句:“我看看有什么特色馆子。”我和杨静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我听她的建议,选择了火锅。
沿着宾馆边上的路的左侧走,不远处有一家店面,门脸不大,显古朴,浸染了烟火气。桌是硬实木方桌,配硬木的条凳。鸳鸯锅在电磁炉上沸腾着,锅边上放着盛了牛肉、豆腐、青菜之类的小塑料盘,牛肉点了四份。父亲连说了几句多了多了,母亲说吃不了拿走,父亲才没再继续言语。
我拧开酒瓶盖,给父亲母亲和我自己面前的杯子倒上酒,杨静面前是果汁。杨静吃了一口,给予了赞许。父亲捏着酒杯,喝了一口,放下,没有吃菜,而是开口说,到了庆城,走到了庆城,遇到了好心人,一个好心的大娘,吃了一顿热乎饭,临走还给了我五毛钱,还给了我一双半新的棉鞋,换上了。
我听出父亲的声音有点颤抖,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搭话,默默喝了一口酒。
我看到父亲的手抖着,身体也是微微地颤抖,他用低低的声音说:“因着那场雪,村上有两个人没能回家过年,一个老头,一个小孩,没有那顿饭,我也就躺下了,跟他们两个一样了,雪地里,天寒地冻的,肚里没有饭,力气缓不过来。”说完,父亲低下了头。
杨静抓过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爸,我知道,救命的一顿饭,我敬你,爸。”一口喝完杯中酒,说,“爸,咱家现在的日子好了。”
“日子是好了,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啊。”我讪讪地接了一句话,说完,我对父亲举起了酒杯。父亲拿起筷子,抖着的筷子碰到碗上,“当当当”地响着。
我清楚地听到临桌响起了清脆的汤匙敲击碗碟的声音,接着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吃饭敲碗,不是好孩子。”我抬头瞥了一眼,看到邻桌一对小夫妻带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在吃饭。
小女孩离了座位,两步跑到父亲身边,说:“爷爷吃饭敲碗。”
小夫妻两个有些慌张,离开了座位,赔着笑走过来,站到了小女孩身后。我和杨静也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紧盯着父亲,也看着母亲。母亲低头吃饭,没有一句话。桌边瞬间无言,电磁炉上的火锅汤“咕嘟咕嘟”地轻响着。
年轻的妈妈拉了一下小女孩,说:“圆圆不乖了,圆圆听话,回去吃饭。”
父亲端起酒杯,他的另一只手伸出去想要抚摸小女孩的头,伸了一半又赶忙缩了回来,笑了笑,说:“爷爷手抖,是天冷,冻的。”父亲没有说是病,没有说老了,出乎我的意料。
小女孩说:“爷爷,吃火锅就热了。”
“吃火锅,吃火锅,爷爷吃火锅。”
小夫妻两个,杨静,还有我,几乎同时放松下来,年轻的母亲赶忙连拉带扯地把小女孩抱回到座位上,嘴里也连连说着“吃火锅,吃火锅”。 没过一会,小夫妻带着孩子离开了座位,离开时还对我们笑笑。
我们喝完了一瓶酒,我有点高了,走在前面,父亲跟在我身后,杨静装模作样地搀扶着母亲走在最后。走上宾馆前的台阶,走进大堂,父亲说:“烟没了,你买包烟,不要太好的。”我从羽绒服外口袋里掏出房卡递给杨静,而后,转回头,出了宾馆。
买了两盒烟,向回走,远远望见宾馆门上的大红字,红艳,透亮,身边一座座高楼直插上天。在这高楼间独步,心怀忧虑,我不知道明天应该去哪里。走进宾馆,在空落的大厅沙发上坐下,破天荒地抽了一支烟才上楼。
走出电梯,远远地看到母亲和杨静站在房间门口,神色焦躁,看到我,慌忙跑过来,急急地喊着,你爸,出去了!咱爸,不见人影了!
我的酒醒了大半,急慌慌折回电梯里,杨静和母亲也跟进电梯。我说我出去找找,你们回房间吧。母亲不说话,只看着杨静。杨静说,妈怎么能待得住,一起去吧,我们俩一路。出了宾馆的大门,对着杨静晃了晃手机,我说了一句,妈,没有事,爸出去溜达,可能是转迷路了,不会有事的,街上警察多。而后我们一路向南,一路向北。
街上行人熙攘,我的心里一片茫然,眼前还不时浮现出父亲描述的雪野。我一个巷子接着一个巷子地摸索过去,路灯的豁亮和没有路灯的漆黑都让我感到孤寂。
在一栋大楼脚下的暗影里,我看到一团黑影,走到近前,暗弱的光亮照着,我确定无疑,那是父亲。我低声喊了一句,又抬高声音喊了一句,父亲折回身看着我,喃喃自语:“觉着是这儿,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心里觉着,就是这里。”
我走到父亲身边,拉了他一下,说:“爸,夜里凉,咱回去吧,明天再找。”我看不清父亲脸上的表情,揣测不出父亲的心情,我只能猜测,我也知道我的揣测并不准确。
走了一步,父亲又停住脚,含混地嘟哝了一句,就算这儿吧。他抖抖索索地蹲下身,面朝南,双膝跪地,额头迅疾地碰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张贤枝,安徽萧县人,安徽省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沉香》,小说集《苦恋》,电影文学剧本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