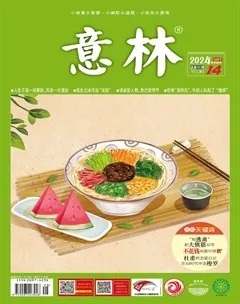老玉米
围着村子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地。父亲正忙着给玉米施肥除草。看到家栋,父亲有些意外:家栋是个大忙人,是单位的顶梁柱,在工作上要强得很,从不甘于人后。这么多年,他节假日都没怎么休息过。父亲问他:“这不逢年不过节的,咋就回来啦?”
“回来看您啊。”
回到家,父亲开了一瓶酒,对家栋说:“来,陪爹喝点儿。”几杯酒下肚,父亲说:“孩儿,你有心事,瞒不过爹的眼。”家栋猛地饮下一杯酒,脸上立马就泛起了红晕。
他想告诉父亲,这次单位要补缺一名副局长,他很想努力去竞争一把,甚至有了一些以往从未有过的、不太好的念头,于是,他想到了回乡下,听听父亲的意见。
看着家栋欲言又止,父亲没继续追问下去,对他说:“吃罢饭回屋歇一会儿,然后咱爷儿俩一块儿去玉米地薅草追肥。”
这一觉睡得好沉好香。等到日头已经偏西,家栋才醒来,父亲说:“洗把脸,咱俩下地去,这会儿没了毒日头,趁着凉快,能干俩钟头的活儿。”
锄完一趟,父亲和家栋并肩小憩。父亲说:“这原本是一块撂荒地,那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开了这片。当年,你爷爷对我说过,怎样才能不让地里长草呀?种上庄稼。只要地里有了庄稼,就不会容许杂草生长了,杂草一露头,就会被锄薅掉。等庄稼铺满了田间,就没了杂草。”
这晚临睡前,父亲从矮柜里捧出一个木匣子,对他说:“有件事你还不知道,我也是刚刚搞明白。你爷爷,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大功臣啊。解放战争的时候,你爷爷立过一个特等功,两个一等功。战争结束后,你爷爷转业到市里的化肥厂工作。后来上级动员职工离城返乡,你爷爷就回到了村里,要不是前不久上面开展军人普查登记,谁都不知道他这辈子还当过兵、打过仗、立过功。”
木匣子里,军功章泛着深沉的微光,家栋看着,鬓角处不知不觉凝出了汗,顺着脸颊慢慢向下流。
躺在床上,家栋又想起爷爷说过的关于杂草和庄稼的道理。他觉得,这些日子,他心里头的那块儿地生了杂草,且横生逞威。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家栋就起来了。他告诉父亲,手头还有一大堆活儿要干呢。
路过玉米地,家栋停下了脚步。父亲说过,这个时节,正是玉米的快速生长期,若是没有杂草,地肥水足,蹲到地头,就能听见玉米吱吱的拔节声。家栋蹲下来,侧耳细听,隐隐地,他似乎真的听到了。
(本文入选2023年湖北省黄冈市中考语文试卷,文章有删减)
曹洪蔚,笔名蔚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学会会员,开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纪实文学学会会长。著有《故乡的背影》等小说、散文集9部,30余篇作品入选中高考(模拟)试题或教辅读物。
《意林》:文章主人公“家栋”虽然没有贴近描写,却也生动立体,是如何创造这个人物的?
曹洪蔚:我一直在机关单位工作,在“家栋”这个人物身上,是有我的影子的。在现实生活中,像“家栋”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很多,他们工作不甘人后,也总想谋求更高的职位和工作平台,施展才华,干一番事业。所以,在面临“进退留转”的时候,也会有些“小心思”,甚至产生过“不太好的念头”。是父亲的“杂草说”,爷爷的军功章,让家栋去了杂念,坦然面对自己的“进退留转”。这个人物不是“高大全”式的,因而就显得生动立体。
《意林》:文章后半部分插入了爷爷的光荣事迹,在故事塑造上有什么用意?
曹洪蔚:我觉得,要让家栋这个人物彻底去掉内心深处的“私心杂念”,父亲的“杂草说”还不足以震撼心灵,而爷爷的居功不傲、高风亮节,恰恰与家栋的“杂念”形成鲜明对照,进而让人物生发灵魂拷问,产生转变,使故事和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意林》:标题《老玉米》中的“老”写作时有怎样的考虑?
曹洪蔚:玉米深受农民的喜爱,这里的“老”,有对父亲和爷爷勤劳能干、无私奉献、明事理、顾大局等传统美德的致敬和礼赞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