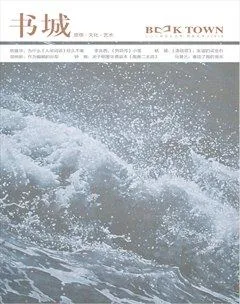谁动了我的音乐
美国作曲家科普兰写过一部舞蹈音乐,直白地题为《献给玛尔塔的音乐》—玛尔塔就是著名舞蹈家玛尔塔·格雷厄姆。后来她编了个题为《阿巴拉契亚山的春天》的舞蹈,科普兰也按她的建议改了曲名,这就是传世的管弦乐《阿巴拉契亚山的春天》。后来,好多人都活灵活现地对科普兰说,“你的音乐让我闻到了阿巴拉契亚山的味道”,科普兰反复解释标题和音乐毫无关系,怎么说也白搭。
类似的梗在古典音乐中太多,抽象的音乐之下,人们非要创造个意象才踏实。当然这也让音乐会的介绍有话可讲,以讹传讹或者一本正经地正本清源。放在过去,对这种梗我烦得想捂住耳朵,现在我对语言、神经科学有了点兴趣,不由得开始琢磨这算是人脑的bug还是feature。
先从语言本身说起
我对日常语言中的隐喻(包括但不限于小学语文老师教的明喻、暗喻)颇有兴趣,也观察到不少大家习以为常的“通感”,比如抽象层面的热(心)、(待人)厚薄、(嘴)甜、(命)苦等,不过我拿到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才发现我们日常用到的隐喻,比我想象的还多,而且,相当多的英文表达可以顺利地直译成中文,因为多种语言的使用者,体现出惊人的相似。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都是我们的日常所遇,“解决了那个问题,我会回来看这个”(回来是有方向的,说明人脑已经把抽象的事件赋予了方向);又如,“在电脑上进入一个文件夹”“你说话跑题了”“谁跟你关系最近”,等等。世上一切事物,原来都自带空间和时间,即便“文件目录”这种似乎扁平、谁也没摸过的事物,在人脑中也是个蜂窝般的立体存在。语言中的隐喻千千万万,相当大的一类是关于方向或身体移动的,这在充满运动的体育和音乐中更常见。《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特别举了“上”这个词,很多意义都可以用到“up”来表示积极、活跃的一面,而中文的球击中也可以说“打上了”,而击败谁谁,往往是“打下去了”,输了比赛也是“下去了”。“上”“高”往往自带“正能量”,比如讲课、演讲,人往往站着,因为较高的位置意味掌控。中英文当然也有不同的表达,比如英语中的“升c小调”,却是sharp(尖),“降调”则是flat(平,钝)。但总之,位置、空间感在各种文化中大量重合,多数语言都有许多介词、副词等所谓“语法功能”的词,“在”“和”“于”“with”“at”等,也都自带主次的色彩,好像专门建构空间,把人和物镶嵌其中。
原书中的隐喻当然不止于此。作者把隐喻分成几大类,也特别强调隐喻是对人脑中概念的塑造(如时间的“珍贵”“浪费”等,以及现代社会对时间的“货币化”)。此书初版于一九八○年,如果放在现在,不知又会加进多少鲜活到炸裂的网络表达。但网络归网络,你观察一下,网络语言中的隐喻仍然充满时间、空间和人体的关系,人与他人的互动,以及几种基本感官的混搭—人的基本欲求也就那么多种,但混搭起来则充满各色的条条块块,且生机无限。
反正,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有千百种描述方式,有了隐喻我们才能抓住mzGReDMY3KARVhqRHuPINF9yCDU2T50g0W/UR7GRShQ=当下最相关的一点来描述它。看上去,隐喻来自“相似”,但这个相似是主观的,甚至对相似的判断就来自现存的隐喻—现存的隐喻已经把我们洗脑了,然后才谈得上更当下的讨论。而“隐喻”这个工具,我猜差不多跟语言的历史一样长,因为没有隐喻我们简直就不会说话,也不会思想。作者说:“隐喻不仅仅事关语言,它还是一个概念的框架(conceptual structure)。”我们自从会说话就一头扑进隐喻的海洋,在其中穿行,理解自身并观察、总结世界,调动感官感受,时间空间坐标、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尽在其中。
仅就我比较了解的话题来说,都说音乐很难用语言表达,但我认为音乐离开语言则更难传播。音乐“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常常成为操练语言、扩展隐喻的试验田。
语言和音乐,相爱相杀
说到音乐,有人直接就想到交响曲和室内乐之类“纯音乐”,但这似乎是欧洲传统中较特别的一部分。世上绝大部分音乐跟语言直接共存,跟叙事或至少一个场景、图像分不开,比如歌词和舞蹈,在通俗音乐、民间音乐、戏剧音乐里遍地都是,甚至跟表演者本人现场构成一个独特并有机的故事,以至于它不好抽象化也不好理论化。
而音乐和语言的关系、异同,我们随意总结一下,可以说出一百条,我这里只想谈一条:它们都跟倾听的过程有本质的联系。
很久以来,神经科学家就知道人脑理解和产生语言,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脑区,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是处理对语言的理解的,其中有视觉语言中枢和听觉语言中枢;而对语言声音的感知和讲话,则是布洛卡区(Broca’s area),所以,仅就听觉而言,人类对语言的处理是“分而治之”的。布洛卡、韦尼克之分很久之前就被认识到了,而较新的研究表明,处理语言的过程,不仅有脑区的不同,也有路径之分:大致地说,背侧通路(dorsal stream)处理音节声音的产生和接收,而腹侧通路(ventral stream)处理声音的意义,如上图所示。对腹侧通路而言,越往颞叶(temporal lobe)也就是图中偏右的区域,接近韦尼克区,对语言意义的解析越明显。听到声音几毫秒之后,音节的意义就出来了,当然各种信息最后还要到额下回(图中的布洛卡区上方)去整合。
虽然布洛卡、韦尼克两个脑区和这两个回路是分开的,但也一直紧密联系,脑区受损而不能理解语言但会说话的病人,讲话也不会顺畅。语言机制不仅应用在正常的听说中,对手语、盲文也适用,无法理解语言的病人,触摸盲文也无法理解。
除了这两个脑区的关键作用,其他脑区包括运动中枢、情感中枢等也在处理语言时不断贡献力量。运动中枢对语言和音乐有类似的反应,举个例子:音乐激活运动中枢,让人听到节奏时就有运动的反应,而语言中的动词也激活它,比如听见“踢”,运动中枢就自觉地产生跟“自己踢”类似的反应。声音也能激活视觉中枢,比如听到“钥匙”,眼前很可能出现钥匙的形象—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殊不知这是人脑演化的结果。
所以,人听到较复杂、有过程的声音,要顽强地给它解码,就不奇怪了。泛泛而言,人类用语言表达一切,又想把一切解析为语言的动力,可以说至死不渝,什么也挡不住。而生理基础和文化传统也是互相滋养的,神经科学家有一句万古不变的名言:各种功能都来自天生(nature)+后天发展(nurture)。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音乐多少年来就有讲故事的传统。打个比方,音乐和词语在听者耳中向来“泥沙俱下”。即使是“纯音乐”,听者想把语言摘干净也并不容易,只是语言有多种,讲述也是。对声音、音乐,我自己的经验是,声音带来的语言经验往往细碎无序,可以有情景想象的闪回,多数时候讲不出文学中的完整叙事。
但另一方面,音乐和语言对不上生活中的故事,可我们有了记谱法,尤其是相当精确的记谱方式,音乐就可以被完整地“看”到并按顺序被复述,音乐就更加语言化,毕竟,乐谱就是一种语言—以至于音乐本身早已生长出奇怪的语言触角,甚至某些结构特质根本听不到,只存在于语言之中。有了语言,音乐经验被记忆得更清晰,也在为更多的语言隐喻做贡献。
音乐和建筑的联系,荒谬还是真实
在历史上,音乐和语言既已发展出千万种“奇葩”的勾结,我这里只举一个有趣的案例:音乐和建筑在语言中的映射。
有人说音乐是XX的建筑,建筑是YY的音乐,而在我看来那个XX和YY才是事物的本质,其他的偷换概念不过是一种狡辩—然而我也同意本质并不唯一,再说谁能剥夺大脑在语言中放飞自我的快乐啊?
一些了解建筑的人可能会用“节奏”一词来形容建筑。而众所周知,节奏本来是音乐语汇,但在建筑中,它可以意味着一些重复的元素,比如颜色、形状、形式等,比如一组一组的拱门、肋骨交叉拱、圆柱、彩色玻璃窗,数不胜数。当我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古老的大教堂的“节奏”,大半猜到原因,“不明觉厉”但也有点佩服。音乐的节奏和建筑的节奏,在我看来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其媒介一为时间,一为空间,但确实都有规整和分组的需求,也依赖重复来建立框架,并且都能传递情感。有人就这么“假借”了,并且被很多人接受。巧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实指出来,时间和空间互相作用,甚至可以互相转换。我们普通人的大脑虽然没有悟出相对论,但隐喻也好,概念混搭也好,偏巧能化合出这样不可预测的幻觉。
我曾经开玩笑地说,假如我们的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追踪空间性和时间性的描述在人脑中如何相互完成映射和转化,是否能成为神经科学中一个有用的案例?
不久前,大名鼎鼎的“塔利斯学者”合唱团(The Talis Scholars)来温哥华演出,我按照老习惯,在网上预习了一下他们要演唱的曲目,找到的录音也包括五花八门的合唱团。在非常不同的教堂空间里,各种合唱团在排布演唱者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些演出,把低音部排在教堂中殿的两翼,各个声部在空间上都分开,也有一些是集中并环形排布。而在“塔利斯学者”合唱团的现场,我发现他们按作品风格站成不同的队形。也许是噱头,也许是声部需要,但至少他们确实想传达一种空间感。
对,音乐的空间感。教堂合唱中,有空疏的声部,也有逐渐增减的对位,那么音乐和空间,会不会仅仅来自记谱方式带来的错觉?对任何一个读谱的人来说,多声部在谱纸上的布局,都会直接带来这种空间感,然而在音乐进行中,至少在欧洲的和声理论里,八度、五度之差并不“远”,它们其实近到相邻,反而是半音之遥,让人在情感上突然有千里之远,一个和弦在半音之内起伏,情绪则如同瞬间坐上“时光机”。但不可否认演奏、演唱者抵达八度之外是要“跳跃”的。音高、音色、调性、和声,哪些音素更有空间感?见仁见智。
然而,从声学角度看,音乐和建筑有着极为真实的联系,除了乐器、人声的站位、管风琴音管的排布对音效的影响,还包括听者身处不同位置对声音的感受。我在同一座大教堂里听音乐会,不同场次坐在不同的位置上,发现每个位置都给了我不同的体验,夸张一点说,教堂里的音乐有无数种听法,因为每挪一步,音乐和空间都合作出一个新场景。音乐厅当然也有类似效果,但教堂里障碍物(比如支柱)更多,让“我听到的音乐”更不可预测。
最近我读到一本关于人如何感知空间的书,《创造空间》(Making Space: How the Brain Knows Where Things Are),就包括眼、耳如何判断视觉或声音信号的位置,而这至少是“空间感”的一个重要成分。
话说各种动物的耳朵,都有判断声源位置的能力—因为耳朵有两个,它们之间有间隔。简单地说,人类和许多动物的听觉回路中,有些神经元是和两耳相连的,那么它就能感知到声源在两耳中抵达大脑的时间差。响度抵达双耳的差别也能让人推测出声源位置,因为头部的遮挡。而头部的遮挡让响度在两耳中差了多少?有趣的是,高音的声波因为波长短,在头部也就是障碍物附近散射得较多,所以“损失”得更多,所以高音在两耳中的相对响度差别(单位是分贝)比低音要大。但仅仅靠两耳位置的差别来定位声音还远远不够,毕竟空间是三维的,所以人类有着褶皱的外耳廓(就是伸手能摸到的这个耳朵)。这个东西像均衡器(equalizer)那样,让不同声音频率体现不同的衰减程度,给大脑提供声源位置的线索。别的动物当然也会,并且可能比人的能力更强。
关于不同频率的声音下衰减模式的差别,作者举例说,音乐从二楼传来,和朋友从楼下叫你,会体现不同的衰减,你的耳朵可能过滤掉不同的频率,尽管距离看上去差不多。具体到各种情况,有着相当复杂的算法,跟音频、头部位置、人对声音的记忆等许多因素相关,所以用耳廓来听声源,跟跳过耳廓用耳机来听是不同的情况,现代的音响工业更是一个讲不完的大坑。
如果这还不够复杂,在空间感方面,听觉还严重地受视觉影响!人脑已经自带了整合眼耳功能的设备,其中包括位于中脑中的上丘(superior colliculus,简称SC)结构,它直接地连结眼球、头部肌肉运动在视觉信号刺激下的运动,也就是,人会跟随不同位置的目标转动眼球,也会转动头部,而人耳在判断声源的时候,也依赖头部的位置,这只是两者互相影响的一个方面。
该书作者格罗教授提到眼耳功能的沟通和整合,已经用到了“跨越语言障碍”这个说法。所以,视觉和听觉、音乐和空间的这种联系,不可能不反映在语言上,不可能不激发相关的隐喻。好吧,视与听,两者的功能本来在两个维度上,鸿沟不小,但从神经传导水平已经在部分地换算,至少在空间感这个方面。她在网络课上就曾经兴奋地说:“上丘是我近年最心爱的结构,因为它谜团太多、太有趣了,不是吗?”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眼球的位置信息在抵达上丘之前,就整合进了听觉回路,而上丘这个几毫米大小的结构,已经被研究者分成好几层,其功能仍然充满未知。
当然,我并没有因为上丘沟通眼耳的功能,就断定它造成了人们对音乐和建筑的通感,但人的耳朵就是个“时空转换大师”。至于时空在词语中的映射,你可以说它是文化中的玄学,但也有大脑的生理基础。也可以说,是语言这个强大的“器官”在记忆的辅佐下最终凝结出这种感受。在巴别塔的故事里,人类因为语言的阻隔而无法造出通天塔。然而在另一个维度上,语言又像泥土一样黏合脑功能和人生经验,创造出一个虽不能通天,但相当丰富并不断生长的小世界。世上事物千千万万,人脑无法分别处理它们,一定要找到联系。好比森林中的树木之间靠土壤来交流营养,世上万物靠语言的联系映射到人脑之中。
音乐的传播:谁在撬动语言
上面说到语言跟音乐时时短兵相接,因为人脑顽强地解读声音,几乎不可抗拒。暂时放下神经科学的话题,如果只用文化来构建解读音乐的语言,我们能走多远?
我以为,音乐和语言的互相作用,在当下看得更清楚:如今资源极为丰富,话语也极为丰富,词汇的触角无处不在。但它能不能攻克当代音乐较难懂的那部分?
比如,有人说现代音乐看似每个作品都不同,其实又特别趋同。对此我觉得事实可能有多面,首先是不是现代作品都“客观”地趋同?不否认这种可能,但衡量起来太难,至少对我完全是未知数。但我猜一下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创新”的欲望在现代太强烈了,太多认真的作品都试图与众不同,那么你让一个受者去谈感受,他就没有基准线可以比较,而脑中没有成形的词汇去归类,就只好糊里糊涂地认为每个都不同,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每个都X”的趋势,最终就在人脑中被标成相同。所以在我看来,与其说现代音乐听上去都一样,不如说听者用语言记录它们的方式、最后形成的记忆贫乏得相同,当然可怜的听者也是因为现代音乐变化太快,语言追不上更来不及沉积。另有一例,某位跟当代视觉艺术界有交往的友人愤愤地跟我说,当代艺术界无聊透了,作品还没见面,已经请好了人写评论,最后作品和评论合作成一个貌似高深的东西,满足大家一个听故事的需要。我觉得,刨去其中虚矫、人为的东西,作品+话语,自古以来倒是一个正常的渠道,人脑中若没有下沉出一个归结到语言的经验,就不可能吸收到文化里。
然而,即便是那些还算悦耳的主流古典音乐,在当代仍然不易传播,因为历史之隔,因为其复杂的本性、时代的需求等原因。但是,欧洲古典音乐也碰巧拿到了一张彩票:它记谱的精确、高度的结构性、逻辑性和复杂度虽然没有用在讲故事上,但它有另一类讲法。大师课,甚至一节普通的钢琴课上,老师头头是道地分析音乐的逻辑,有时两小节复杂的音乐就能讲一个小时,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弦能填充许多博士论文也不奇怪。所以,复杂的经典音乐提供了一种学院式、理论化的语言,这样它跟教育体系重合度较高,能寄生在学校中,被一代代老师和专家讲下去,无论是音乐学院还是私人工作室,系统化的学习可以经年累月。当然,学校生活不是一种“自发”的生活方式,所以有些东西在校园外的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有些东西则仗着人类的教育需求和资源不断传承。
所以,连这种音乐也一直在被讲述,尽管对公众而言,它常常来自“沉默而有话语权的极少数”。
说到这里,我对照谱子认真听了一首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K. 458,也仔仔细细看了他在奏鸣曲式中如何把呈示部的乐句小心切碎了贴到发展部,然后它们也都在再现部中变身但能辨认(即便在这个简单的句子中,我已经不自觉地应用了好几个隐喻)。总之,我觉得古典作曲家的音乐,总有一种“同质性”,音乐也许有特别可记的旋律,也许没有,但总有一种珍珠密布的连续感。有人可能说这也是一种“建筑”,但我觉得作曲家苦心在音乐中处处搭桥或者埋藏“线人”,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帮人记忆,所以编织了这种网络,而这种高度依赖记忆的需求,在以空间性存在为主的建筑中并没有对等的元素。这样说来,我上文中的巴别塔之喻,应该这样讲: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这种音乐面前只有不堪一击的“语言性”联结它们,并且只存在于不太高明的隐喻之中。不过且慢,这首精致细腻、可以容纳无穷分析的K. 458,偏偏有个别名叫作《狩猎》,此标题在许许多多荒谬的音乐标题中,不算最不靠谱,但它和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音乐标题一样(比如莫扎特的所谓《朱庇特交响曲》),让这首曲子成为同类作品中识别率最高、最常上演之作。
参考文献:
Metaphors We Live By, by Professor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Language and Mind, by Spencer Kelly, the Teaching Company, 2020;
Making Space: How the Brain Knows Where Things Are,by Jennifer Groh, Belknap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