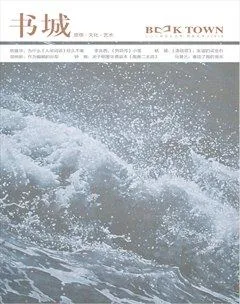燕燕于飞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
之子于归,远于将之。
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
之子于归,远送于南。
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诗经·邶风·燕燕》
抒情诗和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的核心动力时常在于对某种尽头和未知事物的探寻,而在抒情诗领域,人们总是一次次回到开端。《燕燕》被前人誉为“万古送别之祖”,是后世无数送别诗的开端。
在这开端伫立着一个人。他看向远处的目光仿佛在看向我们,而我们也是从他那里了解到最初的别离,这种别离和我们今天的别离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关于一个人如何面对另一个人即将离开的事实,如何一再地拖延却最终无计可施,如何走到能够一起走到的最远的边界处,再停下来,看着另一个人消失在视野中,如何就这么久久地伫立着。钱锺书《谈艺录》有言:“夫客子远役苦辛。旅程烦褥,煞费料量,人地生疏,重劳应接;而顿新闻见,差解郁陶。故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专笃,亦犹思妇之望远常较劳人之念家为深挚。此所以‘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法国诗人(A. V. Arnault)旧有句云:‘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拜伦致其情妇书曰:‘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
《燕燕》就是一首由居留在原地的那个人写下的诗,他写一首诗是为了安慰自己,但最终,他也安慰了无数的人。
在《诗经》十五国风中,《燕燕》隶属邶风。邶、鄘、卫都是殷商旧地,燕子是这里最为常见的鸟类。作为和人类关系密切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飞翔的候鸟,燕子每每给人一种复杂的感受,它辛苦筑巢又注定离去,让人想到远方、漂泊和人生严酷的冬天,但它也让人怀揣归来和团圆的希望,一如对于春天的希望。因此,一首谈论别离的诗从燕子开始,似乎就是非常自然的事。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前人在此处多纠结于“燕燕”是指双燕还是单燕。最早的毛传、郑笺和孔疏都指单只燕子的动作或特征,朱熹《诗集传》也从之曰:“谓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齐之貌。”但后来宋明之际崇尚新学,慢慢就有一些异议,如严粲《诗缉》:“如双燕之飞,其羽差池,相为先后而常相随逐也。”徐光启《诗经六帖讲意》:“燕之宿也相向,其飞也相背,故以差池之羽为别离之意。”这都是取双燕说,认为诗人是用燕子成对和人的别离形成对照。到了清代,汉学复兴,胡承珙《毛诗后笺》就力驳双燕之说,他举出的有力例证是同在《邶风》中的另一首诗《雄雉》,其中有“雄雉于飞,下上其音”一句,从诗意而论显然是指单只雄雉的声音忽上忽下,由此可以推断《燕燕》中的“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亦属同调。但这个分歧并没有就此平息,直至现代,比如陈子展、高亨就依旧认为是双燕,而袁行霈、程俊英则支持单燕说。
就诗意而论,我会认为单燕说要更为深沉一点,因为飞翔这个动作和远行是贯通的。但进一步的确认还要联系接下来的诗句。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此句关系到这首诗最大的分歧,即这究竟是一首谁送谁的诗。毛诗小序所言“卫庄姜送归妾”是历代主流意见,这涉及一段春秋历史,即州吁之乱。卫庄公夫人庄姜无子,庄公和从陈国随厉妫嫁过来的戴妫生子名完,立为太子并交给庄姜抚养,但庄公后来又和一个宠妾生了个儿子州吁。庄公死后,太子完即位,是为卫桓公,十几年后,州吁作乱弑君,不久,卫国大臣石碏联合陈国国君陈桓公诛杀了州吁。主流意见认为这首诗讲的就是州吁作乱之后的故事,此时戴妫在卫国已无亲人,照旧礼可以归返故国,是为“大归”,于是庄姜去送戴妫回陈国。同时因为后来的州吁之死与陈国有关,后世论者又敷衍出庄姜临行嘱托戴妫回陈国伺机劝说国君复仇这条暗线。这个故事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确实也配得上一首杰出的抒情诗。
但这个故事要面对两个难以解决的疑问。首先,“之子于归”这个句式是《诗经》中的常见套语,分别在《桃夭》《鹊巢》《汉广》《东山》和《燕燕》中出现过,在除《燕燕》之外的四首诗中,都意指女子出嫁,即嫁归夫家。因为词语的意义从来不是孤零零出现的,而是依托于前后文字形成的句式和语境,虽然“归”字在先秦有其他意思,但在“之子于归”这个句式中却从未有过其他解释,所以,倘若《燕燕》的“之子于归”,在没有同时代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忽然被解释成女子归娘家的“归”,就很难让人信服。其次,《史记》曾明确记载卫桓公的身世,“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完即卫桓公,完母即戴妫,齐女即庄姜,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戴妫早死,公子完才会过继给庄姜抚养。庄姜送戴妫归陈国的故事,就显然和史书矛盾,此外,《左传》在涉及州吁之乱时也根本没有提及庄姜、戴妫,也就是说,庄姜送戴妫的故事并没有得到正史的支持,或许只是汉代人的附会。当然,这两点其实早在清代崔述的《读风偶识》中就已提出,但后来依旧有部分学者仍持庄姜送戴妫的说法,他们在面对《史记》的证据时会像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那样反驳说,也许史书搞错了,因为司马迁在其他某某处也犯过错。那按照这个逻辑,为什么司马迁在这里就不能是对的呢?既然他在其他很多地方的记载都是对的。
现当代学者大多还是接受了崔述的质疑,转而认为这是一首国君送妹出嫁的诗。之所以是国君,和这首诗末句的“寡人”有关,这在上古通常是君侯的自称。刘毓庆认为“国君送嫁妹”之说有三个问题,一是国君送嫁妹,不合周礼,并引《左传》记载齐侯送姜氏为“非礼”为证;二是寡人是君臣间的自谦用语,不可用于亲人;三是“于归”并非专指出嫁。然而这三个问题,或许都不是问题。首先,关于国君送嫁妹的问题,其实闻一多《诗经通义》早有通达的解释,既然《左传》有记载,就反过来恰好证明当时确实存在国君送嫁妹这样的行为,“本篇亦诸侯嫁妹,君自送之,与齐侯事同科。当时行事,多不准于礼”。再者,如果国君送嫁妹不合礼仪,那么难道身为太后的庄姜出宫送妾到郊野就合乎礼仪了吗?其次,关于“寡人”的问题,其实当代学者已有论证,它在上古并非谦称,而是表示“独一无匹之人”的尊称,同时它在这首诗里也不是用于亲人之间,而是国君送走妹妹之后独自一人时的慨叹。最后,即便“于归”并非专指出嫁,但这首诗中专指出嫁的套语是“之子于归”而不是“于归”,不能割裂开来分析。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另有一种质疑嫁妹说的意见,就是来自这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出嫁这件事不至于这么悲伤。这是典型的以今证古。《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这是记录赵太后送女儿出嫁燕国时的哀泣。君侯之家的女儿出嫁不同百姓,往往是要嫁到他国,因此,对诸侯以上阶层的女子来说,出嫁就几乎相当于诀别。这哭泣因此就并非后世女子出嫁时需要的一种仪式感,而是源自真实的永诀。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 这首诗第二章中的一个争议焦点,是“颉之颃之”句,因为有两种相反的说法。毛传认为“飞而上曰颉,飞而下曰颃”,但后来清代段玉裁等人认为毛传是搞反了或是后人抄错,应该是“飞而下曰颉,飞而上曰颃”,他们的理由是颃通亢,而亢的引申义是高,所以颃就不该是飞而下,而是飞而上。但这个理由其实不太成立,因为我们在讨论引申义之前更应该关注一个字的本义。亢的本义是“颈”与“咽喉”。徐灏《通介堂经说》:“鸟飞而上,必昂其首,故谓之颉。飞而下则见其亢(鸟的喉咙),故谓之颃。上下字不误。《易·小过象传》虞注:‘飞下称亢。’即本毛义,是其明证。”颉,是头颈伸直的意思,鸟向上飞时可以见到它伸直的头颈,鸟向下飞时则可以见到它的咽喉。另一个证据是高本汉在《易林》中找到的,《易林》有“颉颃上下”的句子,颉颃与上下对应,也可以证明毛传并没有搞错。颉之颃之,就是在形容燕子上下翻飞。
“之子于归,远于将之。”将,送也。程俊英《诗经注析》认为“远于将之”句是倒装,即将之于远,送她往远处去。但倘若就照着这四个字的顺序直译,如陈子展所译的“远远地去送了她”,其实更见诗意。这个“远”,就是送别路途的远,和第一、第三章的“远送于野”“远送于南”一致,只不过在这里更强调这段送别的过程,而非终点。
“瞻望弗及,伫立以泣。”从“泣涕如雨”到“伫立以泣”,这并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诗人要呈现的,是一个哀伤的情绪如何一点点被控制住的过程。痛哭已经变成了低泣。这个控制情绪的过程,倘若再联系后面一章末句的“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会更明晰。“实劳我心”,一般都会把“劳”理解成“忧劳”,但我觉得这里其实应当是“慰劳”的意思,和《邶风·雄雉》“展矣君子,实劳我心”、《小雅·白华》“维彼硕人,实劳我心”义同。那个美好的人已经远去了,我停在那里瞻望也瞻望不到她了,但我依然在瞻望,因为知道有一种美好确实地存在于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这本身也构成一种对自己的安慰。张爱玲曾在书信中记录一次离别:“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这段文字,这个伫立涕泣的形象,几乎就是从《燕燕》这首诗的词句中走出来的,又不落任何痕迹。当然,在张爱玲这里,情况更为复杂,她更多是在为某种普遍性的人生境遇感怀,她为之哭泣的,是爱本身。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这第三章没有特别困难的地方,它和前两章拥有大抵相同的句式,但在略作变化的地方若稍作停留,则可以体会到诗人的深心。比如,从“差池其羽”到“颉之颃之”再到“下上其音”,这里面的变化是燕子和我们的距离以及我们观察它的方式,起初是能看见燕尾羽毛的细节,随后是看到燕子上下翻飞的整体,最后是仅仅听见它的声音。这燕子虽然还在我们眼前,却仿佛正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感觉恰恰和送别之情相通。而“远送于野”是送行之初所感到的四野茫茫;“远于将之”是送别过程中的行行重行行,心思只在对方身上;“远送于南”则是送行到最后,渐渐清醒地意识到对方的目的地。这里的“南”,可以泛指南国,或许也就是楚国,因为卫楚两国时有政治联姻。至于“实劳我心”和“泣涕如雨”“伫立以泣”的次序,如前所述,呈现的是一个哀痛者努力做到的自我调伏,从眼泪到心灵,他渐渐平静下来,接受这命运。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第四章的句法和意思与前三章完全不同,所以一直有人认为这一章是错简,但在自己难以理解的地方就断定古人搞错了,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很要不得。因为很可能,难以理解的地方也正是我们学习的入口。
很多现代注者看到“仲氏”一词就认定是指女性,这是没有道理的。在《诗经》的时代,“氏”字并不专指女性,而是“姓氏”之“氏”。《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就是指兄弟二人;《大雅·韩奕》:“笾豆有且,侯氏燕胥”,其中“侯氏”指韩侯,也是男性。但《燕燕》中的“仲氏”,确为女性,只不过这个女性身份不是从“氏”字来的,而是从“终温且惠,淑慎其身”一句得以推断。温惠,即温和惠顺,是待人之道,讲求的是终始如一;淑慎,即良善谨慎,是持身之道,要的是身心合一。是这四种确切属于古典女性的美德,让我们认识了这首诗的女主角。
“先君之思”是这一章的核心句,它的句法类似“莼鲈之思”,是指对先君的思念。无论各家对于诗旨理解的千差万别,落实到对于这一章的解释,几乎都是把前四句视为诗人对仲氏的赞美,然后把“先君之思,以勖寡人”,解释为仲氏勉励“我”(即寡人)去思念先君(即父王),或仲氏以她对先君的思念来劝勉“我”。这在人称指向上的逻辑关系其实非常混乱,但当最初这首诗被解释成庄姜送戴妫这样的妻妾相送的场景时,这种混乱就被掩盖了,因为对于妻妾而言,思念先君(也即她们的亡夫)确实是一种最重要的情感桥梁,这种情感联系掩盖了逻辑混乱。但假如按照我们先前的论证,把这首诗视为一首国君送妹远嫁的诗,那么,再把“先君之思”解释成妹妹对哥哥的叮咛,要哥哥记得父王,并把这种叮嘱视为妹妹美德的表现,就有一点显而易见的牵强了。
让我们再回到这一章最初的“仲氏”二字上来。这两个字开启了气息迥异的第四章,或许秘密也就藏在这两个字中。
《白虎通》:“男子五十称伯仲。女子十五称伯仲。”又引《礼经》:“女子十五许嫁,笄。礼之称字。”由此可以推断,“仲氏”正是礼成之时她的父母所给予的字,而“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这四句的语气,非常庄重,很像是引自父亲在赐字之礼上的评断,而不是兄长的赞美。“任”,是周礼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之一,《周礼》注云:“善于父母为孝;善于兄弟为友;睦,亲于九族;姻,亲于外亲;任,信于友道;恤,振于忧贫。”女儿待人有恩义,讲信用,这是父亲对她根本的判断。“其心塞渊”,和《鄘风·定之方中》“秉心塞渊”相近,“塞”是笃实,“渊”是深远,意指心地笃实深远,这是进一步阐发对女儿的了解。“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则可以看作父亲对女儿的期许。先秦贵族女子出嫁,要经过祖庙,礼拜先祖,所以这一章所记录的情景,或是年轻的国君怀揣离别之惆怅,以及对远嫁他乡的妹妹的各种担忧,一个人郁郁而归,再度途经祖庙时,想起父亲,是谓“先君之思”,进而想起父亲生前(即先君)对妹妹的判断,想到以妹妹温惠淑慎之德行或许在异乡也可以过得不错,由此获得了一点勉励。
“以勖寡人”,“勖”是勉励的意思。在一首送别诗的最后,诗人把“瞻望弗及”的目光收束回来,落在自己身上。他所在意的人,之子或先君,或停留在时间深处,或消失在空间尽头,但借助一首抒情诗,他把这一切的失去统统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