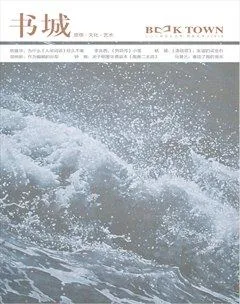梅川书舍札记(十五)
新诗人刘梦苇的绝笔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徐志摩在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个启事》,哀悼《晨报副刊·诗刊》同人刘梦苇的逝世。被视为新月派诗人的刘梦苇是该年九月九日在北京病故的,年仅二十六岁。徐志摩悲叹道:这个“热烈的诗魂,这‘孤鸿’如今实现了最后的自由,更不在人间啼叫了!”
刘梦苇生前只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青年的花》(1924年4月上海青年文艺社初版),但当时文坛最为看重的是他的新诗,虽然徐志摩在《一个启事》中预告他的诗集《孤鸿》已交商务印书馆印行,遗憾的是,后来并未实现。那么,在刘梦苇英年早逝之后,他还有遗作存世否?
答案是肯定的。一九三一年二月北京大学综合性月刊《北大学生》第一卷第三期刊出了署名刘梦苇的《心月》,目录标明《心月》系“新诗”。查阅原刊,发现在刘梦苇的《心月》前,有《北大学生》编辑徐万钧写于同年一月二十日的一篇说明,十分重要:
许是十五年的暑假吧?那时我住在元字十九号,日期不记得是那一天了,我偶然在元字号南厕所的墙根,发现了一本英文练习簿,上边题签着“诗歌”两字。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我揭开看了几页。第一页上盖着飞鸟社的钤记,钤记上边盖了“梦苇”的方章,下边写着“梦苇作”三个字。“梦苇?—这是谁的名字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听着倒很熟哩。我便不经意地把那本小册子携回寝室,随便翻看了几节,觉得作者的情感十分浓郁,辞句也十分生动。这样呕血殚精的结晶,为什么被抛在墙根呢?许是作者正因为呕血太多,殚精过甚,讨厌作诗,却把它抛弃了吧?
不久,我在《晨报》上看到徐志摩先生发起的诗人刘梦苇追悼会这桩新闻,忽然联想到那本无主的诗集的主人来。很想把这本诗集寄给徐先生请他保存。因为私事忙碌,终于不曾实现这件愿心。
今年,滥竽月刊编辑职务,为了新诗方面缺乏材料,忽然想起刘君的诗稿来。本期所登《心月》一章是刘君诗稿中《夜夜的心》的一部分。《夜夜的心》一共分为十八个小题目,《心月》是其中的第四个。其余各章,以后按期登载,以免这样呕心的结晶永久的埋没了。
《夜夜的心》的末一章的最后一节是这么的写着:
死神的请帖既已来到,我可不能不束装就道。可爱的!我们从此别了,黄泉之下的把晤匪遥!
所以《夜夜的心》也许就是刘君的绝笔;因此,更有发表的价值。
这真是充满了戏剧性,也令人悲喜交集。悲的是刘梦苇临终前不得不丢弃(或遗失)自己最后的诗稿,喜的是有心人徐万钧捡得诗稿五年之后终于将其公开,否则,这份珍贵的刘梦苇“绝笔”很可能真的被埋没了。以下是《心月》全诗:
我心如新月,思君夜复夜;痴情夜夜增,将成团圆月。
我心如满月,思君夜复夜;夜夜苦思君,将为君瘦缺。
月团圆,人何处月瘦缺,人更苦
月缺月圆月又缺,月光夜夜照君侧;嫦娥如有情,应早对君说。
值得庆幸的是,刘梦苇这组《夜夜的心》得以在《北大学生》连载,隔了九十多年,现已被完整收入即将出版的《孤鸿集:刘梦苇诗文辑存》(解志熙编),这位“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朱湘语)的作品终于将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三大家题《雄鸡图》
这里所说的“三大家”,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位重要人物钱玄同、周作人和刘半农。《雄鸡图》则指民国画家王青芳于一九三三年(鸡年)所作的国画。
王青芳(1900-1956),安徽萧县人,号芒砀山人,室名万版楼,擅花鸟山水,又擅篆刻,与齐白石交往颇深,曾为其治印多方。这幅《雄鸡图》画一只精神抖擞的大雄鸡屹立于峻石之上,引吭高歌。王青芳自题画曰:
不堪回首。癸酉王青芳为鸡年画鸡,芒砀山人,时一九三三雨窗
其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往事历历,“不堪回首”。王青芳遂在鸡年创作此图,以雄鸡喻华夏,疾呼抗敌救国。画成,王青芳请他所敬重的这三位大家题识,钱玄同先题曰:
徐□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有五德,首带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敌在前敢斗,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信也。 廿有二年八月七日敬题 青芳先生妙绘为鸡年画鸡 疑古钱玄同
(钤白文“玄同之鉨”、朱文“疑古”两印。)
第二位题识者为周作人,他题曰:
郑风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二语甚佳,实能写出极妙情景。今以奉题 青芳先生妙画,亦正相称也。 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作人识于北平
(钤白文“周作人”印。)
最后一位题识的是刘半农,他题曰:
自有生民即有鸡,鸡鸣而起各孳孳。术分仁暴由人择,事必糊涂任我为。国难临头呼口号,倭刀加颈觅飞机。年年曰攘邻家一,敢诩咱们老面皮。 青芳先生自题妙画曰不堪回首,是忧国青年气概。玄同录徐氏说,是经师家法。启明录郑风,是文人风度。余既无气概,也无家法,更无风度,却因青芳善画,曾揩两幅之油,故以打油诗报之,愿其于艺事上努力加油也。 创世纪上帝第五日造动物,第六日造人,故首句云然。 二十二年九月卅日 半农刘复
(钤朱文“刘”、白文“刘复私印”、朱文“桐花其豆堂大诗翁”三印。)
三位题识中,周作人的最短,刘半农的最长,其实是一首打油七律加上附记。查钱玄同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日记,并无为王青芳题识的记载,在此前后,钱玄同事甚多,身体也不佳,想必失记。但周作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日记则明确记载:“上午为半农及王青芳君题画。”次日又记云:“上午往送半农、王晓聃、王青芳诸君件。”题识的来龙去脉已一清二楚。至于刘半农,有无日记不明,也无从查起矣。此外,这幅《雄鸡图》曾在一九三四年“上海艺风社第一届画展”展出,又发表于同年《艺风月刊》第二卷第九期,可见题识早为世人所知,流传有绪。
王青芳邀请钱、周、刘三位为《雄鸡图》题识,当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当时在京的这三位是最具代表性的了(鲁迅、胡适当时已不在北平)。请这三位《新青年》中坚共同为《雄鸡图》题识,正是再合适不过。
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三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大家的墨宝,单人的以周作人所书流传最多,但在画作上题识也颇为少见。三位的墨宝荟萃一堂,又都书写得如此端正,至今未见第二幅。因此,这幅寄托钱、周、刘三大家和王青芳情思的《雄鸡图》极为难得,也极为珍贵也。
鲁迅致韩振业信
鲁迅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得天马书店信,即复。”这即复之信,即二○二四年四月六日在香港嘉德拍卖会上拍出的鲁迅致韩振业信。此信毛笔书于两页玉版宣上,纸有折痕,有黄斑,照录如下:
振业先生:
下午得廿二日函,谨悉种种。我的自选集中文,最迟者一九二六年,其时国民党尚未秉政,我也因为同情他们,被北洋军阀所忌,遁至厦门。倘使今之国民党,非昔之北洋军阀,则怎么十年以前所作,就有反动。但既是对人,无道德,无法律,这些话都不必提了。出版者要救书,作者也会赌气。
虽说救书,循规蹈矩是不成的,我看他们别有用心,恐怕还是恐吓之后,塞进顾问之类的东西来,吸些鲜血。至于书业要因此凋零之类,他们倒满不在乎,他们连明天也不想,正如败家子的拆卖房屋一样了。
《南腔北调集》既已不能改样,也不妨,至于纸张,其实即用报纸也不要紧(但我想特印毛道林的五十部,以分送朋友),因为这并非宝书,无人藏弆,而即有被扣之事,损失亦少也。
照这样的办法,不知先生与令友,还能印几种否?我所能弄回稿子的,计有四种—
一、《高尔基小说集》,即生活书店印后被禁者,现可添上两篇,抽去一篇,换译者之名,另印。
二、《高尔基论文集》,曾付现代,取版税百元,闻未排,可以收回。
三、《烟袋》,曹靖华译,印过被禁,现已重编。
四、《四十一》,同上。
以上四种,后三种在现代,只要送他一百元,便可取回。第一种可以不成问题。第三四种版税,因靖华穷,最好是先付百元,如经济不够,我的二百元可以从缓。如此,则只要排印及纸张费就可以了。如何希示,倘要,当托茅兄往与现代交涉耳。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二月廿四夜
韩振业(1892-1935)这个名字,鲁迅日记中只出现了五次,但天马书店出现的次数就相当多了。韩振业一九三二年与楼适夷、楼炜春兄弟合作,在上海创办天马书店。据楼炜春在《记天马书店》(刊2008年5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初版《百年书业》)中回忆,天马书店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此信中写到的《鲁迅自选集》,时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同月还出版了知堂(周作人)、郁达夫的自选集,次月又出版了茅盾的自选集,从而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自选集系列。同年三月九日鲁迅日记云:“晚往致美楼夜饭,为天马书店所邀,同席约二十人。”想必是庆祝天马开张出书,韩振业应在场主持。
信中写到的《南腔北调集》,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同文书店初版。同年三月三十日鲁迅日记云“得同文局信并书五十本”,正是指此书,其先后时间倒可与此信相衔接。但已知同文书店是联华书局前身,《南腔北调集》的出版似与韩振业无关,也许鲁迅本拟把此书交天马书店出版,或是韩振业一度参与此书的出版?待考。
至于后四种书,《高尔基小说集》指《高尔基创作选集》,萧参(瞿秋白)译,一九三三年十月生活书店初版,三四两种都是数年前未名社旧版。“现代”则指现代书局,“茅兄”指茅盾。这四种书后均未由天马书店出版,但鲁迅帮助友人之情已跃然纸上。
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纪念
创设于一九二六年的开明书店,虽然不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历史久,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的上海异军突起,尤以出版新文学作品为翘楚。茅盾的《子夜》、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朱自清的《背影》、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和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等名著名译,都是开明推出的。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开明出版的文学著译已达二百六十二种之多,非其他出版社所能及。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是开明创业十周年纪念,该日《申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版刊出整整两大版“纪念特刊”,既有始业宣告,也有十年成绩的统计,既有名家的祝贺、同人的感想,也有普通读者的期望,内容极为丰富。茅盾、林语堂、朱自清、丰子恺等开明作者发表了各具特色的贺词。茅盾、林语堂的贺词均为手迹制版,照录如下:
开明书店,从创办到现在,注重出板文艺书和少年读物。究竟它这努力效果如何呢?我和开明书店的主持人一半是朋友,我的话不好算数。然而要是诸位相信小朋友的话是天真的,那么,我就介绍几位中学生的批评罢:他们喜欢读巴金的小说,也喜欢读开明昔年丛书内的浅近的然而有趣的科学译著。
茅盾 七月廿八日
吾尝谓:李白斗酒诗百篇,是诗赖酒精乃成之证。太白之神兴,太白之精合,而后诗成。前人亦谓:书店系书香与铜臭之集合,商香秀臭合,而后书刻得出来也。商秀调和诚非易事,不是以秀害商,便是以商害秀,盖秀盛则商裹,而香亦不存。商盛则秀裹,而臭气冲天矣。开明书店开办十年,能不屑粗制滥造,不出一本坏书,不欠作家版税,可谓商秀调和得当,在此今日妖魅世界已算难得,善哉,善哉。
廿五年七月 语堂
朱自清的贺词题为《开明的书》,全文如下:
书店的职务在推进文化;其成绩当以出书的精粗为断。开明诸位先生品位既高,又处处谨慎,十年来所出的书决没有滥恶不堪一读的。这该是文化界极大的欣慰。再则开明出书,似乎从开始就特别注重中学生读物。中学生是文化界的基础。基础打得好,才可盼望轮奂之美。在这一点上,开明诸先生的眼光也是值得敬佩的。
二十五年七月
丰子恺的贺词《祝开明十周纪念》也一并照录:
开明十周纪念特刊索“箴言”。我无言可箴,但略书所感,以志祝贺。七十年前,英国有名的工艺美术革命家莫理史(William Morris)曾经纠合诗人画家洛赛谛(Dante Gabriel Rossetti)及美术家彭琼士(Burne Jones)等,创办一个工艺美术品商店,叫做莫理史公司。反对资本商业主义所产生的恶劣的货品,企图以工艺制造的诚意来美化人生而改造社会。从很小的小本经营开始,十年而名震全欧。后竟以社会改革事业著名于世,而在美术史上占有数页地位。开明的过去,在某点上或某程度内与这莫理史公司相类似。这是可欣贺的。希望它本此素志而努力前进,将来成为中国出版界的莫理史公司。
茅、林、朱、丰的贺词虽然角度各有侧重,但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不无启迪。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们四位的全集虽然都已问世,《茅盾全集》还出了两版,但这四篇贺词都未能收入他们各自的全集,都是集外文。而今开明书店早已成为历史,但开明书店的出版经验理应好好追溯总结,这四篇贺词也应补入茅、林、朱、丰的新的全集。
《夸父》签名本
中国新诗史上有才华的青年诗人,而今不少已被人遗忘。这册《夸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汪玉岑著新诗集《夸父》,一九四一年三月出版,版权页上署“出版地点:北平燕京大学”,其实是作者自费印行。自印新诗集往往自有特色。《夸父》封面素朴,白底蓝字而已,书脊印“夸父(新诗集) 汪玉岑著 一九四一”,也很别致。汪玉岑当时是燕大国文系学生,才二十六岁。这本《夸父》是他的处女作,而且是献给他的老师的,题词页印有九个字:“献给 亡师钱朔异先生”。
《夸父》分为“忆”和“夸父”两辑。上辑“忆”为长短抒情诗二十三首,下辑“夸父”收叙事长诗《夸父》和《洋娃娃》。两辑并作者《后记》前有薄透明纸作为辑封,全书又有五帧不同题材的黑白插图,均别具一格。从《后记》中可知,此书装帧设计和插图作者为姚克安。
特别难得的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家、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的郭绍虞为《夸父》写了热情洋溢、鼓励有加的序。序中明确指出:
近来的新诗多看不懂,而玉岑之诗则看得懂;近来的新诗多读不响,而玉岑之诗则读得响。我知玉岑深有此癖习;这即是玉岑诗所以能不同凡响之故。
不妨转引两首短小的,看看郭绍虞的品评是否恰切。先引《归》:
金色的日头如故意滞留在地平线,/飞鸟们闪动着翅膀赶过了远林间,/旅人呀,请暂时放下那长长的鞭子吧!/你底牲口对家园正撩起无名的渴念。
再引一首《撒一把盐入淡海》:
撒一把盐入淡海,/再去喝它个痛快;/回头别忘告诉我,/这滋味像不像“爱”。
郭绍虞进一步认为,到了长诗《夸父》,汪玉岑的诗又显示了其“作风将变之兆”。《夸父》是汪玉岑用新叙事诗的形式来歌颂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人物夸父追日的一生。后来的新诗人中如余光中等,也都写过夸父,但汪玉岑大概是最早的。他的《夸父》共九节,长达三百多行,以第一人称出之,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其艺术特色正如郭绍虞所指出的:“其为音,不复如琴瑟之专一;汹涌如浙江之潮,澎湃,澎湃似地一起而一止;如钜鹿之战,如昆阳之战,鼓噪而前,奔腾而出,于雷声风声之中,呼声也足以震动天地。”
《夸父》问世之后五年,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正在台湾的汪玉岑又在基隆新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新诗集《卞和》,《卞和》也与众不同,分为“卞和集”“红玫瑰集”和“夸父集”三辑。“夸父集”系《夸父》全书加上《信》一首,又删去了可能作者自己已不满意的《夜行》《晓》等十首,作为第三辑收入《卞和》之中。《卞和》仍由郭绍虞作序,再次对汪玉岑“诗的进展”表示肯定。郭绍虞为新文学作家作序,据我所知,仅汪玉岑一人,而且接连写了两篇,这在新文学史上也是颇为少见的,可见他对汪玉岑的器重。
我所藏《夸父》,前衬页有如下的钢笔字:
祥莹学长留念 弟 山岭敬赠
山岭是谁,就是汪玉岑吗?谜底就在诗集《卞和》的《后记》。《后记》落款:“山岭 一九四六年双十节于台湾基隆”。由此可知,“山岭”正是汪玉岑的别名或字号。这册签名本当然令我宝爱。
虽然汪玉岑一生只出版了这两本薄薄的新诗集,但新诗史上是否有可能提一提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