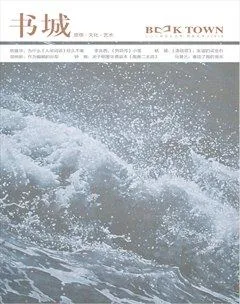说姜夔《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姜夔《扬州慢》
姜夔这首《扬州慢》,在词坛上备受好评。他在词的前面还写有一段序言:“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这段序言值得注意。首先它说明了这首词写于“淳熙丙申”,亦即一一七六年。据夏承焘先生等学者考证,姜夔生于一一五五年左右,那么,这篇可称为代表作的《扬州慢》,是他在二十岁左右时写成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写一段长长的序言,下文再作探讨。
姜夔文笔优美,却一生倒霉。他字尧章,号白石。家贫,早年丧父,只好跟随其姐过活。幸而他诗、词、文俱精,而且又是出色的音乐家,能作曲,擅吹箫。可是命途多舛,屡试不第。他也曾效法周邦彦,向朝廷献上《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却不受重视,自讨没趣。后来,他又献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歌功颂圣的作品。这回皇帝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下诏让他直接参加进士考试。谁知他硬是没有考上,从此一生没有出仕的机会。作为处于底层的文士,他家境贫乏。不错,在词坛上,人们认为他的词风独特。张炎在《词源》卷下“清空”条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他认为“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最符合他推崇的清空风格。这一判断大致是准确的。如果从姜夔的钱袋子来看,他也确属于“清而空”的一类,所以,他说自己“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实际上,他的一生都很凄凉,何止十年。
幸而姜白石在文坛上名声显赫,许多文人雅士、世家显宦,包括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萧德藻甚至朱熹等,都和他意趣相投,喜欢和他结交,常常周济他,并长期请他到府内作为宾客,他拖家带口,有时一住便好几年。在《红楼梦》里,不是有詹光之辈,经常给贾政等老爷少爷们充当吹捧打趣的角色吗?这类人,在元杂剧中叫“帮闲”,在明清小说中叫“清客”。当然,邀请姜白石作为宾客的人士,对他还是相当尊重的。“千岩老人”萧德藻更把自己的侄女嫁与他为妻,还送给他十几亩良田。因此,他与一般的清客又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才华出众而只能寄人篱下的姜白石,内心是极为敏感和酸苦的。尽管他得到朋友的厚待,却也知道自己毕竟是个“清客”。他怀才不遇,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眼看南宋王朝每况愈下,党争激烈,抗金失败,恢复中原的愿望也越来越渺茫,他既没有像辛弃疾那般能屈能伸、恨天无柱恨地无环的英雄气概,也没有像陈亮那样视仕宦如敝屣,敢于嬉笑怒骂的胆识。于是对国运的忧思、对自身命运的失落,种种复杂的情感,像绳索那样牢牢地缠绕在他的心头。在词的创作上,便表现为刻下了或深或浅的伤痕。他在《玲珑四犯·垒鼓夜寒》中写道:“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这几句话,正好是他一生感情的概括。其实,临近南宋末期,在词坛上具有才能而又只能生活在底层的文士不在少数,姜白石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已。
不过,姜白石创作上引《扬州慢》的时候,才二十岁左右,还没有经历多番命运的挫折。因此在这首词中,他对个人命运还未有多少涉及,倒是目睹祖国山河被金人铁蹄残酷地践踏,而南宋王朝又不能恢复失地,不免忧思重重,满怀伤感,于是初到扬州,便写出了动人心魄的名篇。
《扬州慢》的第一组乐句是:“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所谓“淮左”,是指扬州的地理位置,隶属宋朝所设淮扬东路的东方,东属左,故称为淮左。而扬州,早在唐代已经是东南的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城市繁荣。到北宋时期,虽经唐末战乱,但很快恢复,手工业、商业、农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第三大都市。姜白石说它是著名的都会一点不假。跟着他下“竹西佳处”一句。“竹西”,是指扬州著名的风景区竹西亭,亭子就在禅智寺的旁边,这一带景色优美,可以代表扬州的名胜。请注意,姜白石首先以“名都”“佳处”形容扬州,可见扬州是他无比向往的地方。他以为来到扬州,可以赏心乐事,饱看美丽和繁华的景象。他也知道唐代的才子杜牧,也曾在《题扬州禅智寺》一诗中说过:“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所以,当他踏上扬州的地面,便“解鞍少驻初程”,准备饱览一番这里的胜景。这时候,他的心态也和杜牧所说的“停车坐爱枫林晚”一样,希望获得最美的享受。谁知道他后来看到扬州的一切,竟和他心目中所想象的完全相反。因此在这全曲开始的乐句,他把扬州的地位和景物高高举起,实际上是为下文对扬州破败的描写作铺垫。
这词的第二乐句是:“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姜白石也知道,杜牧在《赠别》一诗中曾经写过:“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在唐代,扬州路上春色无边,十里长街处处是歌楼妓院。杜牧说,所有妓院的女子,都卷上了珠帘来窥瞧他,但她们都不及他意中人那么美丽。现在姜白石所看到的,竟然和杜牧大不一样。不错,他也走过了扬州的十里长街,依然有春风吹过,但是这道路上的春风,已经不是杜牧所经受过的香风了。过去的繁华无影无踪,他所看到的尽是青青的荠菜和小麦。在这里,姜白石下一“尽”字十分重要,它是指除了植物什么都没有,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与他原来以为是“名都”“佳处”的憧憬完全相反。原来热闹的地区,现在长满了植物,这凄清的景象,又有暗喻“黍离”之悲、亡国之哀的含义。显然,这乐句和前面的乐句,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让读者脑海中的审美意象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上片的第三组乐句:“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这简单的一句,说明了扬州凋零破落的原因。据知,金兵曾两次攻入扬州,一次是在一一二九年,另一次是在一一六一年,两次都给扬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姜白石在创作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直接写当年的扬州怎样被金兵烧杀抢掠,而是只写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金人的残暴和战乱的阴影,依然长期地笼罩着整个扬州。这样的写法,比直接描写当年扬州人民悲惨的遭遇,更能引起人们心中的痛苦。在现实生活中,隐约说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往往比直言当初遭受的酸楚,在内心更会产生难以言喻的隐痛。陈廷焯说:“‘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见《白雨斋词话》卷二)这是深谙人生经历之谈。只有如此,才领悟姜白石似乎是淡淡写来的真意。
其实,陈廷焯对姜白石在这一乐句的写法,还有未能说得清楚的地方。以我看,就“废池乔木”一句,从“胡马窥江”的结果来看,它是指扬州遭受金兵的蹂躏,以致多年以后,姜白石所看到的,只是些因没有人管理而荒废了的池塘,以及高大扭曲的树木。这一句,属于前句的受体。但是,若从后句“犹厌言兵”的关系来看,它则是主体。姜白石把“废池”和“乔木”(也可以理解为生长在废池边上的乔木),看成是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物体。作者让人感知,就连那些经年累月被荒弃了的东西,到如今也仍不愿意谈起战乱的往事。言外之意,正如南北朝的庾信在《枯树赋》中所说:“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悽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很清楚,在这乐句中,姜白石以“废池乔木”为中介,既表现了扬州被金人摧残的惨象,又说明这里的一切,包括人和物,对战祸都有不堪回首的悲哀。这一来,简单的乐句包含着复杂的意象,姜白石让作为审美受体的读者,通过视觉,从“废池乔木”中启发自己的想象力,从而看到扬州经过战乱后的景况。
《扬州慢》上片最后的乐句是:“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承接前句,姜白石写太阳下山,天色变得昏暗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中,他听到了号角的声音。
其实,作者在创作时,该用什么意象以展示现实,是可以选择的。唐代的张继有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不就是以钟声来表现夜色,并且对人们有所警示吗?至于姜白石在夜色将临的时候,选择写听到了号角的声音,也有着独特的意味。当年,战乱虽暂时停息,但宋金还处在对峙的局面。当夜色渐浓,兵营或官衙会吹响号角,让人们有所警惕。这就是姜白石为什么把他听到的声音,设定为号角而非其他声响的意义。再者,他把号角形容为“清角”,显示它发出的声音是“清”而非壮,这表示城里还有一些戍守的兵丁孤零零地存在,扬州还像处于战时的非常状态。
更值得注意的是,姜白石写“清角”吹出的声音是带着寒意的。本来,号角吹出来的声音只是声波,进入听者的听觉,并不会让人在触觉上产生“寒”的感受。只是音波进入人们的听觉,大脑皮质细胞受到刺激,触发脑海中其他区域的活动,才会让人们从听觉引发触觉上的寒意。这种从心理的“寒”转化为生理的“寒”,更能表现出作者凄凉的感受。在扬州,姜白石看到战乱过后的情景,有所感触,因此号角吹出的声音让他感到寒冷。进一步,姜白石还加上“都在空城”一句,他让读者知道,这号角声除了让他感到寒意以外,也会传遍整个扬州,会让人们觉得寒风飒飒。可是,现在的扬州杳无人迹,只剩下一座空城了。这一来,兵丁吹出的悲凉的号角声,也只能是空荡荡的回响。显然,在这一乐句,作者通过听觉,让读者感受到扬州在战乱后悲凉的状态。
在过片后,姜白石把杜牧曾经到过扬州的故事直接端了出来。下片的第一组乐句便说:“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所谓“杜郎”,明指唐代诗人杜牧。作者知道杜牧来过扬州,并且很喜爱扬州繁华美好的生活。跟着他又说:“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过去,杜牧曾写过赞美和描写扬州浪漫生活的名句,如“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姜白石认为,如果热爱扬州的杜牧现在再来扬州,即使他笔底生花,也难以再写出深情的诗句了。这一乐句,言外之意是,连有才华、喜爱扬州的杜牧,面对扬州如今损破的状态,也势难着笔。请注意,姜白石在这首《扬州慢》里,从词的开始,便处处运用杜牧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下片的开始,还直接把杜牧端了出来,这说明他对杜牧的崇拜。他在《鹧鸪天·十六夜出》一词中说:“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在《琵琶仙·双桨来时》一词中又说:“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简直是在以杜牧自喻。可惜,他或有杜牧的才,却没有杜牧的命。当年杜牧任职分司御史时,能够“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时回”,过着显贵而又浪漫的生活;姜白石则一生寄人篱下,去世时贫不能葬,只能在朋友的资助下草率入土。
紧接着,姜白石回过头来,写他在扬州看到的夜景:“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这一组乐句,依然从杜牧写过的名句入手。当年,杜牧写过《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诗中说:“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表现出风流优雅的情调。姜白石在这一组乐句里,也写他在扬州之夜,看到了这曾被杜牧写过的“二十四桥”,而且也是在明月之夜,但是景象完全不同了。“二十四桥”依然存在,却听不到玉人的箫声了,只看到桥下的水波在轻轻地荡漾,月影冷冷地无声地照着。这组乐句被一些论者视为名句。清代的先著认为,在这句中,是“‘荡’字着力。所谓一字得力,通首光彩,非炼字不能,炼亦未易到”(见《词洁辑评》卷四)。他从炼字着眼,认为以“荡”字表现波水轻轻流荡的形象,十分生动。这意见可供参考。其实这乐句之所以被视为佳句,还不只是炼字,使句子显得生动的问题。姜白石在《庆宫春·双桨莼波》里,也有过“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的句子,所用的“荡”字便不见得有多出色。至于在《扬州慢》中,下片的这组乐句之所以值得欣赏,首先是写二十四桥下波心的水轻轻荡漾,显得这里是一片寂静,连影照到波心的月亮也显得十分清冷。这让作者觉得这平静的波澜,竟然“荡”在天空中的月亮之上,连月亮也觉得寒冷。本来波澜是不可能飘荡到天空中的,明月也不可能发出声音,更不可能有冷和暖的感觉。而当下,作者这出人意料的大胆想象,更能启发审美受体对扬州夜色的悲凉感受。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这乐句之所以让人注目,也是由于它能引起读者对扬州过去繁华和如今凄寂的联想。姜白石在这组乐句中,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把杜牧笔下的扬州夜色,和当下他见到的扬州,作了鲜明的对比。在杜牧的笔下,二十四桥,明月在天,乐声荡漾。姜白石则有意突出“二十四桥”当下的景色,从而引起读者的种种联想。显然,这组乐句之所以成为被人称誉的警句,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只以炼出一个“荡”字所能概括。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这是《扬州慢》整首词最末的一组乐句。红药,就是芍药,花色鲜艳。姜白石看到了它,生长在二十四桥的旁边,于是不禁想到,这花年复一年地生长,原本要供人欣赏,可是,经过战乱,十六年来已杳无人迹,只剩空城。那娇红的芍药,早已无人能见,它徒然在桥边年年生长,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写法,和他在《八归·湘中送胡德华》一词中所说“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得更为含蓄而已。
综观上引《扬州慢》,姜白石在整首词中一直运用烘托的艺术手法。就对空间的展现来看,他处处使用清冷凄寒的色调,像写荠麦的青青、黄昏的灰暗、水光月色的幽冷等,可是在词的最后一句,却出现了“红药”。红色,属于暖色,它的出现,和词的总体色调构成对比,让读者更加感到整个扬州笼罩着凄冷的氛围。
更为奇妙的是,就时间的展现而言,姜白石既写他看到扬州当下凄凉惨淡的情景,又一直运用和贯串着杜牧曾经写过有关扬州美好的诗篇,这又等于把古与今的状态互相烘托,从而让读者更加感悟到当下的扬州产生了悲剧性的变化。这样的艺术处理,就像我们听到一首交响乐,它的旋律总体是新创的,但在某些乐句或在和声部分,却又出现人们所熟识的乐音。这复杂的音形,扭结在一起,让听众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从而获得了难以言喻的感受,这就是词的魅力。
姜白石是音乐家,他写的词,除了小令,一般仍用传统的词牌外,若写长调,一般都用“自度曲”。所谓自度曲,就是作者自己创作的曲。上引《扬州慢》就属自度曲,是在传统词谱中没有出现过的词牌。
按照词坛传统的做法,词是用来唱的,词牌也就是具有音乐性的曲谱。当作者作词的时候,必须按照词牌规定的字句长短和平仄,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文字填写上去。这一来,审美主体往往受到了审美载体的束缚,不能尽情抒发。这词牌的音乐性,反而影响了作者创作在语言上的自主性。姜白石写的所谓自度曲,和传统填词的方法刚好相反。据他自称:“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见《长亭怨慢》小序)说白了,姜白石的自度曲,其创作过程,与现代歌曲的创作大致一样,都是作家先写了歌词,然后才由作曲家根据歌词的思想感情以及语言的声调,谱成歌曲。像《黄河大合唱》,不就是由光未然先写了诗篇,然后交给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后者经过几天的阅读深思,触发灵感,才写出了惊天动地的歌曲吗?
姜白石之所以创作自度曲,是要求曲谱的音乐性,能够和审美主体所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相吻合。像他创作的平韵[满江红],就是根据祭神的需要,把原来仄韵的[满江红]改为平韵。因为仄韵一般比较短促,而平韵的发声可以悠扬,在音乐性方面,更能让歌唱者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在[满江红]句子字数不变的前提下,姜白石改变其节奏和旋律,这当然属于他创新的自度曲。在《满江红·仙姥来时》的前面,他写了一篇序文,记述此曲创作的原因和过程:“[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闻远岸箫鼓声。问之舟师,云:‘居人为此湖神姥寿也。’予因祝曰:‘得一席风径至居巢,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
这段话说得很神奇,其实他知道仄韵的[满江红]上片最末一句的声调很难和语言协调,又知道要用它来送迎神仙,若使用仄韵,不如使用平韵能够把声音拖长,可以表现出信众虔诚的心态。显然,把[满江红]改成平韵,完全是为了“协律”,亦即使词在语言上,能够和乐曲的旋律互相协调。这就是先写了词的内容和文字,然后再谱曲。显然,平韵[满江红]也属自度曲。
就古汉语声调的四声而言,人们认为四声有不同的表现力。在四声中,“去声分明哀远道”,去声的音值向上飘忽拖长,能够在听觉上产生悠远的效果。正如万树在《词律》中指出:“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姜白石的自度曲《扬州慢》,明摆着是属于节奏舒缓的“慢词”,因此在词中,他多用去声的字,我们算了一下,如:处、驻、过、尽、自、去、后、废、厌、渐、在、杜、俊、算、到、纵、豆、蒄、梦、赋、四、在、荡、念、为等,在全首词的九十八字中,去声字约占全篇字数的四分之一。显然,就语音的悠扬跌宕而言,这更能表现姜白石目睹被金人蹂躏后的扬州,无比感伤的情绪。
为什么姜白石要创造自度曲?其原因无非是由于传统填词的做法是先有词谱,然后作者按照词谱规定的旋律和节奏填上词的文字语言。这样做必然会束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自由发挥。当时的宫廷音乐,使用了不同的乐器甚至以外来传入的乐器演奏,“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本根,失之太清……沉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见《宋史》乐志六)。显然,姜白石认为要让听众听得清楚是最为重要的。他又在《白石诗说》中指出:“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他强调诗词创作最重要的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语言的优雅。易言之,如果按照传统按谱填词的写作方式,首先考虑词谱的旋律和节奏的音乐性,然后据此表达作者的情意,那么必然会对意和句的运用有所束缚,这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受体来说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姜白石在创作时,便先写词再配曲。而且他还把这些自度的曲,亦即由他新创的曲加上了相应的曲名,例如写扬州就把这词谱名之曰《扬州慢》,写梅花则把词谱名之曰《暗香》《疏影》等。
在宋代的词坛上,一般作者都要按谱填词,稍微出格就会受到讥讽。苏东坡有些词作,某些句子和词谱不相协律,便被李清照讥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当时,懂得音乐的词家还是有的,如周邦彦等,但大都依律填词,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些词人也懂作曲,但未必熟谙如何把诗意和乐谱结合起来进行写作。姜白石在《玉梅令》序中写道:“石湖家自制此声,未有语实之,命予作。”在《庆宫春·双桨莼波》序中也说:“朴翁以衾自缠,犹赋此阕,盖过月余稿乃定。”这也表明,把新创的乐曲与词语交融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必须兼具音乐才能和文学才能的作家才有所成。
姜白石采用自度曲的做法,就是把最能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放在第一位,然后再创作能够更好地表现和衬托思想和感情的乐谱。在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有些唱词,被一些人认为不能和曲谱的音律配合。汤显祖《答吕姜山》一文做出回应,他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很明显,在创作曲文时,汤显祖是把语言的意趣神色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斤斤计较某些词语是否符合曲谱音律的问题。姜白石创作自度曲,其动机实际上和汤显祖是一致的,都是把人情和人性从词谱和曲谱中解放出来。只不过汤显祖是敢于突破乐谱的约束,而姜白石则索性是先写词后作曲。这对宋词的发展,无疑有着推动的意义。
上面说过,《扬州慢》是姜白石二十岁左右时的作品,显然,这可视为他创造自度曲的尝试。由于这是具有创新性的写作方法,因此我们看到姜白石在词中使用了较多作为介词和连词的虚字,这些虚字又多在乐句中起着引领的作用,像自、算、渐、纵、念等。这些虚字的运用加强了整首作品在抒情中的叙述性和连贯性,让读者和听众对这以新的形式出现的作品更加容易理解。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指出:“若能尽用虚字,句法自活,必不质实,观者无掩卷之诮。”姜白石之所以大量使用虚字,正是为了让听者、读者和唱者听得清楚、看得明白。
我们还注意到,姜白石所写的自度曲,前面都会写有一段序言,说明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这首作品的。在《扬州慢》里,他甚至详细地说明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和情感。我们知道,在宋代的词坛上,起初,多数词作者只在作品中写上词牌,一般是没有题目的。到北宋中后期,有些作家会在词牌的后面加上一个标题。像苏轼的《江城子》就有《密州出猎》的小题目。到了南宋的中后期,有些作家在词牌的后面还会加上稍长的序言,说明他在什么情况下创作了这一首词。但是,总不会像姜白石的《扬州慢》那样,把创作的时间、作品的主题,以及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写得如此细致明白,其字数竟达六十三字之多,实际上已经是一篇小作文了。对此,词坛上有些论者是颇有看法的。周济说:“白石小序甚可观,苦与词复。若序其缘起,不犯词境,斯为两美已。”(见《宋四家词选序论》)他的意见,有说得对的地方。但是周济没有考虑到,姜白石的自度曲,特别是较早呈现在听众耳畔的《扬州慢》,没有采用人们熟识的乐谱,演唱时,习惯旧谱的听众会听得懂吗?能够接受吗?为此,姜白石只得以散文的形式写了小序,这有助于人们对这首作品的理解。我认为,姜白石以散文和词作结合在一起,是他争取让自度曲这一创新的写作方式能够在词坛上立足的做法,而不是画蛇添足。
姜白石从写《扬州慢》开始,便经常以自度曲的方式进行词的创作,这显然得到了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也是他在词坛上名声大振的原因之一,连范成大、辛弃疾等名声显赫的人士,也喜欢和他交往唱和。不过以自度曲的方式写词,既需要有文学的才能,又需要精通音乐,对词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难题,这也是姜白石在词坛一枝独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