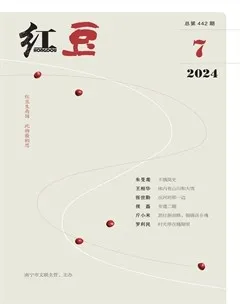两幅简笔画
1
人民路上有好几家修脚店,室内布置大同小异,靠一边墙放几张可以调节升降的修脚椅,对面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锦旗。王一刀修脚店有一点儿与众不同,室内没有锦旗,在偌大的一面墙上只挂了两个小小的画框,里面装裱着A4复印纸。画框玻璃映着光,像两只睁开的眼睛,常常引起顾客的注意。纸上只简单地画了几笔,有好奇的顾客就问王宝忠:“这是不是你家孩子的简笔画?”王宝忠话少,只是习惯性地抬起修脚刀一样瘦削的下巴咧嘴笑笑。他一咧嘴,脸上便出现两条大弧线,像撇开的括号。王宝忠从不对顾客说这两幅简笔画是丈母娘的遗书。
2
王宝忠的丈母娘患有糖尿病,退休后视力急速下降,尤其是左眼,看啥都重影。她的大儿子李青松说:“那好,数钱一张变成两张。”
李青萍带母亲到医院检查,发现是白内障,需要做微创手术。李青松是一家国企的副总,讲话时习惯左手叉腰,右手高高举起,几根手指像鸟喙一样啄着空气,他说:“一大把年纪,房子有你住的,退休金每月按时打到你的账上,又有儿有女。放着福气不享,炒什么股票?天天盯着电脑,眼睛不坏才怪。”
手术安排在晚上。李青松说晚上有个会,不管几点钟做完,打个电话他开车来接。李青萍说:“哥,你去忙,别耽误了工作,这里有我和宝忠呢。”
做罢手术已经是半夜十一点了,丈母娘让王宝忠给李青松打电话。王宝忠说:“我们打的士回吧。”丈母娘说:“为什么要打的士?你给青松打电话。”王宝忠就拨打了李青松的电话,按了免提。电话里传出李青松的声音:“宝忠啊,你看看这都啥时候了,你就不会打个的士?有我开车跑过去这工夫,你打个的士早就把被窝焐热了,是不是?妈老糊涂了,是个人都会算账,打的士多省事。我明天上午有个会,你辛苦了。”
王宝忠搀扶着丈母娘往外走。出了病房大楼,他们忍不住缩了缩脖子。风从耳边吹过的声音,就像大人给孩子把尿时嘴里发出的嘘嘘声,灰色的塑料袋像鸟一样在空中盘旋,树叶在脚下翻滚的声音,和在铁锅里炒菜的刺啦声一样。王宝忠赶忙脱下外套给丈母娘披上。丈母娘左眼蒙着纱布,此刻右眼也闭上了,耳朵也闭上了,嘴巴也闭上了。
王宝忠听见丈母娘呼呼的出气声和半夜的风声一样急促。
3
那天早晨,丈母娘站在床边时,感觉室内的物品像全有了生命一样晃动起来,在倒下去的那一刻她抓起了床头的手机。
重症监护室外,李青松的脸拧得像包子褶儿。他一边举起右手敲击空气,一边痛心疾首地说:“那些教授博士经济学家炒股都亏,她一个只读过高中的普通人炒什么股票!把那点儿积蓄存在银行吃利息不好吗?留给儿子孙子不好吗?请个保姆享清福不好吗?”李青萍说:“妈还不是想多赚一些钱补贴儿女?她又能花多少?”李青松说:“问题是现在不仅仅亏了钱,人也中风了,开颅手术就得一大笔费用,医生说她以后离不了人伺候。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她会拖累一家人的,最终结局是人财两空。”
丈母娘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医生反复强调:“病人这段时间处在昏迷状态,至少得两三个人轮流看护,不超过两个小时就得喊醒一次,多和她说说话。她虽然不能说话,但是能听见。”李青萍请了一个有经验的护工,给母亲抽痰、翻身、喂流食、换护垫。护工说:“我一个人是看不过来的,每晚总得打个盹睡个觉。你们再雇个护工吧,两个人可以轮换。”李青松把大伙儿叫到走廊尽头,说开个家庭会讨论一下。李青萍说:“你是大哥你拿主意。”李青松扫了大伙儿一眼,说:“雇八个护工都抵不上一个亲人,我们暂时只雇一个护工,由我们几个轮流排班给护工换换手。我是老大,我排第一个晚上,青萍排第二个晚上,青海排第三个晚上。”李青萍说:“还有宝忠。多一个人多一份力。”王宝忠咧嘴点点头。
在第四个晚上,王宝忠让护工先睡。护工说:“我这些年照看的病人,啥样的家庭啥样的人都见过,你这样的女婿比儿子还孝顺。”王宝忠咧咧嘴说:“哪儿有儿子不孝顺的?”护工拍了一下大腿说:“你们老大就不如你。你抓着丈母娘的手不停地和她说话。他一直待在走廊连病床都不碰一下。天擦黑他就走了。”王宝忠说话不会拐弯,见到李青松就直接问:“你值班时咋不在医院睡觉?”李青松背着双手,说:“有一个专业的护工在这里,抽痰、翻身什么的我都不会做,还有必要守着吗?再说了,我有高血压,不能熬夜。妈中风后肯定偏瘫,她生命已经倒计时了,如果把一个好端端的人也拖累得偏瘫了,是不是不明智?”王宝忠像刚被捞出水的鱼一样张着嘴巴,不知道说什么好。
丈母娘苏醒后脱离了危险期。李青松走进医院时眉毛总是揪成疙瘩,埋怨多,他每到医院站几分钟就匆忙离去。老三李青海在另外一座城市上班,隔半个月回来探望一次。
为了缓解呼吸困难,医生给丈母娘做了气管切开术,喉咙外面插着导管。她想讲话时,嘴唇像喇叭一样张开着,含混不清的声音像拉风箱一样从导管里呼呼窜出来,而且不断被痰堵塞。医生说:“病人迫切想讲话,你们可以让她写字,她右手能动弹。”王宝忠买了一包A4复印纸和一个板夹。当一串呼呼的声音扫落叶一样跑出来时,他赶忙把板夹举到丈母娘面前,将圆珠笔塞到她手里。
丈母娘每天都写,她有一肚子的话要急着说出来。她写的每一个字都四分五裂,醉汉一样东倒西歪,而且忽大忽小比例失调,往往三五个字就把一张纸写废。她写罢了,便眼巴巴地望着床前的亲人,期待他们能够看懂。有的字大家能看懂,有的字大家看不懂。大家像哄孩子一样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同时又像小时候围着妈妈猜谜语一样,纷纷去揣摩她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猜对了她就笑,猜错了她就一脸的失落。
丈母娘在白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笔,是个散了架的 “月”字。丈母娘又在右下角画了一条线,明显力不从心,线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李青松说:“妈想问什么日子。”丈母娘的眼睛一动不动。李青萍说:“妈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吃胖一些?她看我们都瘦了。”李青海勾着的脑袋像吊着个皮球,满是内疚地说:“妈在责怪我半个月才来看她一次。”王宝忠接过板夹,颠来倒去琢磨了好一阵儿,说:“妈想写个‘股’字,还操心股票呢。”李青松拧着眉毛盯了王宝忠好一阵,说:“真没想到,还是宝忠聪明。”他把大伙儿叫到病房外面,强调为了妈的身体,都得装糊涂,谁也不能和她提股票。
丈母娘在纸上画了一根竖线,又在竖线上面打个叉,大家都猜不出她的意思。因为丈母娘重复画了好几次,大家就抓破脑壳使劲猜。李青松眯着眼微微点着下巴说:“妈先画一根竖线,再打个叉,意思是人终有一死,让我们都看开一点儿。”李青海的后脑勺上像藏着虫子,几根指头一直挠着,说:“妈画的是射线,意思是儿女大了,不管朝哪个方向都是从母亲身边走出去的,不管走多远都要回到母亲身边。”李青萍拍拍手说:“你们是不是想复杂了?妈画的是一个‘米’字,可能就是饿了想吃米饭。等她能咀嚼了我给她蒸香喷喷的大米饭。”说罢又用胳膊肘磕磕王宝忠,王宝忠像睡着了突然被叫醒一样身子一颤。几个人都把目光聚拢到王宝忠瘦削的下巴上,他的嘴巴紧绷着一动不动,脸上的“梯田”难得平整。王宝忠摇摇头,咧开嘴,脸上立即堆出“梯田”的断层。李青松看着王宝忠的嘴巴像贝壳一样打开又合上,说:“依我看只有你能懂。你再看看,妈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丈母娘转到康复科做了一个月的康复治疗,顺利取下了喉部的导管。虽然只能含混不清地说几个字,但终究能通过嘴巴发音了。医生说下一步要进行站立训练,大致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王宝忠凑近李青萍说:“医保之外的医疗费、护工费你们三个儿女平摊了,但出院后的轮椅、拐棍、康复站立架、护理床怎么办?”李青萍说:“亏你问得出口,这能要多少钱?”王宝忠说:“大大小小加起来得两万多元,我修一双脚才五十元,这得我弓着腰低着头修四百多双脚,就算一天修十来个人,我也得修一两个月。”李青萍说:“宝忠你想想,大头我们都分担了,这一点儿我和你就承担不起吗?”王宝忠的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插入头发里,瓮声瓮气地说:“老大、老三的条件都比我们好,他们都有单位。我们呢,关一天门就少一天的收入。我们挤一挤也不是承担不起,关键是老大、老三连吭都不吭一声。”李青萍说:“我们多承担一点儿,哥哥弟弟也不是傻子,他们心里有数的。”王宝忠的喉结像颗珠子接连滚了几下,说:“就怕他们一直当我是傻子。”
4
当丈母娘进行站立训练时,大伙儿就开始商量出院后的事情。李青松抬手往后脑勺压着头发,说:“我想把妈接到我那儿,只是我要上班,文山会海的身不由己。”李青海用双手撑着下巴,说:“如果不是要还房贷我就辞职回来专门照看妈。我在外地上班,鞭长莫及,平时顾及不了,我只能按比例分担医疗费用,一分不会少。”李青萍左看看右看看,说:“我和宝忠开个修脚店,妈住院这几个月老是关门,再这样下去生意怕要黄了。”王宝忠的声音勉强能让大伙儿听见,他说:“要不还是雇个护工?”李青松立马挥挥手:“不行不行,后面又不需要抽痰呀翻身呀什么的,护工的工资高倒是小事情,问题在于请八个护工都抵不上一个亲人。”李青萍叹口气,说:“唉,看来只有我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李青松的目光落在李青萍身上,说:“青萍是照看妈最合适的人选,女儿家心细。宝忠也心细又有力气,可以帮忙挪动。”李青萍说:“这都没有问题,只是我们住的是老式板楼没有电梯,妈上下楼不方便。”李青松说:“这好办呀,让妈住你们店里,你们修脚店在马路门面上,再方便不过了。”
回到店里,王宝忠问李青萍:“咱们店面就这么大,外面一间门脸当了操作间,里面一间当了仓库兼厨房,你说咋拾掇?”李青萍说:“我们可以找房东说说,看能不能换一套大点儿的。”王宝忠说:“装修费暂且不提,还得看房东同意不同意。”李青萍说:“我想请住建局的马科长帮忙打个招呼,房东找她帮过忙,这个情面肯定会给的。”
马科长是一个爱美的女人,她容忍不了右手大拇指上的那只灰指甲,平常在外面吃饭都不好意思伸筷子;左脚上也有一只灰指甲,夏天不敢穿凉鞋。经过几个月的修护,手上的灰指甲好了,脚上的灰指甲还看不出痊愈的苗头,她就有一些焦虑。王宝忠说:“脚指甲在封闭的环境里,活动量也没有手指甲多,生长速度最多能达到手指甲的三分之一,就像楼房北面背阴的树总是没有南面向阳的树长得高长得快,所以你要有足够的耐心。”马科长笑着点点头:“你说得蛮有道理的。向阳的树是亲儿子,背阴的树是女婿,从母亲那里洒下来的阳光肯定是有区别的。”王宝忠咧咧嘴,说家家都是这样。马科长说:“也不一定家家都这样,比如你这个当女婿的比当儿子的还孝顺,将来丈母娘的遗产肯定会多分一些给你。”在马科长的帮助下,房东答应给他们调了房子,新房子前面有一个门脸,后面有两间仓库。
在丈母娘出院之前,王宝忠几乎花光了手头的积蓄。他抓紧时间装修好房子,在里间专门给丈母娘准备了卧室,并且配备了带马桶的卫生间,马桶周边还安装了防滑扶手。在医院待了几个月的丈母娘坐上轮椅,被推进装饰一新的修脚店时,抓了王宝忠的手,嘴唇像筛糠的筛子一样抖动着。
5
转眼之间,丈母娘出院快两年了。邻居们都熟悉这个规律,白天,只要有太阳王宝忠就会把丈母娘推出来晒晒。阳光特别强的时候,王宝忠会将轮椅掉个头,让丈母娘的后背晒得热乎乎的。没有顾客的时候,王宝忠会搀扶着丈母娘偏瘫的左胳膊,让丈母娘用右胳膊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练习走路。晚上,王宝忠和李青萍轮流住在店里照看她,给她麻木的肢体一遍遍按摩。
那天晚上打发走最后一个顾客,王宝忠拉下卷帘门,转身给丈母娘端了盆热水泡脚,给她按摩脚板。丈母娘说:“我有一个事情要你帮忙,不能告诉青萍他们几个。现在我最信得过的也就你一个人了。我的银行卡和笔记本电脑都锁在抽屉里,得有人去拿过来。唉,就怪我,炒股票不仅亏了血本,还熬坏了身体,拖累了一大家子。如果我不炒股,这么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存款也有七位数了。七位数的存款如果能回来,我会把这些钱都留给你和青萍,我那两个儿子是白眼狼。可惜呀,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王宝忠说:“大哥、小弟都好着呢。”丈母娘苦笑着说:“好,好,好个屁!我住院时,青松他从来没有像你一样抓着我的手跟我说过一句话,我知道他嫌弃我。他每次到医院都是做样子给外人看的。”王宝忠不吱声,挺了挺身子,背过两只手捶自己的腰。丈母娘偏着脑袋说:“我知道你长年累月修脚落下了腰椎病、颈椎病,你不嫌这儿疼那儿疼,还要坚持每天给我泡脚按摩。青松他连个护工都不如,从来没有站在床边给我擦过一次口水、喂过一口饭、洗过一次脚,更没有一个晚上照看我。我把他拉扯大了,他的良心却让狗给吃了。”王宝忠说:“大哥工作忙,他说只要有时间会开车带你到广场、江滩、公园玩呢。”丈母娘望着天花板,苦涩地笑着,说:“听他的话明天就过年,他是八十岁的老头儿叨九十斤的烟锅——嘴劲。如果没有青萍和你,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她说着说着眼角就混浊一片。
王宝忠从丈母娘那套房子里取了笔记本电脑,趁着李青萍下午到学校开家长会给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打了电话。客户经理很快就赶了过来。登录交易账户后,客户经理的嘴巴张得像个鹅蛋那么大,他问:“阿姨您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有登录账户了?”丈母娘说:“有两年多了,孩子们不让我碰电脑。这不是突然想起来了吗?我今晚脱了鞋子可能明早就穿不上了,得赶紧把这账户打理好了。”客户经理说:“阿姨可别这样说,您儿子这么孝心,您精神气色也好着呢。我现在还要祝贺您,您是股神啊!瞧瞧您满仓的这只新能源电池股票,虽然价格回调了百分之二十,但净利润还是足足翻了十倍。这真是一个典型的投资案例,对我启发太大了!”客户经理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却没有看见她已经靠在轮椅上僵住不动了。王宝忠捧着丈母娘的脸颊,用右手大拇指掐她的人中,看她眼睛动了动、喘不过气的样子,赶忙扳过肩膀让她靠在自己左胳膊上,右手拢成空心拳轻轻给她捶背。
客户经理走后,丈母娘仍旧半张着嘴巴喘气,她无法看清资产表里的数字,那行红色的数字像针尖扎出的一排血点。她用颤颤巍巍的手指着屏幕,对王宝忠说:“你把表格中那些红色的都读给我听。”王宝忠就把红色的数字逐一读给她听。她垂下眼皮半张着嘴巴像睡着了似的,口水不断溢出,王宝忠不停地抽出餐巾纸给她抹去吊在嘴角的黏液。丈母娘思索了很久才抬起眼皮,说:“我这些年投了一百多万元,总是小赚大亏。那次遇到上千只股票连续跌停的大股灾,我的账户一口气亏得只剩七万多元了。我就想黑夜的尽头是曙光,挺过去了就是一片光明。我豁出去了,把最后的十万元又加了进去。苍天有眼,现在账户上有一百六十七万元,算来算去我赚了几十万元。明天上午开市后,你按我说的全部清仓。”王宝忠问:“不瞒着了?”丈母娘说:“还有啥好瞒的?都瞒不了。”
第二天上午还没有开市,丈母娘就指挥王宝忠打开交易软件,以大幅低于昨天收盘的价格委托卖清仓。王宝忠看见丈母娘像打摆子一样身子一颤一颤地抖着,怕她冷。丈母娘说:“冷啥?我是紧张。”股票在集合竞价时间全部成交,减去当天股价下跌的金额以及手续费,净资产还有一百六十多万元。丈母娘犹如卸下了千斤重担,绷紧的脸庞渐渐松弛,她说:“这笔钱明天就能转到银行卡上了,你们给我记住,以后谁都不能再碰股票。”
丈母娘午睡时,李青萍对王宝忠说:“妈悄悄给我说了她炒股赚钱了。她说先给我们十万元补贴门面装修,剩下的钱都存在卡上,以后看病不要儿女再出钱了。”王宝忠说:“她的钱她想咋花由她说了算。”李青萍笑着说:“妈像个孩子呢,她不好意思对你说。她说她前几天刚给你说过一些话。”王宝忠说:“我只当她和我唠闲嗑,不管她给钱不给钱,我该做啥还是做啥。”
一个星期天,儿女都到齐了。李青松说:“妈把我们都叫齐了,有啥要紧的事快点儿说,我下午还有个会,不能耽误久了。”丈母娘坐在轮椅上缓慢地转动脑袋环顾一圈,说:“我现在是过一天少一天,趁还能说话的时候得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了。我这几十年抠抠搜搜省吃俭用,炒股票又踩了狗屎运,不仅回了本,还赚回了利息。现在我的银行卡上有一百五十万元,这个钱让青萍暂时保管着,留着后面我看病买药,以后不再让你们出钱。哪一天我走了后,卡上剩下的钱由你们三家平分。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一个都不会偏袒。”李青松听了母亲的话立刻板了脸,他清了清嗓子上前一步抓了母亲的胳膊说:“不是我这个当儿子的非要当着你的面批评你,你怎么能够说出这种糊涂话?你这样说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儿女不负责任。嗯,看看你现在身体多好,思路多清晰。如果不是坐在轮椅上,只看气色,谁能相信你是一个中过风的病人?有很多医学无法解释的例子,一些病人心放宽了病不知不觉就好了,说不定就有啥奇迹在你身上发生。”丈母娘像是困了,头靠着轮椅上的枕头,眯着眼睛,轻声说:“那都是哄小孩儿的话。”李青海听了母亲的话像只受到惊吓的兔子,身子猛抖一下,也上前一步抓住她的另一只胳膊,说:“大哥讲得有道理,妈你真是想多了,话可不能像你那么说,你太悲观了。那笔钱你该咋花就咋花,吃好喝好开心就好,你生病住院我们几个还能不给你出钱呀?”李青萍抽出一张餐巾纸,擦去悬在母亲嘴角的口水,说:“妈只是当面给哥哥、弟弟说清楚,让我们都知道她是一碗水端平。”李青松说:“嗯嗯,理解理解,妈一向是公正无私的。”李青海看了哥哥一眼,又看了姐姐一眼,说:“妈生病住院啥时候我们几个没抢着拿钱?还用存一笔钱操心看病买药吗?如果说出去别人准会笑话我们这些当儿女的,好像我们不管老人家似的。依我看还不如早点儿把钱分了,我也能提前把房贷还清,没了还贷压力我就能辞职回来多陪陪妈。”李青松当即接过话茬儿说:“钱怎么着,这得尊重妈的意见。我们现在抓得严,我那个儿子成天吵着要买辆车我死活都没有答应,一是手头紧,二是怕惹眼。像我们当领导的总得防备着被别人说三道四,后面要买车了就说是奶奶送的。”
丈母娘“咔”了一声,想咳嗽却被噎住了,张大嘴巴憋出了眼泪。李青萍慌了手脚连声喊王宝忠。王宝忠听丈母娘和儿女们谈钱的时候就悄悄地走出里间,走到店门口。他蹲下去把浸透了的磨刀石从水盆里捞起来,开始磨一把圆口片刀。刀刃在细腻的磨刀石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一群蚕在啃桑叶,刀柄映着室外斑驳的寒光。李青萍的脸像突然遭到挤压一样变了形,用哭腔说:“妈还没有走呢,你们就想着怎么分钱。宝忠,宝忠,快来看看。”王宝忠把修脚刀扔在地上,站起来一边撩起衣角擦手一边快步跑进里间。他裹着一阵风走到轮椅前,熟练地扳过丈母娘的肩膀,举起空心拳给她捶背。
丈母娘因为突然昏迷被紧急送进医院。急诊室的医生说:“短暂性脑缺血,如果再严重一点儿可能引发二次脑卒中,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新的症状,这两天陪护人员很关键,病人身边不能离人,万万不要麻痹大意。”
李青松对李青萍说:“别犹豫了,你赶紧雇个护工吧。”李青海挠着后脑勺说:“如果要排班的话,我可以退了火车票值一个夜班。最近单位考勤严得很,如果长期要排班的话,建议雇两个护工。”李青萍说:“还是先雇一个护工,总得有亲人守护在旁边的。我们先排班,走一步看一步吧。”李青松举起的手像啄木鸟,说:“嗯嗯,我看行,就按上次一二三四的顺序。”
李青松和李青海走出病房后,王宝忠对李青萍嘀咕了一句:“分钱时按照三个,值班时咋就四个了?”李青萍瞅了他一眼:“都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些?”王宝忠嘟囔道:“我也就给你说说,该做啥我一点儿不会少做。”
丈母娘的病情在第三天就稳定了,只是身体变得虚弱许多,再也无法站立。住院第五天,医生说没有啥问题了,可以办理出院回家休养。李青松紧跟在主治医生后面,反复咨询母亲的病况。主治医生被问急了,摇摇头说:“此前能恢复到这个样子是你们精心伺候得好,已经出人意料了,在后面的日子继续努力尽一份孝心吧。”
李青松又召集大伙儿到走廊开家庭会,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场告别,做儿女的终将对母亲说再见,我必须在妈最后的日子里尽做子女的孝道。妈现在不能站立,哪怕出再多的钱,也得雇一个最好的最专业的护工,妈和护工以后轮流在我和青萍那里住,出院了先到我家住一个月。”
李青海蹲下去,双手握拳捶着脑袋,说:“就我不能把妈接过去照看,我对不住妈,对不住哥哥、姐姐。”
6
王宝忠按照惯例给马科长泡了护理液。马科长说:“我右脚大拇趾内侧隐隐疼痛,你给看看咋回事。”王宝忠抬手把落地灯的灯臂压下来,让灯头贴近她的右脚。马科长的右脚明显感受到了灯管的热度。她看见自己的右脚一下子变得白花花的。王宝忠捏捏她的右脚大拇趾,说:“嵌甲,也就是指甲变形顶着肉了,我给你修一下你就不疼了。”马科长说:“有一段时间不见你丈母娘,她咋瘦了那么多?”王宝忠说:“她住到我大舅子家去了,你怎么会看到?”马科长说:“我们服务大厅人来人往的,看见有人推轮椅,我才认出坐在轮椅上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丈母娘。真的,瘦得我都不敢认了。”王宝忠说:“她去干什么?”马科长说:“你不知道哇?她携带证件和委托书把房子过户给孙子,本人要到现场拍照。我那阵儿正忙着,还说忙完了去和她打个招呼的。她拍罢照就被推走了。”马科长尖叫了一声,“哎哟。”王宝忠用棉签探进瓶里蘸了紫红色的药水按压在伤口上面。马科长龇牙咧嘴地说:“都说你王一刀的刀工好,怎么会修破脚?”王宝忠的脸像涂了层红漆,说:“不好意思,失手了,现在已经止住血了。”马科长叹口气说:“唉,你看你这个女婿当的,丈母娘把房子过户给孙子了你都不知道。喂,你老婆总该知道吧?”王宝忠说:“青萍一嘴都没有给我提过,她应该也不知道。”马科长撇了一下嘴,又一声长叹,说:“唉,亏你这么孝顺,看来手心手背终究是有区别的。你想想那套房子为啥不过户给你儿子,只因为你儿子姓王,不姓李,别说你丈母娘,搁谁谁都会这样做,换了我也会这样。”
王宝忠早早锁了店门回到家里,倒头就睡。李青萍纳闷儿了,坐在床边说:“我下午去看妈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妈出院个把月咋就瘦了那么多?她看见我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李青萍说着说着肩膀抽了起来,从床头柜上抽出餐巾纸蘸着眼角说,“妈的日子恐怕不多了,我想早点儿把她接到店里住一段时间。”王宝忠裹着被子瓮声瓮气地说:“我啥也不争啥也不图,现在把她接过来,青松会不会有想法?”李青萍越哭越伤心,拿餐巾纸擤了把鼻涕,说:“他能有啥想法?本来就约好一家照顾一个月的。”王宝忠就把马科长讲的话告诉了李青萍。李青萍像被塞了撑嘴器,愣了好大一阵儿才说话:“宝忠,我们就当啥也不知道,妈这时候受不得刺激。你明天把店里拾掇好了,我让大哥和护工把妈送过来。”
第二天,李青萍还没有来得及给李青松打电话,李青松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妈昏迷过去了,这次不像是短暂性脑缺血,已经打了120急救电话拉到医院。
李青萍急匆匆从医院赶到修脚店,连口水也不喝,嘶哑着嗓子对王宝忠说:“妈二次脑卒中,暂时在重症监护室,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估计真不行了。后面一段时间我们又要排班,你参加吗?”王宝忠望着李青萍像陌生人一样:“不一直都由你做主吗,咋突然问起我来了?”李青萍定定地看着他,说:“这次不一样,我得征求你的意见。”王宝忠咧咧嘴,说:“还是你做主吧。”李青萍摇摇头说:“那就不排你了。”王宝忠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这次不排以后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李青萍抬起胳膊用袖头蘸了两只眼角,哽咽着说:“宝忠,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做。人在做,天在看呢。”
丈母娘身上插满了管子,床头的各种仪器不断地闪烁着数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虚弱的目光陡然亮了起来,近乎贪婪地看着身边的亲人,凭借回光返照的力量颤颤巍巍地拿起笔在复印纸上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她又画了那幅图案,一条竖线蚯蚓一样爬在纸上,另外两条蚯蚓组成了一个“叉”。因为力不从心,叉与竖线的交会处往左边偏离了一厘米,这是大家早已熟悉了的一幅图案。她颤抖的手仍旧顽强地捏着圆珠笔。李青萍赶忙换了一张纸,再次把板夹举到母亲面前。大家看见她在纸上画了一个瘪瘪的圆圈,虽然瘪得像蚕豆,但是大家确信她是在画一个圆圈。略微停顿,她在圆圈中心打了一个钩,像拐棍一样的钩,然后将目光落在王宝忠身上,圆珠笔从她手里滑落下去。平时只是咧嘴哑笑不见出声的王宝忠喇叭一样哇地哭出声来,他跪在床头双手紧紧攥住丈母娘写字的右手,喊了一声:“妈……”
站在一旁的李青松蹙眉问:“喂,宝忠,只有你知道妈到底想说啥,她到底想说啥?”王宝忠一言不发,只是闭着眼睛摇头,泪水被甩得飞起来。
7
王宝忠像揣着存折一样把两张复印纸拿到隔壁的装裱店,全程盯着师傅装了画框。他回到修脚店,把墙上的锦旗取了下来,然后把两个画框挂在墙中央。他对李青萍说:“妈一直看着我们呢。”
次年清明节,李青海回来了。王宝忠把两张茶几拼起来,在小吃店点了四菜一汤,打开一瓶老白干。李青海喝了酒话多起来,他说:“我对不住妈,陪她的时间太少了。我这个当儿子的还没有你这个当女婿的做得多,我要再敬姐夫你一杯。”王宝忠只喝酒不吱声。李青萍看着一瓶酒喝空了,说:“敢情你们哥儿俩谈得来,我再开一瓶。宝忠你就放开了陪青海喝好,咱们今天歇业好好休息一天。”李青海抹抹下巴上的油水,说:“姐姐和姐夫都是好人,大哥不是人。”李青萍忙说:“莫要乱说,别人会看笑话的。”李青海说:“我就要说,难道他能做得出来我就不能说出来?”李青萍站起来把店里的灯全部打开,然后走到门口拉下了卷帘门。李青海说:“妈向来是一碗水端平的,大哥他肯定是打印了委托书,通过哄骗或者软磨硬泡,也许是强迫着让妈按了手印把房子办了过户。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良心发现主动把妈接过去照看?太阳能从西边出来吗?”李青萍说:“菜都凉了,我端到后面热一热,你们多说说话,喝好,别喝多了。”李青海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指着墙上的两幅画,说:“姐夫你最了解妈,你告诉我,妈最后说的是啥意思。”王宝忠舌头已经硬了,说:“我不喝了,我睡觉去。”李青海一把扯住他袖子,说:“姐夫你莫走,你今儿个必须告诉我,要不然我觉都睡不着。”王宝忠被李青海突然一扯,一屁股坐在地上。李青海弯腰端起两个酒杯,碰出清脆的声响,然后递给王宝忠一个,说:“姐夫,我再敬你一杯,喝了这杯你就告诉我。”
王宝忠撑着胳膊从地上坐起来,接过酒杯一仰脖喝下,然后趴在一张修脚椅上打起呼噜。李青萍跑出来,把修脚椅缓缓放平,又用力把王宝忠扶正,而后再把李青海扶到另一张修脚椅上,分别给他们盖上毛毯。
王宝忠说梦话似的说:“妈,我知道你写的‘1’,是在说老大呢……”
【作者简介】北极,本名熊万里。作品散见于《长江文艺》《芳草》《青年作家》《天津文学》《草原》《文学自由谈》等刊物。
责任编辑 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