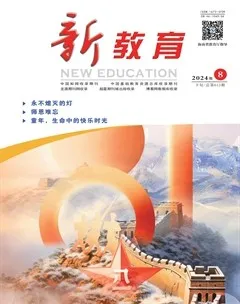童年,生命中的快乐时光
我的童年像是蓝天一样的颜色,很纯,很美好。
我小时候是在大姨家度过的。大姨家在一个小村里,每天我都会牵着大姨家里的两只山羊和村里的小伙伴结伴去放羊,这也成了村里的孩子们最快乐的游戏时光。
我们玩的最多的游戏是“顶犄角”。
“顶犄角”游戏说起来很简单:先是两只羊比,接着两只羊的小主人也要进行比试,这无疑给游戏增加了难度,也增加了趣味性。
我第一次饶有兴趣地参加游戏的时候,选择的对手是香草。香草家的羊个子要比我大姨家的羊矮半头,也瘦一圈儿。我想当然地认为我大姨家的羊一定会完胜香草家的羊,但比试过程却让我大失所望。
小伙伴们围了一个大大的圈儿,把我和香草牵着的羊围在了中间,一个个瞪大眼睛,兴致勃勃地等待游戏的开始。香草的头上扎着两个朝天辫儿,她笑眯眯地看着我,撇了撇嘴儿,又看了看我大姨家的羊,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
我当然是不服气了,在小伙伴的呐喊声中,两只羊的一对犄角顶在了一起,游戏正式开始了。两只羊的犄角在一起顶来顶去,可好玩了,你顶我一下,我顶你一下,像极了两个淘气的“男孩”在一起调皮地打打闹闹,根本就分不出输赢来。
见此情形,我有些不理解了,就求救似的看向香草,希望能够得到答案。香草微笑着告诉我,这两只羊原来都是我大姨家的,是一个羊妈妈生的亲哥俩,亲哥俩怎么会真的“打架”呢?好还好不过来呢。
原来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了。既然两只羊分不出胜负,就只好通过我和香草分出游戏的胜负了。我刚才光顾着想我大姨家的羊怎么赢香草家的羊了,根本没考虑香草是个女孩子,这会儿我才意识到我是男孩子,香草是女孩子,我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玩“顶犄角”的游戏,我就是赢了也不光彩呀!
香草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她笑着说我不一定能赢她。果然,当我和香草的两个小脑袋顶在一起时,我才发现香草的力气还是蛮大的,一点也不比我这个男孩子的力气小;而且她的头皮很硬,顶得我的头皮生疼,没过三分钟,就把我顶出了比赛画的那个大圈儿,不用说,自然是香草赢了。
香草直起腰来,看着有些狼狈的我,腰又弯下去了,笑得她那两个朝天辫儿一个劲地在我眼前晃悠,像极了羊的两只“犄角”,好俏皮好俏皮!
我输了,香草笑着说要罚我,我只好乖乖地认罚。
香草也不说罚我什么,只是笑着让我牵着那两只哥俩羊,像个“俘虏”似的跟着她走。她把我带到了她家,让我把羊都赶到了她家的羊圈里,示意我进屋,脱鞋上炕。
在北方农村,每一家都盘着一个大炕,北方的冬天“贼冷”,家家都把大炕烧得火热,进门,脱鞋,直接就上炕,盘腿坐在热气腾腾的大炕上,屁股底下那叫一个热,满身的寒气瞬间都没了,要多舒服就有多舒服。
我正迟疑,香草变戏法似的从灶上端来了几个菜,都是农村最常见的,有酸菜粉条,有辣白菜,有小鸡炖蘑菇,有红白肉。香草说请我吃饭。
在北方农村,吃饭一般都是在大炕上,我瞅着那一桌子的美味,馋得直流口水。我不解地问香草:“你不是要罚我吗?”
香草看着我说:“是啊,是罚你,罚你吃饭。”
这样的罚我当然愿意了,香草家有好吃的,赶上了,就吃,就跟在我大姨家一个样。我也不客气,学着香草的样子,也像模像样地盘腿坐在了大炕上。盘腿这个活儿看着简单,真做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刚盘腿的时候,还能忍受,时间长了,两条腿就受不了了,麻酥酥的,难受。我一会儿单腿跪着,一会儿又双腿跪着,一会儿又蹲着,后来,我干脆站了起来。这一幕惹得香草“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眼泪都笑出来了。
下雪了,很大,下了不长时间地上就积了厚厚一层。吃罢饭,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了雪地里,兴致勃勃地跑啊跳啊,像只小毛驴似的撒欢。平展展的雪地上,一脚踩下去,雪就没过了我的小腿儿,棉鞋里都是雪,凉丝丝的,但我一点儿也不在乎,还是疯玩。
雪地里,不知道是谁家留下了十几株玉米棒子的干秆儿,在东北风的吹拂下“哗啦啦”地响,声音那叫一个好听。我在玉米秆中间钻来钻去,略显滑稽,香草在一旁笑个不停,直说我傻。
就这样我还是不满足,又像只小兔子似的,在雪地里蹦蹦跳跳,尖叫着在雪地里打起了滚儿,白花花、平展展的雪地上顿时留下了我翻滚过后的印迹,张牙舞爪的,像是一个个“小怪物”。
雪越下越大,我玩得越加开心,天不知不觉黑了下来,远处传来了大姨叫我回家的声音,我这才恋恋不舍地和香草一起回去了。
这样好玩的日子有很多,它们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后来,我把这些日子带给我的思考,经过沉淀,都变成了我儿童文学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