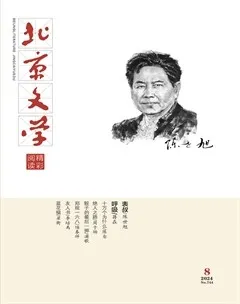秋日,提笔卞之琳(外一首)
之琳。提笔的时候,南方的红杏
还要半年才能大方地出墙。
而我已经不常住你故乡的隔壁,
许久未能拥有
如你名字般惹人误会的景色。
生活近取譬后,把我扔进满是银杏
的学生伦理,和陌生的同行们
同行于旧瓶新酒的小径。
十月了。这一年的新教师初登讲台
已经有了些时日。像你预感过的那样:
无论长短的世纪以来,写诗单调坠落成
更寂寞的事;诚实地讲,我们
自己的寂寞,偶尔展颜于历史耳际
那充分和悦的装饰。寂寞随即自己
张开翅膀成长,也时常收敛几朵
宿泪和青春痘。大概,用来爱与否定的容器,
都业已失去唇边历史的效力。
之琳。学院在秋天打着哈欠,说起诗歌
以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往事。比如:
和你在延安擦身而过的文小姐,喝着白酒
也进了剧团。而你用尽瑜伽的姿势
不过在笔端,拍了场别人梦过的电影。
你一定不会介怀:八十年后,圆脸书生我
也得逡巡舞台之外,用指针选定
围剿你文字的方寸。只略略可憎,
你总把自我陶醉的话按着不说,
辜负了后来的好人缘。只是
之琳。不被赋格的日子,我多想学你
在木屋外抽三年的烟。吐出的烟圈
要比年轮更像螺旋。类似地,
会有一个法国男人看到我
用烟蒂打磨玫瑰色,比喻也从此
还诸陈述,大意是:
“回来的他已不是他”*——常被看作
一句比肺叶更轻的话。而
戒烟以后,没有一个今天,真的成为
昨天的沉淀。
*“回来的他已不是他”:出自卞之琳1941年所写的《浪子回家集·译者序》。《浪子回家集》为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作品。
古德寺*
情人节后,人们信了观音。
这不算是奢侈的日常:
镜头集散,快门披拂。
古德寺、古德寺,其实念出来
才有了俏皮的禅意。
相信观音后,我们发烧了。
七色的砖瓦被政治遗落,胡乱倚在
赋闲的荷塘;残冬里它和橘皮厮磨。
只是立春久了,耳郭
积攒再多凉,也无法阻止谁
点燃三十八元的香。
香火缭绕,功德箱的二维码前
弓着仍用饭盒乞讨的人。点一根烟
还是点一炷香,他可否区别?
哥特涂抹、小区围墙,夕照下
也体温粼粼。算而今,
寺院的脸依法哭花了迷信,难于卸妆;
却又出落半张徽派建筑。
日出以后,它叫作天王殿,它
一呼一吸。慈悲应识:
时代错位的沙砾巨而婴,哪懂什么
因地制宜?
黑色到焰色的头发见证:几十年,
天王殿
习惯这样呼吸。
今天,他乡的人穿过长江的横批,应许
遥遥的佛祖岭*——
它英雄般一衣带水。依然差一步,就
穿入建筑历史的心脏,发烧的人
抬头见到菩萨。
菩萨面前,我们健康、目盲;或
偶发地敞开,并联几秒心脏。
*古德寺、佛祖岭:均为武汉地名
章旻辰,2000年生于江苏如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