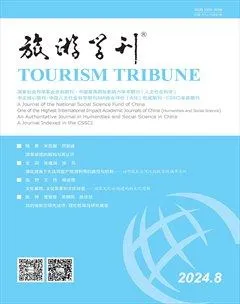“我要去巴黎旅行!”:旅游作为“意志”与伦理研究的可能
尽管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人应当怎样生活”,但一般伦理学的兴趣集中在道德行动及其与幸福的关系上,而对其他实践理性兴趣寥寥。胡塞尔指出了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分野,“与实践道德理性的某些原则有关的道德只是伦理的一个部分”2,“如果我犹豫是否应该在晚上听肤浅的滑稽剧,还是欣赏贝多芬庄严的《英雄交响曲》时,我可能会理性地决定后者,但这里不存在道德意义上的良心问题”3。胡塞尔意欲寻找实践理性的一般性原则,而非有限意义上的道德感。伦理问题在其根源处与意志相关,伦理生活是由“意志引导和塑造的生活”,道德行动只是其中之一。在深入意志领域问题时,胡塞尔多次使用去巴黎旅行的论述4,澄清交织在一起的诸多概念。无论这种选择是否带有巧合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随意性,毫无疑问的是,胡塞尔将“我要去巴黎旅行!”当作意志行为的典型实践样式。那么,我们能否从“意志”打开“旅游”,并考察旅游与伦理生活的关系?
一、“我要去巴黎旅行!”:从意志到价值
首先要确定的是旅游作为“意志”研究的内容和意义。现象学将“意志”问题看作是意识分析从理论意向性到实践意向性的过渡,意志行为的分析是实践哲学的逻辑发端。意志作为非客体化行为,是由价值引发的。问题在于,“我要去巴黎旅行!”具有何种价值?
在一般的旅游研究中,推-拉理论、娱乐、放松、教育,甚至一种体验内容上的存在主义原真性,都被冠以旅游价值一说。此类“价值”在现象学视域中,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心理物理因果性,意味着“人格自我的自身遗忘”1。胡塞尔在《伦理学和价值学说(1908—1914年讲稿)》中对意志、情感进行了考察,将非客体化行为提高到原初地位,认为意志行为自身可以作为目的论的意向性。因此,旅游中存在的价值并非只有经验的时空因果性的“动机”,还具有先验的精神因果性的“动机引发”。先验的“我要去巴黎旅行!”的价值,并非在于我去巴黎后,会看到了、体验到了、得到了什么益处或效果,而是在“我要去巴黎旅行!”这一意志的动机引发及其实践行为中具有当下自我的自身超越的生命价值。
具体而言,“我要去巴黎旅行!”的意志与“我想去巴黎旅行”的愿望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意志明确要求一种实践可能性和实践行为,而愿望则是以“可能实现”和“不可实现”两种状态存在。同时,意志也并非用于满足欲望。开启一段旅行意志既不会消除对旅行的欲望,我在旅途过程中还有可能生成对下一次旅行的欲望。在旅行的意志中,欲望持续存在于意识的底层。意志的主要特征是有创造性地(而非已经设定的)指向未来,“在此要求一种被充实的意志过程”2,而不是愿望的实现和欲望的满足。在此意义上,一种纯粹的“旅游体验”,如扶手椅上的旅行或者是“卧游”或者是虚拟旅游,绝不可能替代实践意义上的旅行。意志的“创造性”解构了传统的因果关系的行动理论。
依据传统的行动理论,我想要去旅行是因为我确信这一行为会让我获得诸多丰富体验,当我获得了这些体验时,我会感到满意,如果我没有获得,我则会感到失望。期望差异理论即是此传统行动理论的发展。但是,作为一种意志,旅行从不让人失望。因为我去巴黎旅行的行动的价值,在于意志的充实和创造性的未来,而不是预期的体验内容的充实。意志的行动理论指明,个体在行动过程中,没有一个确定的可以被实现的目标信念,而是在实践过程中的自我“更新”:非现成对象的创造和未来的作为本己的自我生成。这即是旅行作为意志现象的价值所在。
旅游作为意志行为的分析打开了旅游世界中新的指引关系。首先是旅游作为实践行为的现象学分析。意志作为实践意向性行为,它本身是缺乏独立质料的非客体化行为,因此,只有实践意向的相关项。以旅游来看,这个实践意向的相关项就是“巴黎”这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是旅游目的地作为实践意向的相关项这一性质的理论化,“旅游目的地”不是一个实体的物质,而是随着旅游实践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实践意向的相关项3。借由此种性质,更为广泛的异乡世界的旅游地化过程及其意义,也变得可以理解4。其次是意志行为内含的“对意志-实践的决定”,意志决定给予了旅游实践本身在生命意义上先验还原的含义,它以意志“将人引向一个神圣的、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和典范的起源之域中”5,旅游蕴含的伦理“悬隔”和“还原”在此可得到充分的阐释。再次是旅游活动在自我引导、自我塑造和塑造世界上所具有的创造性的生命价值,更进一步的研究将揭示被构造的自我的方向(旅游目的地-陌异的世界、决定-理想的自我)。这3个方面构成了旅游实践的现象学研究基本方向,而旅游作为意志的现象学分析,也开启了旅游实践研究的伦理学视域。
二、“实践应当!”:从价值到伦理
我所意愿的即是我所应当的,我们要追问的是,旅行何须“应当”,又“应当”如何?这一问题引导旅游研究通往伦理学。
胡塞尔在一战后对现象学伦理学的探讨,倡导我们要面向伦理学最初要求,即“指示‘我’现在‘应当’如何在这个社会的和历史的联系中存在和生活”1。这一初衷要求伦理学回到对一般性的理性实践原则的探寻。因此,尽管现象学伦理学主要关注的是道德意识,但胡塞尔的“改造伦理学”所面向的“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2是指所有领域的实践,“在普遍的以及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把每一种与伦理目标理念之定言要求相符的自我规范的生活称作伦理的生活”3。因此,对非道德行动的实践所构成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价值辩护和规范指导,同样归属于追求好的生活的技艺学(kunstlehre)的伦理学4。在此意义上,现代旅游实践代表着一种意愿和行动:我应该去旅游,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幸福的生活,是我所意愿的“好的生活”56。
“我应当去旅行!”揭示了一个无涉道德领域的实践应当和伦理生活。人理解着周遭世界,并发出旅行的意志,在旅行中确立自身的存在意义,理性地塑造着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旅游实践中被构造的自我,不以传统宗教和神圣理想为目标,而是与幸福直接相关的实践应当。旅行的伦理辩护和引导,既绕过了理智道德论者的神学化倾向,“将目光更多朝向彼岸,朝向超越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朝向作为理念之场所的上帝”,也绕开了情感道德论者在以世俗世界为家园时掉入的相对主义陷阱7。这种伦理理想不再和宗教的拯救恢复合为一体8。
三、“旅行”:作为一种伦理生活
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先于其存在并作为所有实践的基础——较之工业革命之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去旅行的意志为特征的休闲生活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休闲与伦理生活的关系是有历史和文化起源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9,而儒家的“曾点之乐”也是以一种休闲生活状态呈现“尧舜气象”。而把旅游及休闲纳入伦理生活中考察,是当代伦理研究发展的需要。因为在当代生活中,人格的一个本质特点便是对自我生活的实践决断,便是“我要去巴黎旅行!”。
旅游从反日常到日常实践的发展中,逐渐凸显出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意志特征。它不再以自然态度从盲目生活中寻找旅行的目的,而朝向了基于日常生活悬隔和还原的伦理生活。在此意义上,旅游实践分有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沉思生活的基本特征。这种“意愿的伦理生活”,既是当代人自主选择的塑造我的生命整体的方式,指向的是伦理的真,又是从当代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中产生的“哑的”实践理性的生活方式。胡塞尔对伦理学的“改造”,要求理性指引伦理生活,旨在回归一种哲学根本兴趣,即对生活的兴趣以及“人成功地驾驭他的整个生活、他的全部此在”10的兴趣。这种转变、回归或者改造,要求重新思考当代休闲与伦理生活的关系,通过阐释这类休闲实践的先天价值和描述其“应当”的生命样式,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提供指引。旅游研究可以在这种关系中开辟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致谢:感谢倪梁康老师允许我阅读其尚未出版的《伦理学和价值学说(1908—1914年讲稿)》译稿。
(作者系该院助理研究员;收稿日期:2024-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