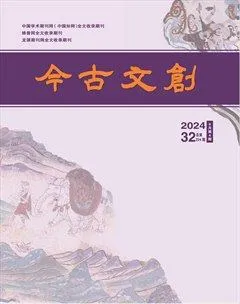经典文本影视改编 “ 忠诚度 ” 探讨 : 以《简 · 爱》为例
【摘要】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如何“忠实”于原著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性话题,至今也并无一个准确的说法,但影视改编应该忠实于文本的“精神”被普遍认同。由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简·爱》自出版以来多次被不同的导演改编,但对于同一部经典作品的不同改编影视版本各有其特点,在不同程度上呼应、延续经典文本中的相关内容。本文选择了两个翻拍版本即1996年佛朗哥·泽菲雷里导演的改编版本和2011年凯瑞·福永导演的改编版本做出具体分析,分别就其中的情节与主题、人物形象、氛围这三个部分与原著进行比较,同时比较两部影视作品,阐明影视改编版本的侧重点与独特之处,探讨以《简·爱》为代表的影视改编作品对于文本“精神”忠实性的问题。
【关键词】影视改编;《简·爱》;情节与主题;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2-008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2.024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达,传统文学作品的形态与载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文学经典正逐渐摆脱纸质载体的单一束缚,以及传统上仅由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解读与传播模式,走向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当中,成为真正的消费产品,如连环画、影视、舞台剧等不同类型。
《简·爱》这部作品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广泛好评,直到现在也依旧是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宝库中的精品。一部经典的作品随着时间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各种形式传播到更广泛的接受群体当中,《简·爱》从诞生之日起便由纸质书本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话剧等各种不同的形式,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走进了千家万户。电影艺术的应用使这部经典作品实现了真正的通俗化。而对于一部由经典文本作品进行改编的电影,被接受的程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导演和编剧对于原文本的理解及在影片中所反映的对于文本的“忠诚度”,即这部改编的影片在何种程度上、哪些方面忠实地对于文本进行了再现。
文学作品以文字的排列组合为表现手段,通过塑造文学形象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内心,而不是靠读者的视觉效果,相对于电影的直观性与外在视觉性,文学作品更侧重于内在性与思考性。而所谓“影视改编”,是运用影视的思维在遵循影视规律的基础之上对于文学经典作品的一种“再创造”的活动。正因为如此,一部影视作品是不可能也是没必要百分之百对于文学作品进行还原,在两个小时之内表现一部数十万甚至百万的文学作品势必要对文本进行改造,从而在有限的时间里体现出文本的主要表达思想,塑造有特点的主人公,体现出充分的“创造”特征。
《简·爱》的各个电影改编版本各有不同的特点与侧重点,每位导演都想将一部经典的精髓表现在自己的影片中,他们对于文本有着不同的阅读感受,也对文本主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在自己的影片中表达不一样的主题,如歌颂冲破封建门第观念的爱情,或者是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表现与思考等等。而就多部改编影片的“评价”而言,由凯瑞·福永导演拍摄的2011版《简·爱》在观众群体和评论家中口碑最好,被评为了“有史以来最炽热优雅的改编版,最棒的简爱形象”,很多人将其看为翻拍最“忠实”的《简·爱》。而相对于2011版改编版本的备受推崇,1996年由佛朗哥·泽菲雷里拍摄的改编版本,则成为整个《简·爱》的改编史上公认的失败记录,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影片因“令人尴尬的选角错误”而失败,绝大多数当时的影片委婉表达了观点“一流的演技,末流的选角”[1]。而1996版的失败似乎归根到底就可以理解为这一部改编的影片并不“忠实”于原作,从这些评价中就可以看出,起码在角色的塑造上,1996版的角色塑造与原著相差甚远,这就与2011版的备受推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充分比较两部改编影片的不同,讨论两部影片对于文本的“忠实之处”。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写作《简·爱》之前,她对于自己要描绘的主人公已经有了明确的打算,她曾对妹妹艾米丽·勃朗特说过主人公的样子“我要写的是一个新型的女主人公,她同我一样矮小和丑陋,但是我相信她能同你们塑造的任何一个漂亮的女郎媲美,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兴趣”[2]。
作者想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的反抗,即文字的力量来对抗这种不合理的落后制度,因此她想塑造的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新女性形象来传达自己的理想。无论观众是否读过文本,观摩影片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影片中出现的角色,所以对于影片中主要人物的选角是验证改编作品是否忠实于文本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从文本来说,主角简爱的性格特点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自尊、追求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大胆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进行反抗;同时追求真挚、自由的爱情,反抗虚伪的宗教权威。就影片的改编来说,凯瑞·福永导演的改编版本让人物很符合原著中的性格特征,尤其突出的是主人公的反抗意识,整部影片组织起来的几个情节围绕的就是主人公的反抗过程,反抗权威与宗教。
在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关系中,米娅·华希科沃斯卡所扮演的简爱在这段关系中显得更加主动,而不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在误解罗切斯特时,简爱将自己的内心所思所想向罗切斯特先生全盘托出:“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真心了吗?我的心灵和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和你一样充实……我现在不是以血肉之躯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对话。”在简爱的心中,人与人之间本就是平等的,男人与女人之间,富裕的人与贫穷的人之间都应该是这样。彼时的英国,家庭教师这个职业备受歧视,薪水很低,也不能让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立,而简爱将这看作是不合理的约束,面对“尊贵”的罗切斯特先生,她永远不卑不亢,她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家庭教师与大家族的继承人是平等的,人的地位并不以财产来衡量,她以一己之力对这种畸形的社会制度进行反抗。
而在1996年的版本中,导演选择了里德姨妈家和在学校中的情节,体现了主角简爱的反抗精神。但是对于男女主角的爱情关系,相对于2011版,1996版的女主角在这段关系中显得更加被动,而不如2011版主动争取自己的爱情和幸福,面对自己心爱的罗切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的“爱情”关系,1996版的简爱更加无力,躺在床上“吃醋”,在舞会上坐在角落里,舞会后悄悄离场。对罗切斯特先生的询问,她回答:“请原谅先生,我,我真的很累了。”迅速背对罗切斯特先生上楼,想躲避罗切斯特先生的眼神。米娅·华希科沃斯卡在演到舞会的情节时,对于英格拉姆小姐和夫人们的谈话,她显得不卑不亢,冷眼面对这些人,似乎在嘲弄她们的庸俗。她所扮演的简爱重视的是精神上的平等,对这些物质条件优越而精神世界极度匮乏的小姐太太们一定心里充满了鄙夷。面对罗切斯特的询问,她不再躲闪,只是回答“I am tired,sir”,眼神也和回答一样不卑不亢,她主动争取自己的幸福,要求平等,主动申请辞职以保存自己的尊严。1996版中虽然也有对于罗切斯特先生那段经典的表白,但是显得更加被动,是在罗切斯特的追问下的被动结果,主角简爱也显得更加“多愁善感”与脆弱。
同样是对于简爱回去探望里德姨妈这个情节,两个版本都有“宽恕”这一情节。1996版夏洛特·甘斯布扮演的简爱显得更加温柔与真诚,面对将死的姨妈,简爱发自内心地谅解,体现出女主人公作为一位“新人”女性在反抗的性格之外还多了一份女性的柔情。在2011版中,面对姨妈狠毒的欺骗,米娅·华希科沃斯卡扮演的简爱则不如1996版的温柔和真诚,而是面对行将就木的亲人给予礼节性的安慰,结尾一句“be at peace”则更如一句套话。因此可以看出,两个版本对于简爱这一角色的塑造上,2011版侧重于简爱叛逆反抗性格的刻画,主角由此显得些许“冷酷”,而1996版的简爱则更加温柔、脆弱、多愁善感。正因如此,两者可以说都不是完全“忠实”于原作中的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各有其独特之处。
如果说简爱是一个“新人”形象,罗切斯特也可以说是一名封建贵族阶级叛逆的“新人”典型。书中对他的性格刻画主要有这几个特点:在书中,他的性格被深刻而细腻地描绘为多重矛盾的交织体,他似乎生活在一个永远缺失温暖家庭与真挚爱情的阴影之下,情感上如同荒漠般贫瘠;与此同时,他又展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在众人面前盛气凌人,对一切都嗤之以鼻。这是罗切斯特身上的“矛盾”,也正是腐朽落后社会制度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
对于两部改编影片来说,在人物的气质上2011版由迈克尔法斯宾德所扮演的罗切斯特更像原著中的角色,他带有英国绅士的气质,更加神秘与冷峻。面对帮过自己的简爱,罗切斯特不道谢,而是说道:“All governesses have a tale of woe,what is yours(家庭教师都有悲惨的故事,你也讲讲吧)”,当老管家想让僵持的气氛活跃起来,罗切斯特却粗暴地拒绝,由此一个粗暴的、蛮横不讲理的贵族子弟让观众对于这个人物有了初步的印象。随着剧情的推移这个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完善与丰满,教堂婚礼情节的剧情“突转”,让观众意识到这个角色让人同情的一面,也就改变了对于这个角色的看法。2011版对于“突转”后罗切斯特对简爱的挽留同样让观众动容,面对简爱的离去,罗切斯特哭了,他内心对于简爱的所有情感一下子爆发“我以我的名誉,我的衷心向你发誓,我爱你,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一个神秘的、粗暴无礼的英国绅士在地下苦苦哀求着自己真正爱的人不要离开,马上将这个看似冷酷的人心里最脆弱的一面暴露给观众,让观众造成强烈的心灵震撼,对于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的悲剧感到痛心。
而1996版由威廉·赫特所扮演的罗切斯特,被普遍认为是“一流的演技,末流的选角”[1],评论都认为,这个版本的罗切斯特“以温和的古怪取代了拜伦式的阴郁”,威廉·赫特所扮演的罗切斯特太过于“文艺”与“深沉”,而缺少原著中罗切斯特的神秘和狂野。如面对简爱的离去,罗切斯特的台词只是“我爱你,说你也爱我”而没有感情的爆发,让观众感觉到人物对于这种重大事件的冷漠,缺乏2011版罗切斯特炽热的感情,从而一定意义上对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削弱,同时为了使影片更加紧凑,将“疯女人”放火烧庄园和简爱的离去两个情节在同一时间进行展示,是对原著情节的一种改编,罗切斯特面对代表了自由真诚爱情的简爱和代表了封建禁锢的“疯女人”和庄园,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属于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也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这一“叛逆”的新人形象。在1996版中加入了罗切斯特冲入火海救原配妻子伯莎的情节,这个细节体现了1996版罗切斯特的温柔与善良,也很符合1996版的人物气质,在这一版本中罗切斯特不如2011版的冷酷与神秘,缺乏绅士风度,但却显得温柔与真诚,而温柔与真诚虽然让观众记住了这个复杂的人物,却并不符合原著对于罗切斯特的描绘和原著的精神,所以就选角与角色的塑造,1996版的改编作品并没有紧密地契合于原著。
二、情节与主题的不同呈现
主题可以理解为文本的主旨与中心表达思想。具体来说,主题是一种用人物和情节综合归纳出的一种思想或者观念,即作品的中心思想和全文主旨,可以用一种名词性短语来进行归纳。[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简·爱》这部作品的前三个具体主题可以分别总结为“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爱情”“新型女性的成长”,而对于宗教主题和殖民主义的主题来说似乎不好用一个名词性短语进行概括,从而体现出后两种主题的复杂性。就影片的改编来说,一部电影一定要由一个或多个主旨内容贯穿始终即通过电影表达某种或某些主题。
就2011年凯瑞·福永导演的版本而言,主要突出的就是原著的女性主题,影片通篇表现主人公简爱的反抗与平等意识,而将爱情主题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影片最开始的情节就是简爱幼年时对于里德家的反抗,无论是对表哥身体上的反抗或是对于姨妈精神上的反抗,从而奠定了主角的整体特征,即一个从小到大彻头彻尾的“叛逆者”。在学校面对无理的虐待,她要夺下打人的木棒,当着老师的面掰断它。最明显的是在桑菲尔德庄园,简爱望着晚霞的独白“我希望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勇于活着,这想法激得我痛苦不堪……”整部影片都是围绕着简爱的反抗进行,由童年对于权威的反抗,在学校对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反抗,在桑菲尔德庄园对于腐朽的封建门第制度的反抗,对于罗切斯特先生爱情的反抗,到最后对于代表着宗教权威的圣约翰的反抗(电影中删减了原文中的简爱对于上帝直接反叛的语言,如她不相信上帝可以给她带来幸福,又如圣约翰责备她不爱上帝时,她很干脆地回答只相信能为人间真正带来幸福的上帝,而电影中删去了这些情节与对话,可以说削弱了一些简爱的反抗精神,由原文中的对于上帝和宗教的反抗变成了对于圣约翰爱情的反抗,也是一种对于男性权威的叛逆,但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批判性),可以说电影的每一个情节的设置都是为了印证这个中心主题,塑造一个有反抗精神的新型独立女性形象。
这就不得不提到文本情节与电影改编情节的关系。例如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第二部《学习时代》中,热爱戏剧的主角威廉,认为戏剧应该原原本本地表现原著,他将艺术的原作与改编比为树干、树叶、花朵和果实的关系,歌德借助于塞罗的话来这样对威廉进行反驳“总不能把整棵树搬上餐桌,艺术家必须把金苹果盛在盘里端给客人”[4]。虽然歌德所提到的是原著与戏剧的关系,但在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中,关系也是如此。这说明对于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主要的或者是次要的角色都在几个小时的影片中表现,是不可能的,更是不必要的。
在原著中,记录的是主人公简爱的成长史,由童年到婚后生活这几十年的过程。其中的情节设置又重点突出,主要在学校、桑菲尔德庄园、圣约翰住宅的生活这几个情节多加笔墨,剩下的情节像具体细节或是主人公的婚后生活则像蜻蜓点水一般几笔略过。这种写作方式将主人公简爱几十年的生活浓缩在了一本不到六十万字的小说里,这就是“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的差别。电影则需要在两个小时之内表现几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在几小时内将一本著作完全复刻是不可能的,由此需要编剧更加精细地筛选与概括情节,进而表现出原文本的精髓与中心主旨。
凯瑞·福永导演的改编版本打乱传统自传性作品的叙述顺序,以简爱在雨夜的荒原上到了圣约翰的住宅为开场,有点像戏剧作品一般,在开头就将冲突与悬念最大化。同时,导演在影片中又不断运用插叙的手法,使场景和情节不断变化;由圣约翰的住宅回忆到童年在里德庄园和学校。再到桑菲尔德庄园,再接上电影开头的情节回到圣约翰的住宅,虽然叙述方法不断转变,但整部电影的每个情节都有内在的脉络,就是按照主人公简爱的反抗与叛逆来组织。导演和编剧选择与概括的情节都是为了映衬“叛逆”主题。这样的叙述、拍摄手法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主人公以一己之力打破了英国一直以来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也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四次对抗男权社会,最后收获了真正的爱情与自由的女性。但由此电影中的另一条线索即男女主人公爱情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是为了反映女性主题而服务的,相较于原著相比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则显得些许苍白。
而另一部影片,即1996年佛朗哥·泽菲雷里导演的版本情节则不像2011年版本一样采用各种倒序、插叙的手法,而是如同小说一样按照时间先后的发展,选择情节组合成了一部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在此版本中,与2011版所表达的女性主题似乎有些不同,这一版本主要强调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最开始的情节是童年的简爱在红房子受到虐待的场景,也如新版一样,一下让主角处于十分激烈的冲突之中,但两者的情节选择有很大的差别,最大的就是关于圣约翰的一条故事线,在1996版中将这条线完全删除干净,这也可以说明电影的主题似乎并不只是在突出女性要求平等、对于现实男权社会反抗的主题,影片开头部分对于里德姨妈的抗争,以及在学校里对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反抗也能证明“抗争”的主题,但随着主角的成长,时间地点的变化和推进,到了桑菲尔德庄园之后的情节发展印证的却是“爱情”主题,主角没有像2011版中的主角有发自内心的独白,面对罗切斯特先生,简爱的语言似乎是在塑造一个面对权贵面对权威“不卑不亢”的精神,一种平等的精神,而不是和不合理的社会、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1996版削弱了原著所传达的社会批判意识。
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上,1996版加入了一个在简爱离开后,罗切斯特先生在起火的庄园里救“疯女人”的场景。这一场景无论在原著里还是2011年的版本中都是不存在的,原著里是在酒馆中的客人向简爱复述的,而在2011版的电影中则是由老管家向主角说明,只有很小的一段话来概括一个情节,而在1996版中却将原著中这一句话用了几分钟拍摄了一个情节,让本来抽象的一句话变成了更加具体的影视片段,目的是为了更好塑造罗切斯特这个角色的形象,面对火势他奋不顾身冲了进去,如果疯女人死了罗切斯特可以顺理成章寻找自己的真爱并与之结合,因为在那个年代丈夫是无权与妻子离异(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了封建的制度),“疯女人”罗莎代表了封建的婚姻制度,罗莎的死象征着腐朽制度的破灭,罗切斯特才可以获得“新生”,但即使这样罗切斯特还是要救罗莎,面对自己幸福的阻碍罗切斯特说“来我身边,别害怕……我绝不会伤害你”,这些台词是原文中没有的,导演加入了这个情节和这些台词,就是为了突出罗切斯特的善良与柔情。
总之,在主题的选择上,相较于原文,两个版本的影视改编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而主题的不同选择势必要选择不同的情节,塑造不尽相同的人物形象来呼应这个主题。
三、结语
电影与文学不可分割的关系源自它们共同对完美艺术的追求,但是在文学改编电影的过程中不免会因为其不同叙事手法和传播载体产生巨大差异。[5]无论使用何种改编的方式,无论拥有多么先进的技术对于经典文本进行改编或对经典影视进行翻拍,没有一部《简·爱》的影视改编版本可以完全地客观地对于原著进行还原,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展现原著的每个细节,产生出让每一个书迷都满意的、最完美的版本,仅凭借有限时间内的画面与声音的结合体永远无法精确地表现出由文字所构建的世界。
艺术创造是一种主观性的创造活动,因此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固定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对于经典文本的艺术改编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与独特之处,经典文本的影视改编成为一种潮流,面对现代观众不断提升的审美水平和审美需求。如果一味强调由文本改编的影视作品完全“忠实”于文本,事无巨细地表现文本情节,就会使影视作品缺少新时代的突破与创新,让一部可以在新时代焕发不一样光彩的经典作品陷入平淡无奇的境地,也会使得观众失去新鲜感和对于改编影片的期待感,不利于文学经典在新时代的传播与影视改编的健康发展。
只有掌握艺术的规律,加深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坚持对于经典文本的影视改编“忠实”于经典文本,而又不“陷入”文本之中,使电影在不拘于原著文本的同时,呈现出原著文本之外的新光彩。影视改编可以对于人物形象和具体的情节进行增删和修改,并加上编导、二次创作者对于原著的理解和审美观点,但绝不能失去原作的精神和灵魂,这样才可以让经典的文学作品走向现代,走向更多观众的视野中被更多的观众所接受,让经典文本在新的时代焕发出独特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戴锦华,滕威.简·爱的光影转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郑克鲁、蒋承勇主编,黄宝生、陈建华副主编.外国文学史(第3版)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第2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马子新.从小说到电影:简爱形象塑造考察[J].甘肃高师学报,2016,(11).
[5]姚兆寿,冯树贤主编.文华影韵:影视文学改编现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作者简介:
何莹,女,浙江台州人,温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