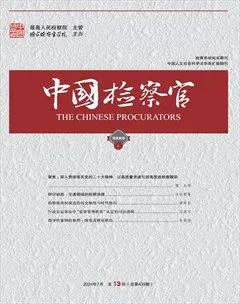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实践困境与完善
摘 要:《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但实践中办案流程存在争议,情节认定存有质疑,低龄未成年人处遇难等方面的问题和困惑影响了制度运行效果。需要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理清相关法律争议,完善配套措施,明确办案流程和工作标准,加强专门学校建设,提升专门矫治教育实效,从而完善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工作。
关键词: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 情节恶劣 教育矫治 专门学校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备受关注,但法律施行3年多来,相关配套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关于《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理解和适用有颇多争议。本文聚焦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一、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立法背景
1962年修订的《刑法》(草案第27稿)将14周岁设置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一直延续至1997年刑法。[1]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日趋早熟,同时严重暴力犯罪向低龄化方向发展。检索2016年至2020年新闻报道,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就有10余起,引发较大舆情的包括“湖南12岁男孩弑母案”“大连13岁男孩杀害女童案”等,凶手因未满14周岁,均未受到刑事处罚。对此,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应当调整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以遏制日益增多的低龄暴力犯罪现象。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即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刑法已经有条件地降低了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不到位,影响了法律规定的统一正确实施。
二、司法实践中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面临的障碍
笔者结合所办的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报请核准追诉案件,对实践中的困惑开展调研,发现当前办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案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办案流程存在争议
1.立案、侦查程序认识不一。低龄未成年人在实施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造成严重后果后,能否进行刑事立案并开展侦查活动是司法机关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有学者认为,由于最高检尚未核准追诉,故对低龄未成年人所犯罪不能按照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可按照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调查程序收集证据。[2]还有学者认为,只有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开展侦查查清犯罪事实,才有后续进入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可能,刑事立案并不影响或决定是否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3]因此,公安机关可以按照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相关规定对实施严重暴力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立案并开展侦查工作。
2.适用强制措施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在最高检未作出核准追诉决定之前,根据法律保留原则,不宜对低龄未成年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也有学者指出,对低龄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可以参照最高检《关于办理核准追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核准追诉规定》)第4条规定,即在最高检核准前,侦查机关可以对低龄未成年人适用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5]
3.提出报请的检察机关级别认识不一。有观点认为,由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量少,社会关注度高,为更好统一追诉尺度,由设区市级检察院作为报请机关为宜。[6]另有观点认为,基层检察院作为报请机关更为适宜,一是从工作质效考虑,基层检察院与基层公安机关沟通便利,检察官能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提前介入了解案情,同步开展引导侦查工作;二是从工作流程上看,基层检察院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重大恶性案件会及时向上汇报,上级检察院也能给予指导和帮助,因此由基层检察院作为报请机关不会影响案件质效。[7]
(二)情节认定存有质疑
1.对“情节恶劣”的质疑。《刑法》第17条第3款对“情节恶劣”这一关键要素的规定较为笼统。有学者认为,只要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造成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后果就应认定为“情节恶劣”。[8]也有学者认为,认定“情节恶劣”需要综合考虑“主观恶性”“平时表现”“社会影响”及“犯罪结果”等多方面,是罪行和犯罪结果之外的条件。[9]
2.对“社会影响”的质疑。参照《核准追诉规定》第5条关于报请核准追诉案件条件的规定,社会影响系核准追诉的条件之一。实践中,低龄未成年人在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时,是否会产生社会影响并不是其实施犯罪的主要考量因素,且社会影响很大程度上与媒体报道、社会舆情相关。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等考虑,通常情况下,办案机关会最大限度降低案件的社会知晓面。因此,如何评价社会影响及如何将产生社会影响的结果归责于低龄未成年人需要进一步研究。
3.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质疑。依据法律规定,公检法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等情况开展调查,调查后形成全面反映其犯罪主观恶性、平时一贯行为表现和犯罪后是否具有帮教矫治条件的报告,即社会调查报告。尤其对于认定是否属于“情节恶劣”,主要基于社会调查,对其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和矫治教育可能性开展评估。目前由于现行规定对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流程、具体内容、报告事项等不明确,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粗略不全面、结论依据不够客观、建议的专业性不足。
(三)低龄未成年人处遇难
1.低龄未成年人面临“无校可去”的现实困境。对实施了严重暴力伤害行为但未被核准追诉的低龄未成年人,可依法送至专门学校接受教育矫治。但实践中,专门学校总体数量偏少。根据2023年底教育部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专门学校119所,其中还只有部分学校满足“专门场所+闭环管理”条件,有资质招收涉罪未成年人。[10]有的省份尚未设立专门学校,专门学校分布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低龄未成年人往往面临“无校可去”的困境。
2. 低龄未成年人适用的教育矫治模式不明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 条规定了专门教育,第45条规定了专门矫治教育。由于适用对象不同,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在程序构造、决定机制、矫治手段等方面应当有较大差别。因此,对处于报请核准追诉阶段的低龄未成年人到底适用何种教育模式不明确,给实践带来困扰。
3. 专门矫治教育缺乏可操作性。专门矫治教育前身系收容教养制度,填补了介于刑罚与非刑罚司法处遇之间的矫治区域空白。尽管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进行了构建,但对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启动程序、评估标准、决定标准均未说明,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程序设计还存在大量空白,制度可操作性不足。
三、完善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明确办案流程
1.明确立案、侦查程序。在最高检核准追诉前,侦查机关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对低龄未成年人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第一,符合司法办案规律。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发现严重暴力伤害案件,先行刑事立案启动侦查程序,后查清并确认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和犯罪事实,符合司法办案的一般程序和逻辑。第二,能更好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刑事诉讼法》对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有明确的程序要求,如讯问时安排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开展情况调查等,从法律层面使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第三,《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并未明确表述行政机关制作的行为人供述及辩解可以作为直接使用的证据材料,且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制作的讯问笔录只有转化为刑事笔录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侦查阶段如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制作笔录还需要进行证据转换,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第四,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伤害行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会使得被害方、社会大众情感再次受到伤害。
2.明确强制措施的适用。在最高检决定是否核准追诉前,可以适用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但一般不宜适用逮捕措施。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不仅有利于案件的顺利侦破,也能为送入专门学校预留时间。但逮捕措施除外,其适用对象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而对于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犯罪嫌疑人,只有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故在确定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之前,不宜适用逮捕措施。
3.明确由基层检察院作为报请核准追诉的主体。实践中,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系由基层公安机关进行,一般而言与之同级别、同地域的基层检察院更为熟悉和了解发案原因、案件事实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情况,由基层检察院先行审查案件并提出是否核准追诉的意见,更有利于最高检审查决定是否核准追诉。同时,如果发现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或案件证据薄弱需要补充侦查时,基层检察院可以及时开展侦查监督、引导侦查。在办案中发现存在其他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时,基层检察院能够更为便利地开展综合履职工作。
(二)明确工作标准,提升案件专业化程度
1.细化裁量标准,明确何为“情节恶劣”。“情节恶劣”是核准追诉与否最重要的考量因素,需要结合未成年人一贯行为表现和个案具体情况及犯罪后行为表现,综合判断其实施犯罪的情节恶劣程度,从而保证对低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成为“别无他法的唯一选择”。[11]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明确低龄未成年人报请核准案件中“情节恶劣”如何判断,细化审查裁量标准。
2.引入听证程序,精准评估社会影响。低龄未成年人报请核准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需要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意见,同时也符合《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关于听证的条件,为准确评估低龄未成年人所实施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可以由承办案件的基层检察院启动听证程序,以不公开方式进行,根据需要召集相关领域教育专家、法律从业者、心理专家、矫治教育专家等参加,为核准追诉提供客观公正的参考意见,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明确评估标准,提升社会调查报告专业度。为充分发挥社会调查报告的价值,应进一步明确社会调查在广度与深度方面的专业标准,用更为科学的标准和更为专业的方法来评估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再犯可能性。如关于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需要调查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生活习惯、在校表现、平时是否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关于家庭监管情况需要调查是否系隔代抚育或单亲家庭、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监护人的教养方式等。关于社会关系情况需要调查平时交友情况,是否与不良少年交往等。关于案发后表现需要调查低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对此次犯罪行为的认识、家庭是否有赔偿意愿与能力、有无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关于家庭及社区态度需要调查监护人对孩子及监护教养方面的认知程度、有无意愿和能力提供切实有效的监管举措、社区对未成年人回归的态度、能否接纳未成年人并提供帮教等。[12]可以灵活采用面对面访谈、实地走访、量表评估等调查方式,形成全面、客观的社会调查报告。
(三)加强专门矫治教育工作,破解低龄未成年人“无校可去”困境
1.加快专门学校建设。建议司法机关与教育部门牵头,建立司法机关与教育部门、专门学校衔接机制。每个省按照本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至少设置3所专门学校,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合理划分班级和校区。学校要配置教育矫治所需的学习、生活设施,从行为矫治、心理行为观察、日常行为监督等各环节进行管控,定期分析评估,严格规范管理。
2.明确处于报请核准阶段未成年人应当接受专门矫治教育。专门矫治教育前身系收容教养制度,填补了介于刑罚与非刑罚司法处遇之间的矫治区域空白。对处于报请核准阶段的未成年人,虽不确定其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但仍应参照《刑法》第17条第5款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的规定,实施专门矫治教育,这也体现了“教育和保护”相结合的办案理念。
3.完善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分级处遇评估功能,构建适合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的实施机制,明确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事项的具体范围和标准,尤其是未成年人进出专门学校的评估标准和方式。健全专门学校的管理模式、行业准入、考核、退出及惩戒机制,提升专门教育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对于最高检不核准追诉的低龄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工作,不能仅依靠专门学校,还需公安、检察、教育、民政、妇联等各相关职能单位的协同共治,多维度补强专门教育矫治力量,最大化提升教育矫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