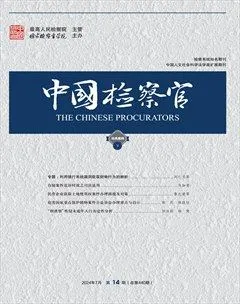存疑案件追诉时效之司法适用
摘 要:追诉时效已超越犯罪范畴而进入刑罚视野,其适用应以犯罪为前提。犯罪是实体法上的概念,即符合犯罪成立条件,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撑。存疑案件不符合这一前提,因而不能适用追诉时效。案件事实存疑时,追诉期限有多种可能性,存疑案件仅系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性,势必建立在假设之上而带来滥权风险。超过追诉期限对终止刑事诉讼程序不具有绝对意义,存疑案件适用追诉时效亦非更有利于行为人。
关键词:追诉时效 存疑案件 终止审理
追诉时效是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期限。对于存疑案件是否可以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此,有待从追诉时效的基本法理出发,合理界定追诉时效的适用条件,并结合不同处理方式的适用后果进行权衡,以求更准确地适用法律。
一、存疑案件追诉时效司法适用中的争议
[基本案情]自诉人徐某甲诉称:其与被告人徐某乙合伙开设公司,后因与徐某乙发生矛盾退出公司。徐某甲离开公司时提出补偿要求,徐某乙在《境内汇款申请书》上加盖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徐某乙的名章后,向徐某甲转款38万美元和14万欧元。2012年年初,徐某乙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境内汇款申请书》上的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并非其加盖,意图陷害徐某甲,使徐某甲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立案,并于2012年6月19日被羁押,至2013年12月20日因公诉机关撤回起诉方被释放。故徐某甲以徐某乙犯诬告陷害罪于2019年11月15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海淀区法院立案后经审查认为,徐某甲对于徐某乙犯诬告陷害罪的指控缺乏罪证。徐某甲无补充证据,且坚持不撤回起诉,海淀区法院裁定驳回自诉人徐某甲对被告人徐某乙的起诉。宣判后,徐某甲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一审遗漏了对于追诉时效的审查,经二审审理发现案件存在超过法定追诉时效的情形,因此裁定对本案终止审理。[1]
本案是自诉案件,一审法院依法受理后予以立案,经审查以缺乏罪证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以超过追诉期限裁定终止审理。对于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已立案,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开庭审理后,则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于超过追诉期限的自诉案件,如果已经立案,则应裁定终止审理。但对于同时存在缺乏罪证和超过追诉期限两种情形,案件应如何处理存在争议。公诉案件中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行为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审查起诉或提起公诉,同时存在证据不足与超过追诉期限两种情形,如果按照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应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应作出无罪判决;而按照超过追诉期限,检察机关则应当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则应当在受理审查时退回检察机关,或经审理后裁定终止审理。
本案二审裁判认为,刑事诉讼中对于追诉时效的审查和适用优先x89IOoOdTLoXOFqOHyz7hg==于对案件的实体审判。一审法院经审查后已决定立案,虽然未经实体审判即以缺乏罪证为由裁定驳回自诉人的起诉,仅是一种程序处理,但立案已经标志在程序意义上启动了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符合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前提条件。在案件进入二审程序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应以超过追诉期限为依据,裁定对本案终止审理。二审法院优先选择适用追诉时效,观其论证路径,系诉诸于《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项。然而,该路径忽略了一个前置性问题,即立案虽然标志着追诉开始,却并非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项的充分条件,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项还需犯罪成立。笔者认为,存疑案件不得适用追诉时效,也就是不得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项,而应根据案件事实存疑作出相应处理决定。
二、从追诉时效适用条件分析存疑案件可否适用追诉时效
追诉时效有其适用条件,其中首要的是探讨追诉时效的部门法属性及其在我国法律上的定位,进而确定追诉时效适用的位阶;其次是根据追诉时效适用之位阶,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2条,准确界定《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项中“犯罪”的概念。
(一)追诉时效在我国法律上的定位
论及追诉时效本质,有实体法、程序法以及混合时效理论之分。实体法理论视追诉时效为刑罚解除事由,程序法理论视追诉时效为程序障碍事由。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规范,追诉时效没有被规定在《刑法》第一编第二章“犯罪”名下,而是规定在第四章“刑罚的具体适用”部分,足见其虽为刑法总则内容,但并不是作为犯罪成立条件存在的。依此,追诉时效应定位于实体法,作为刑罚解除事由而存在。追诉时效的依据在于实体法,但其效果却被局限于程序法。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8年10月10日发布《对如何理解和适用1997年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关问题的意见》和最高法《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1997年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关问题征求意见的复函》明确了对追诉期限跨越到1997年刑法施行之后的犯罪行为适用’从新’原则”[2];按“实体从旧、程序从新”这一普遍承认的法律适用规则,追诉时效属性上已趋向于程序法,而不是仍将其作为实体法受从旧兼从轻原则之制约。这也符合比较法的立场,例如德国虽然也是在刑法典中规定追诉时效,但司法实践及刑法通说均无争议地视追诉时效为程序障碍事由。[3]不管定位如何,追诉时效已然超越犯罪范畴是不争的事实。若将追诉时效定位为刑罚解除事由,就必须确证犯罪,始得适用追诉时效而解除刑罚;若将其定位于程序法,更须确证犯罪,此时追诉时效已不是直接作用于刑罚的解除,而是阻碍刑事诉讼程序的发起与推进,超过追诉期限才会因程序性前提不满足而最终导致刑罚解除。
(二)《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项中“犯罪”为实体法上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如果在此意义上把握“犯罪”概念,那么只有法院定罪后,始得适用追诉时效;在此之前,均系犯罪嫌疑。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条,对于超过追诉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如此,只要超过追诉期限,理论上就永不可能达到法院定罪的地步。如果依照该路径,将使追诉时效永不可能得以适用。因此,对于《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项中“犯罪”概念之界定,不能立足于《刑事诉讼法》第12条,而应认为来源于《刑法》第78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中“犯罪”概念,进而诉诸于《刑法》第一编第二章,此时“犯罪”应界定为一个这样的概念,不仅符合犯罪成立条件,且每个成立条件均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撑,可称之为实体法上的犯罪概念。只有符合这一概念,法院始能定罪;裁判作出前不管哪个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均须以这一概念为基础。有罪判决作出前,尽管行为人在程序法上应推定为无罪,但司法(监察)机关在立案、侦查(调查)、审查起诉以至审判阶段(裁判前)均有权亦有义务对是否构成犯罪予以认定,并据此作出相应处理决定,追诉时效之适用亦然。裁判作出前均系“犯罪嫌疑”,此系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之规定;但是,在此之前,也应根据实体法上的犯罪概念,对是否符合犯罪成立条件作出判断,区分出裁判作出前之“犯罪”确证与存疑两种形态,追诉时效的适用要限制在裁判作出前之确证“犯罪”范围内。对于案件事实存疑,也就是证据不足,犯罪无从确证,则不得认为属于此处之“犯罪”,也就不能适用追诉时效。
本案二审裁判理由认为,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追诉时效,自诉人徐某甲起诉徐某乙涉嫌诬告陷害罪,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本案的追诉时效应为5年。而徐某甲控告徐某乙犯诬告陷害罪涉及的行为发生在2012年至2013年间,诬告陷害犯罪行为不属于连续或者继续状态,且本案不存在时效中断、延长等情形,故从徐某甲指控的事实分析,无论是以徐某乙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的时间计算,还是以徐某甲被采取强制措施,甚至从徐某甲被释放、被决定不起诉的时间计算,本案均已超过5年追诉时效。不难看出,不管是追诉期限,抑或追诉期限之起算时间,均系基于徐某甲指控的事实作出的判断,但二审裁判并未对犯罪事实予以认定。该指控内容经一审法院审查,属于缺乏罪证情形,对此二审裁判亦无异议。已如前言,其确立的规则是,刑事诉讼中对于追诉时效的审查和适用优先于对案件的实体审判。该规则赋予追诉时效适用上的优先顺位,即在对案件进行实体审判之前就要优先适用。对于案件实体审判之前,如果经审查认为构成犯罪,适用追诉时效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缺乏罪证的案件,并不符合追诉时效适用条件,其优先顺位并不存在。因此,对于该规则应予以限制,须将其限制适用在构成犯罪的情形中。在此意义上,一审法院以缺乏罪证裁定驳回起诉应属正解。
三、从追诉期限分析存疑案件应否适用追诉时效
追诉期限系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确定。但是,在案件事实存疑时,应如何确定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仅以涉嫌犯罪之法定最高刑来确定追诉期限难谓正当。
(一)存疑案件追诉期限之多种可能性
侦查(监察)机关立案、侦查(调查)、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均需根据犯罪事实对案件进行定性,也就是确定所谓涉嫌犯罪罪名。只有证据确实、充分,才能案件事实清楚;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如果案件事实存疑,根据有限的事实、证据对案件进行定性就不止一种可能性,例如同样一个用刀捅人的动作,既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也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甚至特殊情况下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然而不一样的定性,其追诉期限是不同的。再如司法实践中,案件被告人故意(放任)驾车撞死被害人证据不足,最后以被告人逃逸认定其全责,综合认定为交通肇事罪。[4]笔者认为,该案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理据并不充分,因为逃逸行为不可能成为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5]如果排除逃逸,则该案事故责任无法查明,被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即属存疑;此时该案不仅故意杀人罪存疑,而且交通肇事罪亦存疑。此种情况下,就有两种可能性,根据故意杀人罪(存疑)则不超过追诉期限,而根据交通肇事罪(存疑)则已超过追诉期限。
对案件每一种可能的定性均证据不足,由于定性不同,刑度即不同,或延伸至同一犯罪之不同刑度,而追诉期限由法定最高刑决定,由此追诉期限亦长短有别。就本案而言,诬告陷害罪有两种情形,对于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时法定最高刑是3年,追诉期限是5年;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时法定最高刑是10年,追诉期限是15年。在缺乏证据证实本案到底是情节严重还是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时,追诉期限就存在5年和15年两种可能性,该案二审裁判径以第一种情形确定追诉期限是5年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无论以徐某乙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的时间计算,还是以徐某甲被采取强制措施,甚至从徐某甲被释放、被决定不起诉的时间计算,本案是否超过追诉期限就有两种可能性,根据前者已超过追诉期限,根据后者则不超过追诉期限。
(二)追诉期限多种可能性之缺陷
存疑案件之所谓事证涉嫌某罪,仅系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性,即便这是司法机关根据现有事实、证据判断相对更为充分的可能性,却仍无法达到确证犯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程度。即使事证更为充分,甚至认为根据有限的事实、证据只有一种可能性,此种可能的行为定性也仅是一种假设,而不是以犯罪确证为基础,那么以此种可能的行为定性作为对犯罪的确证,进而以此确定追诉期限,就是建立在假设之上。司法实践中,常常归为“即使构成某罪,也已超过追诉期限”。[6]此时,与其说要确定的是案件所涉犯罪的追诉期限,不如说仅是针对与案件无关的单纯某罪的追诉期限,而这实属多余。更值注意的是,案件存疑时,案件定性有多种可能性,就难保不同的司法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对案件的认定保持一致,结果就是对是否超过追诉期限产生争议。其进一步的影响在于,因为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就面临司法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使个别司法人员有权根据行为人的具体情况,或选择轻罪名而使追诉期限届满,或选择重罪名而继续追诉,这将使追诉期限的判断流于恣意。这还可能导致因超过追诉期限之故怠于调查,而怠于调查可能丧失本该发现再行犯罪追诉期限中断的机会。
四、存疑案件适用追诉时效的法律效果优劣分析
司法实践中,关于追诉时效的法律效果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超过追诉期限可以完全终结刑事诉讼程序;二是认为对于存疑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在法律后果上更有利于行为人。但是,这两种认识均系思维上的惯性使然,实质上均非必然。
(一)超过追诉期限对于终止刑事诉讼程序不具有绝对意义
本案二审裁判理由认为,驳回起诉毕竟不等同于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如自诉人被裁定驳回起诉后又提出自诉,被告人仍然可能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局面,而以超过追诉期限为由裁定终止审理,则可以完全终结本案,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避免因诉讼程序反复运行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其实,以超过追诉期限为由裁定终止审理尽管可以终止程序,但追诉时效自带不彻底的基因,其适用本身就是一种允错机制。追诉时效作为刑罚量处事实或程序性事实,不仅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不同,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等程序性事实不同,其证明标准亦有差异,例如对于追诉期限延长或中断事由只要不能确证,即使存疑,亦不得认为该事由存在,如果事由确证即须重新启动程序。进而言之,本案中追诉期限是根据第一档法定刑中的法定最高刑来确定的,对应的是“情节严重”的情形,如果此时“情节严重”得以确证,即使“造成严重后果”存疑,此时应认为已超过追诉期限;如果事后另行查明本案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理所当然只要在追诉期限内就要再次重启程序,关键亦取决于事证问题。况且,本案中“情节严重”即属存疑,所谓“完全终结本案后续可能继续的程序”,实不过是一厢情愿之举,该裁判理由在逻辑上并不周延。相反,即使以缺乏罪证裁定驳回起诉,自诉人再次提起自诉,如果要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自诉人也须提出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否则也不可能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法院也不会轻易再次立案追究,刑事诉讼程序也不会反复运行。司法资源浪费之说亦属牵强,追诉时效制度固然有节省司法资源之考量,但仍须以符合其适用条件为前提。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这种自认一劳永逸的处理方式有限制自诉人诉权之嫌。
(二)对存疑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并非更有利于行为人
对存疑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并非更有利于行为人,以国家赔偿责任为例,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3项,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机关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然而,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3项,对于根据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条[7]等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属于免责事由,司法机关不承担赔偿责任,犯罪超过追诉期限就属于其中情形之一。既然司法机关被豁免赔偿责任,自然就由行为人来承担。而在以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和存疑不起诉情形下,司法机关不在被豁免之列。此时终止审理或绝对不起诉,对比无罪判决或存疑不起诉,对行为人更为不利。至于其论理,就存疑不起诉而言,《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关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视为无罪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批复》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对案件作出了无罪的决定。但是,因超过追诉期限之绝对不起诉,却是内置了已确证犯罪这一前提,存疑不起诉基于的是实体上的无罪,而因超过追诉期限之绝对不起诉,基于的却是在确证犯罪前提下刑罚之解除或纯粹程序上的障碍,二者差异在于犯罪之有无,国家赔偿责任正是以此为标准厘定赔偿与否之界限,也因此无罪的认定使得行为人法律地位更为优越。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无罪判决,其本身就是实体性的无罪判决,行为人优越地位更毋庸赘言。
本案在立案后被一审法院以缺乏罪证裁定驳回起诉,系未经实体审判即作出,与以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之实体处理方式不同,似应归于程序上的处理方式。但即便是程序上的处理,其赖以为基础的仍是实体上不构成犯罪,而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等仅属程序上的理由,应认为其效力与以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实质上相同。再予以延伸的话,可以溯及到受理审查阶段,按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20条第2款第2、3项的规定,无论是缺乏罪证,抑或犯罪已过追诉期限,审判机关均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自诉人不撤回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尽管处理方式亦属程序上的,但理由并不相同,以缺乏罪证裁定不予受理仍系基于实体上的理由。况且,缺乏罪证是第2项,而犯罪已过追诉期限是第3项,二者之先后决定着适用顺序;且根据追诉时效适用条件,二者是相斥的,不得同时适用。[8]因此,应当坚持体系解释原则,坚守追诉时效的基本法理,对于存疑案件不符合追诉时效适用条件的,不能优先适用追诉时效规定,否则可能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