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新质生产力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有两个维度要综合起来考虑。第一,人们已熟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概念,即科技成果应用方面前沿创新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加速升级并产生质变特征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当然是新质生产力。第二,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下,科技、制度、数据等和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这些供给侧要素组合的优化所形成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的阶跃式升级,引出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也是新质生产力。这两个视角应是综合的,第一个视角主要涉及实际生活中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第二个视角同时涉及所有的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质生产力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还需要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认识新质生产力。
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认识新质生产力
在信息革命、数字化生存和升级发展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得承认,是硅谷引领了人类这个信息革命的巨变,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也正在发力实现再升级。一些权威专家力求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认识,指出我们须正视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一波创新发展中还是落后的,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急起直追。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追赶这个升级发展前沿状态,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中央已明确表述了数字经济头部平台企业要“完成整改”,这是事关全局、长远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指导。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些企业努力在“互联网+”赛道上试错创新,少数创业企业熬过了痛苦的“烧钱”阶段迅速发展,出现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全局的头部企业。后以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为标志,进入整改。这是发展中必然会有的一种从起始高潮进入相对低潮ZYuiT9Wg/xWv5kJMZGPGMQ==的波浪式变化,整改的目标是为了让企业更健康的发展,而中央随之又非常明确地给出了概念——“完成整改”。2023年李强总理亲自主持了这个主题的座谈会,说明国家对头部平台企业的整改非常重视,希望它们起到带动上下游企业和整个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抖擞精神地打开新局面。
总书记之问意味深长
习总书记在一个座谈会上专门发问:中国的“独角兽”新增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总书记的发问意味深长,是需要我们进行全面分析、深入探究的。我们要在“问题导向”之下,进一步通过调查研究,认清其成因,有的放矢去解决。基于初步思考,我认为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值得讨论。
第一,应该承认,在最前沿的数字化科技领域,我们的原创能力和重大应用创新的支撑力不足。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创是极少的,闯出来的头部企业,比如一开始被评为“一飞冲天”的阿里公司,还有后面也很有影响的腾讯公司,他们的业务迅猛发展和巨大的市场影响,让外国人惊呼中国人轻易超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推出了在商业性金融轨道上普惠金融性质的扫码支付。然而阿里和腾讯所依托的原创技术是来自国外。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曾经注意到这个原创技术并推出了“飞信”,当时人们的手机上曾不断接到邀约短信,但飞信没有做成气候。然而腾讯的微信运用这个外来的原创技术,却终于熬过了瓶颈期;与此类似的是做扫码支付业务的阿里“支付宝”。这两个竞争者其实是互相成就的,在相互竞争中各自精益求精。虽然中国没有拿出原创技术、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重大的应用创新技术,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形成了支撑力。但是,这几年我们在这一领域继续发展的支撑力不足。
第二,我们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件建设方面,我们支撑力不足。几年来中央反复强调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自贸区开始试行的一套治理原则非常好:企业面对负面清单,而政府则是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对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可以放手试错创新;政府要自我革命限定行为空间,法无授权不可为,且匹配对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作量化评估并建立对执行者有奖惩的问责制。这是非常好的治理原则,但是贯彻落实还存在明显不到位之处。在“三年大疫”期间,我们的地方政府行为有明显的扭曲,一些地方甚至有不少出格的表现,以至现在我们还处在抚平疫情“疤痕效应”过程中。一个典型的表现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税收没有明显上升(近几个月还有下降),非税收入增长则相当可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不规范的“刮地皮”抓收入。政府机构如果要对一个企业倒查多少年追究在税收等方面的毛病,很可能就以“自由裁量权”把它搞死了。这样不符合中央规定的情况需要高度重视。
第三,破解“钱学森之问”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前沿创新领军人才的不足,包括对特殊人才的发现培养环境和对外来人才吸引力问题,都值得讨论。首先应看到,这些年我国在教育科技方面的投入是明显增加的,比如,我国现在从名校到地方的大专院校、包括职业教育学校,在硬件方面甚至跟欧美相比也不逊色,但是领军人才的发现培养的环境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它的后面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需要我们去探讨。

至少上述这三个方面,都和总书记对“独角兽”之问有关。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及其相互结合上,真正有的放矢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会有对布局和实施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的指导文件,我们需要很好依据三中全会这样的权威指导来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区域高质量发展初探:以成渝“双城”为例
新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调因地制宜。举国上下对此都很重视,也有很多讨论。因地制宜就是要更多地考虑,在一个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各个具体场景中,如何真正贯彻习总书记表述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指导方针。因地制宜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创新第一动力,落实于各领域、各个行业、各企业的具体场景,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供给侧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当下在扩大内需反周期的同时,结合跨周期的供给侧改革主线所面临的挑战性考验。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拿来就可套用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案,必须因地制宜做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例如,中国西部发展的战略枢纽中心——成渝双城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可提出的参考性建议。
我们成都重庆和整个西南地区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一阶段的数实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强调的“新基建”大有可为。它是以硬件为支撑的、不必按照传统的梯度推移方式,可以加快形成支撑力的基础建设。成渝双城打造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腹地,尤其需要注重作为数字经济“硬件”的新基建,要和老基建很好结合在一起。成都、重庆城市建设的老基建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新基建”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锦上添花、进一步发展?条件是肯定具备的。当然这种物质形态的新基建与老基建的结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软件结合,还要加上非常重要的“制度基建”,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三中全会指导之下,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显示自己的亮色?新、老基建加上制度基建,应该是三中全会的指导加上超长期国债发行中,“双城”遇到的现实机遇。
超长期特别国债解决的问题
首先,政府虽然并不适宜直接上阵去支持一些更适合由企业作为主体去试错创新的“人工智能+”前沿创新项目,但是相对而言,政府可以凭借在整体国土规划方面的相对优势、对于全国“一盘棋”式顶层国土开发规划管控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国家重大战略性支撑条件建设项目,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即用30年到50年的可用资金覆盖下来,不仅可以形成当下就可以增加就业、提升经济景气、扩大内需的效应,更加作用于中长期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以及长期、超长期的这样一个优化状态,进而给企业的前沿创新突破,提供高水平的经商与投资环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运用的空间是相当可观的,现在的1万亿元到50年后还本,压力就非常小了。1998年我国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本金到2028年才要归还。当时感觉是天文数字,现在还算什么问题吗?况且这是完全处在中国自己的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之内、我们要充分肯定政府可做的事情。

第二,在数实融合之路上,我们要更多注意大力培育地方的专精特新企业。我曾经参加中关村国家级战略规划研究,当时在讨论中提到要打造中国的硅谷。到今天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科研成绩,但没有冒出一个能够打开全局局面的头部企业。这说明前沿科技领域创新的不确定性,政府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发”。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尽心尽力,中关村概念之下在北京有星罗棋布的几十个点,发展状态蒸蒸日上,但还没有冒出像杭州的阿里、深圳的腾讯这样的头部企业。这可能是这一轮信息革命创新里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
我们的成渝、西南,可能要特别注意在专精特新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政府应对他们尽到大力发展和培育之责。而后面跟着的,有没有可能冒出来谁也想不到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头部企业呢?这是未知之数,但确实又是应当加以期待的。政府当然不是简单的等待,而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发展过程中,自己要争取积极而理性地有所作为。
第三,在欧洲和中国,政府的作为都有一个明显与硅谷不同的经验。硅谷主要讲政府的开明、宽容、低税、保护产权、公平竞争。而欧洲和中国都加上了政府介入的孵化器、创业园区、产业引导基金等。中国在这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尽心尽力做了不少前期工作,成渝双城应该是在已经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努力。但总结这方面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等等经验的基础之上,还得承认,那些风险度极高、或者说成功率极低的前沿创新、“人工智能+”的项目(比如,根据提出“独角兽”概念的美国风险投资家艾琳·李的统计,2003年以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6万家软件/互联网企业中,最终只有39家成功,即1538家企业才会产生一家“独角兽”——达到估值超10亿美元,这个比例不足万分之七),不是政府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直接去试错创新可能发挥优势的对象,这种试错创新的相对优势,只能认为是归于非政府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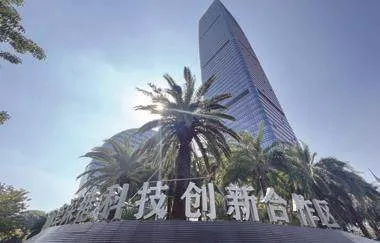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在各地区发展中,要积极引入和发展非政府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包括最前沿的天使投资。阿里公司一飞冲天的时候,据说人们惊呼“赶上风口的猪,没有翅膀也能飞上去”,而它冲过瓶颈期主要靠什么?马云曾经有几个阶段创业都不成功,到互联网+的时候,他到处去找支持资金来源,而人们几乎都把他看成是个骗子,但是据说他只用30多分钟说动了韩裔日本人——软银的掌门人孙正义,2000万美元天使投资,帮助他冲过了那个烧钱的痛苦阶段,一飞冲天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孙正义手上的股权爆炸式地接近600亿美元,财富膨胀3000倍。但是这种极高的风险项目,只有像这种风投、天使投资才可以去做,因为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一下子跌入失败的谷底。据说后来孙正义在印度做了一个大手笔投资,最后血本无归;后来又在美国有一个大手笔项目,眼看不行了,忽然又咸鱼翻身。这种过山车式的风险考验不适合政府和国有企业,一般而言只能由非政府主体,风投、创投、天使投资来发挥主要的作用。这样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建议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要积极引入和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当然,政府要更加注重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我国直接金融的比重,同时以中国特色继续积极探索产业引导基金,做好孵化器、产业新区等工作。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