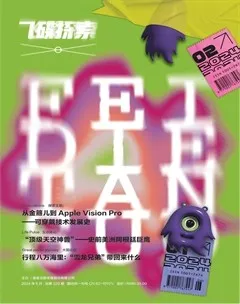新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储能,就是把多余的电先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相当于给电网安装一台大“充电宝”,使“靠天吃饭”的太阳能、风能发电都能稳定、流畅地接入电网,存储备用。
压缩空气储能则是以空气为介质充放电的“空气充电宝”。它性能优异,规模大、寿命长、成本低,发展势头迅猛。
与锂电池、抽水蓄能等其他储能技术相比,压缩空气储能非常“年轻”,在中国仅有1 0多年的开发史,却发展迅猛,成为后起之秀,令许多业内人士坦言“没想到”。
一张表
压缩空气储能的概念起源较早,第一个专利于1 9 4 9年在美国问世。德国和美国分别于1 9 7 8年和1 9 9 1年建成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并运行至今。虽然世界各国对压缩空气储能都有布局,但并不热门,真正将它发扬光大的还是中国。
2 0 0 4年,刚刚参加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程热物理所”)副研究员陈海生开始思考未来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给自己定下3条选定标准:朝阳产业、创新性领域、同工程热物理专业相关。但是,满足这3条标准的技术是什么?
经过3个多月的调研分析,陈海生相中了储能技术。这在当时是极其冷门的方向。
那时,我国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不足1%,是能源领域里的“小兄弟”,更不存在并网难题。那时的人们很难想象,有朝一日,太阳能和风能会撼动火力发电的主体地位,储能也将由“冷”转“热”。
陈海生画了一张表,纵坐标是各种储能技术,横坐标是创新性、技术成熟度、专业相关度等指标,结果压缩空气储能以5颗星领跑其他技术。但在当时,压缩空气储能在中国仅有理论研究,没有技术攻关,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空白。
如今回头看,过去1 0年,我国风电和光伏装机增长了8倍。2 0 2 3年,风电和光伏装机更是历史性地超过火电,占比达5 0.4%。储能不仅登上了能源发展的历史舞台,而且将扮演重要角色。
一场创新
2 0 0 5年,陈海生被公派去英国利兹大学访学,这是一次技术探索的好机会。
在英国,他和导师共同提出了液态空气储能的概念,很快得到6 0 0万英镑的经费支持。为了完成这个项目,原本为期1年的访学变成了4年的正式工作。最终,他们在2 0 0 9年建成国际首套兆瓦级液态空气储能装置。由于液态空气的密度远大于气态空气,该系统解决了依赖大型储气洞穴的问题,比传统技术更为先进。
有了这次试水,2 0 0 9年回国后,陈海生立志发展比液态空气更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
当时,传统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存在效率不高的缺点。德、美两国储能电站的效率分别仅为42%、54%。也就是说,存进去1度电,只能放出来大约0.5度,另外0.5度在存、放的过程中被消耗了。而且,传统压缩空气储能装置必须依赖天然气提供热源。
要从根本上突破这两大技术瓶颈,在中国走通压缩空气储能这条路,显然不能仅依靠模仿、改进,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技术创新。而创新的底气,源自我国科学家在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领域的多年积累。
传统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基于燃气轮机技术,在用电低谷时,利用富余的电能将空气压缩并储存在储气室中;在用电高峰时,释放高压空气进入燃烧室,同燃料一起燃烧,驱动透平膨胀机发电。这相当于让燃气轮机分时工作,储能、释能过程相互独立,最终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该系统的关键在于叶轮机械的高效运转。工程热物理所自1 9 5 6年建所以来,在叶轮机械方面研究基础深厚,创始人吴仲华先生是国际公认的“叶轮机械先锋”。
基于自身的“金刚钻”,2 0 0 9年,工程热物理所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在用电低谷时,用压缩机取代燃气轮机压缩空气,同时回收压缩热;在用电高峰时,释放储存的热量加热高压空气,驱动膨胀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这一改进不仅不使用额外的燃料,实现了零排放,还将原先浪费的压缩热能利用起来,储能效率大幅提高,理论上可达70% 以上。因地制宜,本土化的条件就此建立起来。但这一改,也意味着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技术,再到工程开发,都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
一堵“墙”
自压缩空气储能概念提出后,世界各国一直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技术路线,直到中国科学家提出换掉核心部件,业界才看到一条新路。但是,我国在这项技术上并无技术储备,更谈不上产业基础。陈海生形容当时面临的困难就像一堵墙。
2 0 1 0年,陈海生带领一支新成立的小团队,确定了一个“钉钉子”时间表:用3年时间完成1.5兆瓦示范项目,用4年建成1 0兆瓦示范项目,用5年建成1 0 0兆瓦示范项目。
项目需要攻克的除了核心部件压缩机、膨胀机的内部流动与传热机理相关的难题,蓄热蓄冷技术也是决定技术成败的一大关键点。
传统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需要补燃,消耗大量天然气,工程热物理所储能团队经过努力,用先进的蓄热蓄冷技术弥补了这一不足。并且,他们用的蓄热蓄冷介质是成本最低的水。“这是一个全世界都没有出现过的方案。”工程热物理所研究员王亮说。
要“啃下”这样的硬科技,必须具备足够的硬实力。从1.5兆瓦到1 0兆瓦再到1 0 0兆瓦,每一次规模放大,都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从原理到关键部件的重新研发设计。就这样,随着一个“钉子”接着一个“钉子”被楔入,在堵路的“墙面”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厚墙”终于被突破了。
2 0 2 1年,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在河北省张家口顺利并网,发电效率达到7 0.4%,每年可发电1.3 2亿度以上,节约标准煤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 0.9万吨。
通过进一步技术创新,山东肥城3 0 0兆瓦示范电站设计效率达到7 2.1%,与储能技术的“老大哥”——抽水蓄能相当。该电站年发电量约6亿度,在用电高峰可为2 0万~3 0万户居民提供电力保障,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 8.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 9万吨。未来,这将是更适合我国发电行业的主流技术路线。
“成本必须降下来,要大规模推广,无论如何都得降。”陈海生说,从投入研发的第一天起,他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一技术真正在中国落地,造福于民。
一个“螃蟹”
第一个试验台、第一个示范项目、第一个并网发电……一路走来,工程热物理所都在做中国压缩空气储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王亮至今记得,搭建第一个1 5千瓦试验台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场地,他们在两栋楼之间的夹道里搭了个顶棚、装了扇门就成了实验室。因为里面有一棵很粗的树,安装试验台时大家绕来转去,很不方便。
做技术攻关,试验台是必需品,但对一支刚起步的团队来说,这是“奢侈品”。由于投入巨大,2 0 1 2年建设1.5兆瓦中试平台时,经费非常紧张,必须集中所有可以用到的资源。
除了经费紧张,没有经验可循也是这些年轻人面对的一道坎。
“当时几名刚毕业的博士带着几名在读博士,经常在现场一待就是一个月”,那是大家第一次努力把科学思想变成设计图纸,再把设计图纸变成仪器设备。由于国内外都没有可参考的先例,每走一步都要靠自己摸索。
按照“研发一代、示范一代、应用一代”的发展策略,工程热物理所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持续发展,在上一代技术示范应用的过程中,下一代技术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始研发。这些年来,大家跟着项目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2 0 2 3年团队开年终总结会时发现,半数以上职工出差天数超过1 0 0天,有的甚至超过3 0 0天。
张家口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首次采用人工硐室,也就是人工开发的地下储气洞穴。由于这是首创的技术路线,施工过程中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大家笑称“总是‘吃螃蟹’也有点受不了”。
2 0 2 1年1 2月3 1日,项目成功并网的那一刻,在场的团队成员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大家激动地合影留念,一致推举现场唯一的女性——测试工程师付文秀站在“C 位”。她说:“压力虽然很大,但成功后获得的幸福感是别人不能体会的。”
一次成功
对于压缩空气储能的今天,很多人表示“没有想到”。
一些老先生曾善意地提醒陈海生:“进去4度电,出来3度电,你好好考虑,这个研究方向对不对。”
一位国内同行感慨道:“以前我们都不看好,因为技术上太难了,没想到真干成了。”
而在已经担任工程热物理所所长的陈海生看来,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在中国科学院诞生、发展,绝非偶然。他说:“第一,中国科学院鼓励创新,支持科学家开展前瞻性、需要长期探索的技术研究。第二,中国科学院有鼓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传统,能够支持一项技术从研发走到示范应用。第三,中国科学院能够形成大团队,开展大兵团作战。”陈海生介绍,压缩空气储能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需要搭建大平台,提供长时间、高强度的稳定支持。
储能研发中心现有职工和学生2 0 0余人。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储能产业迎来发展机遇,储能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但团队成立至今,核心成员一个都没离开。
王亮表示,在团队里干活踏实,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未来充满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能让我坚持深入干一件事,实现自己的理想,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