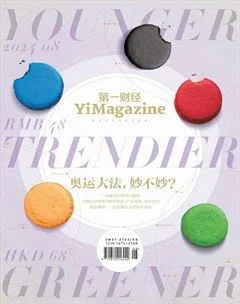Philippa Perry:我担心年轻人在手机上长大
YiYiMagazine
PPhilippa Perry

01
Yi现在,越来越多心理学名词因为大众传播在互联网上为人们所熟知,比如NPD、PUA、回避型依恋、煤气灯效应、情感操控……人们也越来越热衷于在网上谈论自己遇到的情感操控。这是一种时代变化吗?即媒介的聚焦带来更多的知识普及,从而带给不正直的人更多操控他人的武 器?
P我认为问题在于,人们很快就会指责别人,分析别人的行为,他们已经有了“勾选框”,所以可以把人一个个对号入座。他们没有审视自己的行为,也没有更多的同理心或好奇心去了解他人,所以会用一个标签或者一个名字,比如人格障碍,来定义他人。有的时候别人问我问题,他们会说,我的妈妈很自恋。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自恋”是什么,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母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许这位母亲是个大忙人,有时除了她的成年子女,还有其他优先事项;也许成年子女觉得自己有给母亲贴上标签的定义权。我想要的不是有人说我妈妈自恋,而是向我描述你妈妈的行为及她对你的影响。当人们把他人放在一个个“勾选框”里并贴标签,也就封闭了好奇心。
此外,我认为,即使人们给自己贴上标签,有时也会把自己说成是一成不变的。但人脑是可塑的,我们可以成长,可以学习,可以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大脑是灵活的。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框框里,就可能变得僵化,被困在“勾选框”里。
02
Yi给人贴标签确实是当代生活中一个很糟糕的现象。
P是的,我认为人们对很多心理学概念有些误解,它们成了标签化他人的工具。以“自恋”为例,如果你想创办一家新企业,你必须有一定的自我信念才能做到,如果你想成为流行歌手,你也必须相信自己。其他人都只是配角,但你永远是主角,这就是自恋。自恋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健康和不健康之分。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人,那就是不健康的。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即使是给他人贴上什么标签也都可以。只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方向错误的“捷 径”。
03
Yi你认为心理学术语和心理学概念的流行是件好事吗?
P浅薄知识的流行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人们太急功近利了,把它当成随手可见的小测验,而不是在以一种“那是一个人的整个复杂人格”的态度对待。我非常警惕心理医生给人贴标签,更不用说普通大众给人贴标签了。我非常不喜欢“他们看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一类说法。
04
Yi在专业的训练下,心理咨询师对情绪管理通常会有更高的自我要求,你们掌握的方法也更多。比如,你们会要求自己不能表现以及展示负面情绪。作为个体而言,你平常会发火吗?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吗?
P我不会压抑自己的情绪,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让任何一种情绪主宰我。如果我感到愤怒,我会表达出来,比如被开了一张停车罚单时我可能感到很生气。
我不会打人,不会攻击停车场的其他人,但我的愤怒会促使我对不公平的停车罚款提出异议。我是这样看待情绪的:情绪可以被看作员工向我们的汇报,我会像一个好老板一样,倾听他们的所有意见,无论我们认为它们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们都是有用的,可以为我们的行动和决策提供依 据。
如果假装情感不存在,或者压抑情感,它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浮现出来,也许是一种病态的方式。要把情感引导到有用的地方,不要压抑情绪。你可以怀着足够的愤怒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做,我希望你停下来。这就是有效地利用你的情绪。但如果我打人或喊叫,别人就听不到我说的话。所以,你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表达你的愤怒,但不应该是难以承受的程度,比如失控,你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05
Yi“我发现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网络交友当作购物,通过滚动鼠标和滑动屏幕来寻找完美的伴侣,就像在寻找一条心仪的牛仔裤。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完美伴侣并不存在。”你的意思是对自己所拥有的怀有满足心态。这是否意味着“错误的伴侣”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人应该选择在什么时候结束一段关系?以及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对一段关系抱以宽容态度?
P“错误的伴侣”的概念是存在的。如果你是一位年轻的异性恋女性,那么一个90岁的老太太不会是你的理想伴侣。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对完美伴侣抱有巨大期望是不现实的。与其认为自己有一个理想类型,不如对每个人都敞开心扉,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爱上了谁。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场婚礼上被她的朋友和另一个朋友撮合在一起。这两个相貌堂堂、志趣相投的人约会了几次,都不温不火,并没有真正来电。而婚礼上还有另一个男人,他的工作听起来很无聊,长相也不出众。但我朋友发现自己被他吸引住了。现在,这两个人非常幸福地在一起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他们自己。
我的意思是提醒人们不能像浏览购物清单那样找伴侣,你可能会被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吸引。所以,保持选择的开放性是很好的,不要以为自己有一份清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我们得到它的时候,就会知道它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06
Yi弗洛姆说,爱是一种动词,即爱是一种给予,而非索取。我发现一些人似乎并不相信这套说辞,而是更愿意相信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生命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P这听起来很悲哀,他们没有经历过爱。我会建议拥有这样人生的人多读小说,了解它。我们不一定非要感受到爱,才能以爱的方式行事。如果我们认识的人不能以爱的方式行事,我们仍然可以以爱的方式对待他们。
有一个非常类似的议题,我不确定是否相关。但我知道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是亲密关系的大敌。这个问题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尤其是一辈子都在智能手机陪伴下成长的年轻人。有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年轻人每天花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的时间超过2到3个小时,他们很可能会有心理健康问题,因为我们的生理结构并不允许我们手中握着手机这个额外的“器官”。人们在网上过着自己的生活,当帖子得到一个赞的时候,多巴胺就会立即发挥作用。你会沉迷于这些点击率,然后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关系比在网上难得多。
所以,我很担心年轻人在手机上长大,错过学习如何处理正常关系中的发展缓慢和各种困难。我认为Z世代可能是我们经历过的最不幸福的一代人,他们会发现处理人际关系很困难。如果你在成长的时代被封闭,不得不与家人隔离,就学不到社交技巧。我认为人在学校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友谊是如何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团体是如何建立的。他们在教育中错过了这一点,紧紧抓住自己的手机,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方向。我对此感到担忧。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并非所有年轻人都是这样,毕竟有些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很好地与他人交往。比尔·盖茨就说,他不会让任何孩子拥有iPhone或iPad,因为这会扭曲他们的大脑。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一切还是被不遗余力地推向了世界,这让我有点愤怒。这是一个悲剧。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注定要彼此相处。
07
Yi一个人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爱的能力?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得到过太多爱的人来说,要自我察觉并学会给予爱似乎更难?
P的确,这很难。如果一个个体在婴儿时期没有得到过爱和珍惜,那么他真的很难去爱和珍惜一个人。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可能只想从那个角度看他们,但这不是爱。真正的爱是去了解一个人,抛开对他们的偏见,这才是爱的方式。
爱的行为可以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做家务或按摩。当我们都以这种方式行事时,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这是最好不过的。比如我的朋友生病了,很沮丧,我可以带着我的工作去她家,这样我就可以陪着她。我尊重她,我爱她,能为她做些事情是我的荣幸。这就是我所说的“有爱心的行为”。我们不会总觉得自己在做这些事情,但我觉得这就像是,如果你身在别人的处境,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但很明显,你也要向别人确认,他们希望得到同样的待遇。
08
Yi从数据上来看,抑郁症、躁郁症等心理及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数在不断上升,这一情况甚至也出现在青少年群体之中。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P关于对疾病的诊断是有待商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所谓的“精神疾病”。我有时候会翻翻Facebook,然后就有广告出现了——“Hello,你有躁郁症吗?”“你可能有躁郁症,你应该去看医生。”这很有趣,但我真的没有躁郁症。人们在网上做了一个小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他们得了抑郁症,于是他们去看医生。这就像是社交媒体上的社会传染病。人们是如此沉迷于他们的手机,他们认为他们有注意力缺陷这样的疾病,但其实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失去了集中精力的意志,因为他们总是在玩他们的手机,他们的注意力管道已经因为手机而关闭。人们会说自己得了ADHD,但他们患上的其实是手机瘾,只要放下手机就能治愈。ADHD其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 病。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场多方决定的风暴。有一种完美的风暴会增加我们的痛苦感受,比如网络生活和那些吸引你注意力的头条新闻,它们总是利用恐惧来让你点击内容。我们在手机上获得了所有的信息,然后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社会传染。最后,我们认为自己生病了。想想看,倡导者都是什么人?你病了他们就可以卖出更多的东西。面霜是怎么卖出去的?他们会问,“你看起来老了吗?”。没错,我看起来老了,我也确实老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被广告操纵的。
09
Yi你有没有从多年的治疗经验中收获哪些特别的启示?
P我发现,当人们抱怨自己的人际关系,会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他们对对方抱有期望。当你对一段关系不满意,你的期望就会落空。如果你不能欣赏对方,就会成为那个满是抱怨的人。他们抱怨对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就像他们认为父母应该是完美的人,但很显然,没有人是完美的。就像父母也可能期待孩子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这些对别人的概念性期望总是会让我们自己失望。如果我们放下这些,其实会过得更好。当然,如果这件事不难做到的话,我就不会接到工作了。事实就是这样,认识现实是一个快速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方法。
10
Yi有没有什么你曾经相信,但现在持以怀疑态度的事情?
P我从小就不信神,我没办法信神。这让我很难过,因为我就是做不到。我想信神是因为我想有归属感。每个人都喜欢归属感,我也喜欢归属感。但小时候,我的家人都信神,而我4岁时知道了这都是编造出来的。我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我认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时代越不确定,未知数就越多。人们渴望确定性,这很危险,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支持给出看似最可靠承诺的政客,最后往往导致独裁的结果。我们需要学会拥抱不确定性,因为这实际上是我们所拥有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