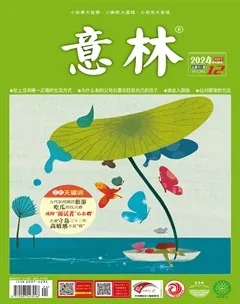攥一把芳香的泥土
故乡三面环山,土地不贫瘠也不肥沃,依然保留着传统农耕文明的习俗和风貌。置身故乡的田间地头,格外兴奋踏实。泥土的故乡,扎满我生命的根须,是我心灵皈依和朝拜的圣地。
难忘童年时代,我放学后扔下书包就去沟底岭剜菜、割草、放羊。麦苗浇过返青水,麦苗间弥漫着薄薄的雾气,伴随各种野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夏季,田间、沟底、河沿上的野草紧紧抓住大地,长得墨绿、茁壮、坚韧,那是上等的牲畜饲料。
我深爱土地,缘于我的祖辈,尤其是我的爷爷。爷爷每次下地,必须先把鞋脱了,直接光着脚板。爷爷说,地是通人性的,可不能用鞋踏。如果踏了,地就喘不动气了,庄稼也就不爱长了。因而全家人把土地当作恩人、亲人,春夏秋冬,义无反顾地爱惜、保护着。
父亲就像能感觉到土地的体温和脉动。他经常把责任田深翻整平、刨垄调畦,体味土地苏醒的喧哗与冲动。记得那年播种前,父亲走到地中央,深深刨了几镢头,轻轻跪下右腿,将十指插入泥土中,用力攥一把,看一看土地的墒情,放到鼻子前闻一闻,口里念叨着:“这土,多润呀!这土,多香呀!这土,多肥呀!肯长庄稼,种啥都成!”那是父亲一生重复了许多次的庄重礼仪和独特享受。人勤地不懒。那普通的土坷垃,在串串汗珠的浸润下,长出一茬茬小麦、地瓜、苞米,点缀着全家人幸福的鼾声。那把弯弯的镰刀,在父母布满老茧的手里,飞快地收割生活的希望。
记得童年时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捏泥巴、塑泥哨、摔跤等游戏,每项游戏都离不开泥土。山地上的土壤是砂土质的,干净,爽气。大家沐浴着温煦的阳光,手里抓满温软的浮土,让土从指缝里慢慢漏下来,看细土在头皮上、脖子上、肩膀上、胳膊上水一样流淌,挂在密密的汗毛上,一会工夫,个个除了眼睛外,都成了“泥娃娃”。
游子在外,根依然扎在故乡的泥土中,血液依然流淌在那片土地上。因为心里装着乡村的碾磨、土坯房、庄稼地和亲人,于是就有了根深蒂固的乡情和刻骨铭心的故园情结。
年复一年,土地一声不吭地奉献着。只要用犁深翻,依然露出一层层新土。万物生长于泥土,又回归于泥土。故乡的土地上,有我的祖辈辛勤耕耘的足痕和生活艰辛的泪滴,记载着一代代人的苦乐、荣辱与辉煌,包括安睡在山坡上的坟墓;又孕育着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常有婴儿清脆的啼哭划破山乡的黎明……
赤脚走在故乡的土地上,攥一把芳香的泥土,一股地气从脚底板一下传遍全身,顿增许多昂扬向上的力量。
(本文入选2023年山东省聊城市中考语文试题,文章有删减)
厉彦林,山东人,当代作家。已出版《享受春雨》《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赤脚走在田野上》等作品集十余部。纪实文学姊妹篇《延安答卷》和《沂蒙壮歌》,引起很大反响。已有130余篇文章入选各类教材、教辅,许多被选为中考试题或高考模拟题。
《意林》:标题中用“芳香”是何用意?
厉彦林:这缘于我在自家菜园地里手攥了一把泥土,那种感觉让我铭刻于心。春天的泥土是干净的,闻一闻有一股淡淡的土腥味、清香味。这淡淡的清香,在我脑海里立刻变成了芳香。泥土让人亲、让人爱、让人敬。让“芳香”二字入标题,能让读者感到新鲜,引起共鸣。
《意林》:文中是如何表达和描写对故乡的眷恋的?
厉彦林: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写我家祖孙三代深爱土地。另一方面,鉴于农村外出求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文中抒发了游子们根深蒂固的乡情和刻骨铭心的故园情结,还述说到人最终要回归于泥土,土地成为人一生苦乐、荣辱与辉煌的载体,从而升华了热爱土地的意义和价值。
《意林》:您对中学生作文写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厉彦林:我高中毕业后就当了当时我们管理区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知道写作文是同学们的头痛事。于是我坚持和同学们一起写、一起练、一起总结,慢慢我自己就喜欢上了写作,总的来看,写作不易,但也没那么难,妙招就是坚持多读、多想、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