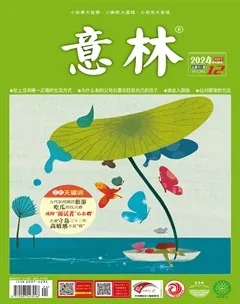包子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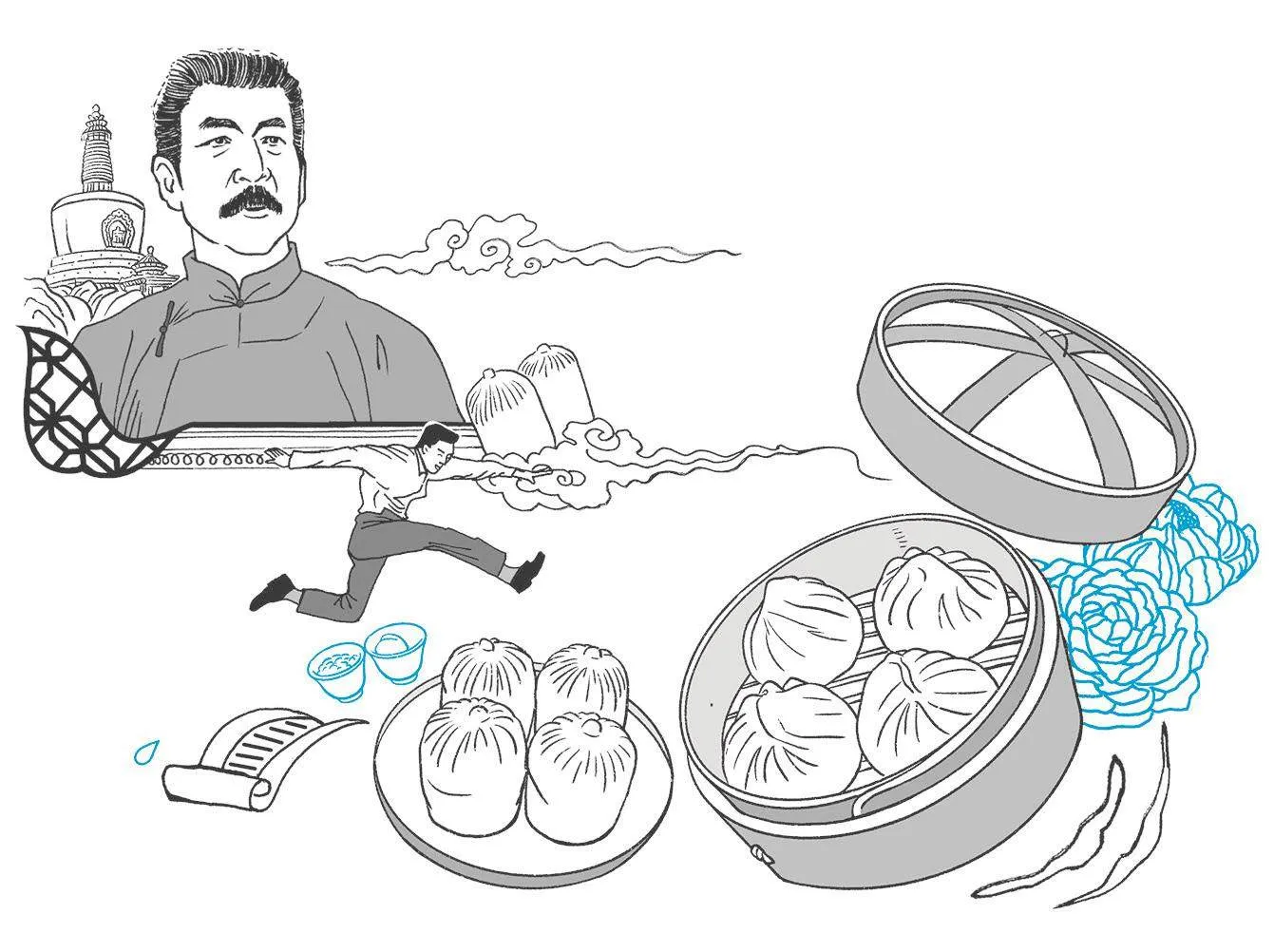
万物都有谱系,包子也是。一直以为,只有就着炒肝吃的那种包子才是标准的包子。一两三个,不大不小,正好用手拿着可以蘸炒肝的汤汁。肉汁浸在皮里,葱味揉进了馅儿里,融和相安。“和”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先王之道,斯为美”,搭着舒服吃着美,就是“和”了。
吃包子吃馅儿,老北京的包子,精髓却在皮上。这种皮说薄不薄,面却很筋道,透着光泽。馅儿不能填得太满,总要留有一些余地,中间鼓囊囊的,两边塌陷着,边缘上下的皮都叠在一起,趴在盘子里,总不那么挺拔。但就是这样留着余地的包子才更有诱惑力,眼看着香油沁到皮上,隐隐地像要从皮里流出来。一屉包子端上桌,总忍不住要抓看着最松弛、油沁得最多的那个。
这种包子讲究的是手上功夫,手劲大小与面的筋道有很大关系,和面不能拖泥带水,要干脆、到位、有节奏,还急不得。小时候看家人包包子,和面是道漫长的工序,不揉半个多小时不能下手切面。那时候最期待看捏褶,只见家里的女眷们聊着天,手上却丝毫不怠慢,两根手指轻捷地一捻,一层褶就出来了,左手一转,右手一团,一个包子就捏好了,简直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大概是因为包子太家常了,一种包子便会唤起一种乡情。在很多北京孩子的印象里,只认这种不大不小,又不那么工整的包子。杭州小笼包一口吞一个,不过瘾;山东酱肉大包又太大了,一个人吃不完。
一度,因为便捷省时,杭州小笼包曾占据了北京大街小巷的早点摊儿。小笼包吃着快,包着也快。师傅一舀、一捏、一攥,一个包子就好了,这种生意做起来很是便利。这大概皆因北京极强的包容性,无论来自天南海北,都会被融进这座城,入到此地,慢慢就随了此地的乡情。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冬菜包子很有名,据说鲁迅当年常去吃。冬菜包子扎根北京算来有百余年了,它更像是京城包子谱系里的老资格,却是地道的外来户。
店不大但是名气不小,当年的文人名士如林徽因、张恨水都经常光顾。鲁迅更是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写他的书稿,翻译他的文章,每次必吃的就是冬菜包子,用他的话说叫“可以吃”。倒不是因为味道有多难舍,只因“包子、汤面最方便”。
现在卖的冬菜包子做成了鸟笼形,高帮的,像是给包子穿了双皂靴,很有特点。不知是为了凸显京韵而特意设计的,还是鲁迅吃的包子就长这样,留出这样的厚底实在要费一番功夫,不懂捏褶的我想象不出是怎样一种操作。而这大概也是种态度:造型承袭了南方人的精致,个头是北方人的大气,当然还有老北京的讲究和浓浓的文人味。
有一阵子,我吃早点常叫一家小笼包的外卖,每次送来时,包子一定要整整齐齐地围着餐盒摆成一个圆,保证它们在屉里什么样,在盒里仍旧什么样。我问老板,这样多费事,有打包的工夫能多送几屉外卖。他说,得让人拿到手里看着顺眼,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多一道工序多一点好评,还是赚的。
是啊!做事不就得有模有样吗?就是一只包子也有自己的形象,有生活的态度。想起家人手捏的那些包子,虽没有那么好看的卖相,但是寻常而有味,不张扬也不委曲求全,总是给自己留有余地。这些是我至今没能捏会的褶,也是至今没尝透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