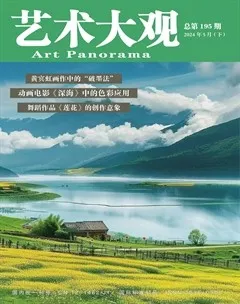肖邦《第二叙事曲》的“悲剧性”及演奏特点


摘 要: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诗人”,其名曲《第二叙事曲》深刻抒发肖邦个人情感,映照波兰民族历史与时代精神。文中溯源其创作背景,通过剖析作品音乐结构、和声与调性布局的变化,阐述了音乐内部的冲突张力,揭示其作品蕴含的“悲剧性”元素;且挖掘该作品的演奏特点,指出演奏者需精准把握作品悲剧基调,通过细腻触键、运用踏板及力度变化,将肖邦音乐中的“悲”、痛苦等复杂情感细腻呈现。综上多维度解析,旨在为理解肖邦此曲的“悲剧性”及演奏艺术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关键词:肖邦《第二叙事曲》;“悲剧性”;演奏特点
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05(2024)15-00-03
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钢琴作曲家之一。肖邦的四首叙事曲是其钢琴作品中的巅峰之作,而其中的《第二叙事曲》,是在肖邦生命中重要创作阶段完成的,当时他正在应对欧洲的政治动荡以及个人的健康问题,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他的创作灵感。本文将通过对肖邦《第二叙事曲》的悲剧性及其演奏诠释进行深入分析,从创作背景、作品中“悲剧性”的体现、曲式结构与演奏特点等多个角度探讨这部作品的“悲剧性”和演奏难点。
一、肖邦《第二叙事曲》的创作背景与文学性构思
(一)创作背景
肖邦的《第二叙事曲》创作于1836—1839年间,出版于1841年,在此期间,肖邦的健康状况不佳,他患有肺病,这使他时常感到虚弱和痛苦。这一时期,欧洲正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1830年,波兰爆发了旨在争取从俄国统治下独立的“十一月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这一事件对波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一名波兰人,肖邦深受其祖国命运的影响,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忧虑。
《第二叙事曲》在此背景下,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响应。作品中的悲剧性色彩和深沉的情感表达,反映了肖邦对波兰动荡命运的感慨和对个人生活中种种苦难的思考。
(二)文学性构思
肖邦的四部叙事曲与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兹的叙事诗相关。舒曼在对肖邦作品的评论中指出,肖邦的叙事曲灵感来自密茨凯维兹的诗歌。《第二叙事曲》与密茨凯维兹叙事诗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美国钢琴教育家爱德华·巴克斯特·培里认为,肖邦的灵感来自《希维德什》。另外,由于《希维德什》和《希维德什扬卡》两首诗歌都包含湖边景色描写的诗句,一些学者认为《第二叙事曲》与《希维德什扬卡》有关联[1]。
《希维德什》和《希维德什扬卡》是密茨凯维兹根据波兰民间传说创作的叙事诗,它们都与波兰的一段民间故事紧密相连。这两首诗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描绘了田园般的湖光山色和美丽的姑娘,这与肖邦音乐作品中的两个主题和形象相映成趣。肖邦在创作中并非直接复制叙事诗的具体情节,而是依据音乐的形象和情感,对密茨凯维兹的诗作进行了自由联想。他的构思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音乐性诠释,而非简单的情节再现。
二、肖邦《第二叙事曲》中的“悲剧性”
(一)音乐结构的戏剧性体现其“悲剧性”
《第二叙事曲》采用了奏鸣曲式主题对比与非规范回旋曲式相结合的曲式结构(见表1),两个性格鲜明的主题不停地交叉出现,变奏,具有强烈的对比性和戏剧感,戏剧性的音乐结构体现了其“悲剧性”。
A段第一主题采用了柔和的旋律线条与和谐的和声,营造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氛围。纵向的四部和声贯穿第一主题,主要是主属和弦与下属和弦的变化,同时左手伴奏平稳进行着。这一主题田园牧歌式的表达,不仅让听众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和美丽,也传递出一种内心的平静与安详。然而,这种宁静很快被B部分的狂飙风格所打破,形成了作品中的第一层对比[2]。
B段是作品的高潮段落,也是第二主题的呈式和展开。其旋律急促而激烈,节奏紧凑而富有动力,和声也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这种狂飙风格的表达,不仅反映了肖邦内心的激烈情感和矛盾,也象征着波兰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变革带来的不安。B段的音乐语言,充满了戏剧性和冲突性,与A段的田园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冲突和对照是这首叙事曲音乐构思的一个基点,整首乐曲正是建立在这个矛盾对立的基础之上。[3]这种对比,正是《F大调第二叙事曲》悲剧性表达的核心所在。
A¹段是第一主题的再现,随着第二主题逐渐消失而浮现。在这一段落中,作品的悲剧性和叙事性达到了顶点,展现了恐惧与激情的交织。这种情感的对立正是作品“悲剧性”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肖邦性格的复杂性和他内心的焦虑。
在B¹段中,第二主题再次呈现并进一步展开,如同一场猛烈的风暴。与之前的平静不同,通过和声与调性的转变,逐渐与第一主题相融合。突然的调性转变与和弦的非传统连接,创造出不可预测的音乐效果。此时,第一主题也不再保持其温柔宁静,而是以坚定而深沉的低音和高音区激烈的颤音相结合,为听众带来强烈的震撼。这两个原本对立的主题在此实现和谐,为作品的尾声铺垫,生动地展现了整部作品的悲剧性冲突。
肖邦通过对A部分和B部分主题的再现和变形,将整部作品推向高潮,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性色彩,也是对作品整体情感的升华。特别是在Coda的结尾部分,音乐逐渐变得平静而沉重,似乎在暗示着一种无奈与悲伤。
(二)无序自由的调性布局及和声进行体现其“悲剧性”
肖邦擅长通过和声变换增强色彩对比,特别是明暗之间的对比。他扩展了下属功能和声,采用了半音和声和线性和声技术,《第二叙事曲》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作品的第一主题以纵向和弦式的和声织体呈现,节奏稳定,音响色彩纯净,营造出宁静明亮的意境,如同月光下平静水面的倒影,同时暗示着人内心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和憧憬。在A部分中,调性从F大调—a小调—g小调,最后回到F大调,这种半音级进的调关系增加了旋律的动力性和和声的张力。
第二主题的音乐织体产生剧烈变化,左手八度敲击的旋律短句与右手波动的音流,将调性从明亮大调转为阴郁小调。这种对比不仅构成了全曲构思的基础,也让人联想到密茨凯维兹叙事诗中的紧张和戏剧性。和声进行以带有和弦外音的小三和弦和减七和弦分解的技术性六连音为特点,就音域而言,左右手分别从极高或极低的音域开始,接着迅速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这种巨大反差所带来的震撼加强了音乐的冲突感与“悲剧性”[4]。
当第一主题再次出现时,音乐织体变为多声部,调性频繁转换。再现的第一主题在情绪表达上更为强烈激动,与呈示部中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却又在矛盾中实现统一。
尾声以a小调结束,与F大调形成三度调关系,这种首尾调性不统一的现象正契合肖邦无序自由曲式的逻辑布局。乐曲最终并未回到最初的大调,而是在小调中结束,增添了一层暗淡的情感色彩,增强了结局的“悲剧性”。
三、肖邦《第二叙事曲》的演奏特点
(一)第一主题:抒情性乐段的演奏特点
《第二叙事曲》的第一主题平静柔和,旋律清晰稳定。乐曲开头的同音递进,如溪流般缓缓流淌,演奏时应采用指腹贴键的方式触键,柔和而均匀地弹奏。音色应柔美而清晰,具有歌唱性。在第一主题中,右手的高音声部始终是旋律声部,演奏时要一直清晰明确右手高音的旋律,同时要像唱歌一样,旋律干净且具有歌唱性。乐曲的开头节奏平稳,手腕与键盘平行。低音和次中音声部的轻微旋律起伏也很重要,应注意音乐的推动力,它就像起伏的水流推动着声音向前,并随着乐曲的发展给人以田园牧歌般的流动感。
为了对看似简单却深具内涵的第一主题进行恰当的诠释,演奏者必须了解整首乐曲的悲剧基调,才能合理地将音乐形象直观化,并产生相应的情感处理。由于主题情感的细腻和力度变化的微妙,音色的掌控成为乐曲演绎中的一个难点。演奏者需在有限的力度区间内探索多样的情感表达,以展现乐曲的“悲剧性”色彩[5]。
通过调整手指触键的位置和速度,可以实现音色的多样性。在旋律流畅且情感丰富的乐句中,演奏者应保持手腕的自然放松,利用力量的传递,让指尖以较快的速度触键,以产生圆润而明亮的音色。在第一主题接近尾声,为第二主题的引入做铺垫时,应使音色渐趋轻柔,仿佛轻纱缥缈,通过指腹的轻柔触键,让每个音符都如同轻触般逐渐淡出,直至声音完全消散。
通过巧妙使用踏板可以创造出多样化的音色效果。在乐曲的起始和结束部分,采用弱音踏板与音乐的情感表达相结合,通过它来实现声音的渐弱效果。在需要更细腻的音量控制时,可以适当地利用弱音踏板来达到所需的效果。
无论是通过踏板的调整还是改变触键的方式来塑造音色,演奏者都必须培养用耳朵聆听音色、用思维去分析音色的习惯,确保演奏出的音色不仅符合乐谱的要求,还与旋律的走向和音乐的整体形象相匹配。
(二)第二主题:“悲剧性”演奏特点
第二主题以极其迅猛之势突然袭来,宛若一阵猛烈的飓风,在节奏、力度、调性与旋律线条上,与第一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赋予了音乐一种戏剧性的转变,为作品增添了“悲剧性”色彩。第二主题蕴含了极高的技术挑战和剧烈的情感冲突。在开始演奏之前,演奏者必须对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的界限有明确的理解,并在第一主题接近尾声时,提前布局铺垫第二主题的演绎,以便产生强烈的听觉冲击[6]。
进入第二主题时,首和弦必须以强烈的情感与明显的对比来呈现,其力度达到ff,尖锐的减七和弦与带有倚音的小三和弦交替出现,高低声部的冲击、紧张感与戏剧性迅速显现。演奏者需从平静的第一主题脱离,在此乐段表现出乐曲的“悲剧性”。在弹奏第46小节时,演奏者需要在内心感受到一种倾向,面对沉稳有力的八度音(见谱例1),左手手腕要充分支撑手臂的力量,使手臂与手腕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腕关节和掌关节的协同发力,指尖迅速触键,以产生具有爆发力和力量感的音色。进入第47小节,左手的小指要特别突出,而右手的上下行模进与转调则不断推动情绪向上攀升。
右手的连续琶音技术要求演奏者在小指站稳的同时,用手腕带动手指触键,以达到明亮且穿透力强的音色效果。在第二主题的前12小节中,音乐持续地进行着动荡不安的发展。在59—62小节,音乐采用了第二主题的动机,以持续下行的方式,形成了一条大连线。在演奏这段音乐时,右手的双音应该被强调,作为重音来弹奏。同时,左手的八度音要流畅地连接,达到一气呵成的效果。为了左手的八度音的自然连接,可以利用气息与踏板的技巧。
在第70—78小节的段落中,随着音量的递减和节奏的调节,演奏者需确保右手的和弦弹奏既稳定又精确,即使音量逐渐递减,也应保持弹奏的深度。可以类比为海浪逐渐减弱的过程,一波接一波,逐渐减小。与此同时,左手的音阶演奏应采用贴近琴键的弹奏方式,避免产生过于明显的颗粒感,仿佛潮水退去,逐渐恢复平静,第二主题逐渐落下帷幕,向着宁静的第一主题过渡[7]。
四、结束语
《第二叙事曲》巧妙地将自然界的景象与肖邦深刻的内心世界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艺术上的和谐统一。整部作品充满“悲剧性”色彩,这种“悲”不仅反映了作者自身的情感体验,而且涵盖了波兰民族乃至其所处时代的全貌。该作品的“悲剧性”也在其音乐主题与结构、和声的冲突、对比与变化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演奏者在演绎此作品时,需要深刻理解作品的悲剧基调,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作品的情感内涵相结合,通过合理的音乐处理和情感表达,将作品的悲剧性直观化,使之成为触动听众心灵的艺术表现。
参考文献:
[1]钱仁康.肖邦叙事曲解读[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
[2]雷吉娜·斯门江卡.如何演奏肖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3]于润洋.悲情肖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4]刘庆钢.钢琴的演奏与教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5]舒曼.论音乐和音乐家(中译本)[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
[6]史小亚.肖邦叙事曲音乐标题性解读——以《F大调第二叙事曲》为例[J].音乐天地,2017(03):45-48.
[7]冯羽.评于润洋著《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J].音乐研究,2010(05):1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