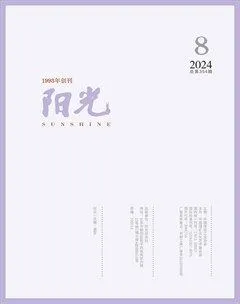青莲阁随想
山与水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山水相连,相互映衬,两者联袂生发出万千气象和繁纷意象。它们共同织就了一个经纬度,山为经,是高度;水是纬,有长度。只是这里没有山,只有阁——青莲阁,而阁同样有高度,虽然不似山一般巍峨,没有自然高度,却有文化高度。这里还有水——泗河。阁与水同样互相映照,释放出斑斓气象。
阁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有阁就有人登临,就可以向水歌吟。古人登临,大都和水有关。王之涣登鹳雀楼看到的是黄河,王勃登滕王阁眼前呈现的是赣江,范仲淹写岳阳楼,凝望的是洞庭湖。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是在泗河西岸。
对于青莲阁,我心仪已久。站在青莲阁下面,我没有急于登临,而是先在远处端详着,思忖着。青莲阁与泗河,一个是凝固的音乐,巍然矗立;一个是欢快的精灵,轻盈地腾跃。60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相互交流,律动。
前面的十几个台阶正对着青莲阁,我在想有何寓意。
我端详着青莲阁,它重檐飞翘,彰显出凛凛气势。如果兖州是一曲文化交响乐,青莲阁就是华彩乐章,虽然不是唐代所建,却辉映出李白的傲然风骨,盛唐的雍容气度。
我注视着青莲阁,在想着它的阁局与格局。后人为了纪念李白建造了青莲阁,就是因为他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是因为李白的诗,更因他的人格魅力。这里是一个场,磁场和道场。磁场,就是凝聚,把人们吸引过来。道场,就是弘扬,把一种精神渲染出去。
青莲阁不是李煜的凄楚西楼,也不是陈子昂的悲怆幽州台,这里没有悲哀、凄惨,只有豪迈、豪情。青莲阁不是物质的砖墙结构,而是诗句构成,有着精神的支撑,思想的建构。李白的格就是人格,他的格撑起来一个阁,这个阁不仅是物质属性,更是精神特质,它有体量,更有当量,而且是核当量,因为有了李白的精神内核。
公元736年,唐王朝仍是盛世,36岁的李白也正值盛年,这时,他来到了兖州。随他而来的,还有太白雄风。这风,是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是他的古风,是历史之风的鼓荡,是泗河漫卷着的波涛,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
青莲阁被赋予了人文属性,写实与写意相对应。就像中国的文人画,就是写意。此时,我凝望着青莲阁,就有了这样的意念,它是写实,因为青莲就是李白。同时也是写意,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具有丰富的意蕴。它是青莲阁,更是文化阁,精神阁。
青莲阁虽然位于兖州最东面,与泗河毗邻,相对于兖州的西面高楼林立,这里位置偏僻,一片寂静,但是并不寂寞,600多年来,有泗河的波涛与它为邻,李杜的诗歌在身边回响。一个楼阁,一条河流,本来都是物质属性,因为一个人的存在,浸润了浓郁的人文情怀,有了历史的承载。青莲阁已经成为兖州的一个名片,一个文化符号,它的飞檐斗拱是一个时代文化气韵的张扬。
我拾级而上,古人的审美意象可谓千形万象,就是一个楼阁,也会生发出缤纷多彩的意象,一个栏杆,衍生出拍栏,凭栏,倚栏。辛稼轩的拍栏,岳武穆的怒发冲冠,凭栏处。青年毛泽东登黄鹤楼,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无论是何种举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浓郁的家国情怀。
古人登高望远,不仅是一种行为举止,已经羽化为一种审美、文化现象。我登上了青莲阁,虽然无古人的那种高迈,雅致,既然上来了,站在这里,也是一种登临吧,感想自然会生发出来。一个楼阁的最大亮点是什么,它有一个纲,就是文化,文化具有辐射功能。在这里,人、阁楼、景物融为一体,成为多元组合。
我现在登临,已逾花甲之年。虽然我是第一次登临,可是和青莲阁早已神交。1981年,三十二处建设鲍店矿北风井,我就在那里参加了工作,就在泗河的左岸,自兹始,已经领略了从青莲阁带来的气韵。清晨,我常在大堤上跑步,或者是骑自行车北去,沿着泗河大堤去兖州新华书店买书。到了泗河大桥,总是向着东北面青莲阁的方向投去心仪的一瞥,同它有了精神的对接。那时,我对古典诗词兴趣正浓,而买的有关诗词书籍中,就有一套北京出版社的《唐诗选注》,是上下册。其中李白的诗歌我很钟情,能够背诵20多首。他的诗如同阳光,冲散心里的阴霾、愁绪,让年轻的心激情澎湃。
青莲阁砖木结构,三间上下两层。这座阁楼,不仅是一个物质建筑,地标,还是一部兖州文化史,象征着诗歌史的一个高峰。我细细品咂,它的大梁是李白的风骨作支架,我仿佛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在阁楼四围回旋。
公元736年,李白来兖州之时,杜甫也刚来到。李白住在城东门外,东面不远就是泗河;家的南面有沙丘,沙丘往东靠近河边就是尧祠;沙丘往南是酒仙桥,从桥往东就是石门与金口坝。
青莲阁不仅当作一个地标,还是文化坐标,不仅横向看,还要纵向观,它还是一种精神传承。我想,为何叫阁,而不是楼,细细想来,楼和阁的区别在于,阁虽然是脱胎于楼,却是架空的楼。这是和楼房的区别,正因为它的镂空,它的空旷,正可以鼓荡起风。这种风既是自然之风,更是文人雅士们吞吐出来的文化之风,精神之蕴。
青莲阁下面的这片土地,就是李白经常和杜甫相会之处。李白来了,杜甫来了,他们在兖州相会,我想象着,那个时辰,兖州的天际一定是祥云缭绕。太白金星和文曲星在这里相会。歌未竟,东方白。想必泗河的波涛也在绽放笑意,两边的树木也伸展双臂为他们鼓掌。他们带着瑰丽的华章丽篇来了,而泗河本身就是弦歌地,它多少年来就在鼓歌而行,它的波浪就是跳荡的音符。在这里,泗河与李杜,开始了新的奏鸣。
虽然李杜不是官吏,不像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挂着刺史、通判的官衔,一边做官,一边吟诗,还行着善事,为当地百姓留下了白堤、苏堤,但他们都是一样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用诗歌抒发对于家国的赤子之情。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就足矣。
总以为,怀古是为了察今。只是回头一瞥,时光越千年,没有李白、杜子美飘逸的身影,目之所及,我看见的是前面的一所医院,而且引人注目的是特别突出了一个诊室:精神科。围栏上面还用醒目的字符祝福人们精神康健。我不知道,那些前来就诊的人们是什么心态,可是有一个共性问题,也是现在人们普遍的症状,就是焦虑,抑郁。
医院阻挡了我的视线,却阻挡不了思维,阻碍不了思想。李白当年在这片土地上歌吟,没有医院,也没有楼阁,他的思绪是长风呼啸,他的胸腔里汹涌着激越情愫,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我想,现在很多人心情郁结,心理上焦躁不安,主要还是现代人心理、精神层面的因素。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理一旦被消极的情绪控制,就会形成“堰塞湖”,需要疏通,而李白的诗就是最好的导引。如果年轻人能够读一读李白的诗,内心会充盈着浩然之气,豪迈之情,使人心情奔放,神情俊朗。
我站在这里,感念不断漫溢出来。按照古人的传统,站在这里,或者倚栏,或者拍栏,可是我却是一个凡人,只有正襟危站,让思绪牧放。凛冽的东北风漫舞着,从额头上掠过,它是从泗河吹来,有湿漉漉的感觉,这是泗河的风韵,有乐感,就像一串音符在跳跃。我仿佛看到了那条从位于泗河畔的北风井蜿蜒过来的小路,泗河对我是一条岁月的彩带,从青春年华,到花甲之年。今天,终于在这里相聚。光阴似箭,青莲阁正好和泗河相向而行,我感觉泗河就是一支利箭,笑傲前行。
我忽发奇想,如果那些著名的登楼的古人们集聚在这里,会是个什么景观,王粲一定是眉宇间英气勃发,范仲淹蹙着眉忧国忧民,陈子昂脸色怆然。这里会有一场奇幻的辩论,而这些金玉之音会成为历史文化的回声,鸣奏出洪钟大吕之音,在青莲阁周围萦绕。
年轻时,我以为泗河、青莲阁都是单一的存在,后来才明白,它们是近邻,这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意象。青莲阁的外表不需要色彩斑斓,也不需要多高,李白的身姿就是高度,高格。青莲阁的高度是精神。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可争日月传。李白的诗就是最好的色彩,足以让这个阁楼花团锦簇,流光溢彩。
古人登楼,临水,生发出缤纷意象,万千星辉。一个楼,一个阁,在他们眼里熠熠闪光。登高,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高度,是物理的高度,更是精神的高度,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有了精神的高度,就有了崇高感。
现在的人们基于生活压力,也喜欢登高望远,只是登山的多,登楼阁的少,倒是爬楼的多。我们身居闹市,蜗居楼内,虽然也有阁楼,可是被禁锢了,目之所及,满目的钢筋水泥丛林。人的身体不能缺少水的滋养,同样,人的内心亦需要滋润,虽然不像古人那样登高抒怀,心里面收藏下若干首唐诗宋词同样也是一种陶冶与慰藉。
我们在青莲阁下合影,每一个人眉宇间都是神采焕发。作为背景,青莲阁的眉宇也是英气飒飒。先有存在,后有意识,后人为了纪念李白修建了青莲阁,还是因为他的诗篇,人格魅力。有了他的格才有阁。我们后面的青莲阁,也在发出会意的微笑——
绣口一开半盛唐,青莲阁上镂华章。
轩阶掷笔滋阳耀,斗酒投诗泗水狂。
亘古精神辉日月,从来物欲黯玄黄。
最痴儿女门前戏,饮马天涯未敢忘。
毕季清: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能源兖矿集团退休职工。在《文艺报》《中国煤炭报》《花溪》《山东文学》《北方作家》等发表散文多篇。报告文学《借衣服领奖的采煤工人》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人民网联合举办的“他们是时代的领跑者征文”一等奖。散文《高原的月亮》收入作家出版社《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灯盏·2019》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