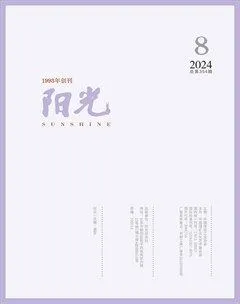老羊倌和信
老羊倌和信住在村子西南角上的一座石屋内。
那是一座建在半山腰上的石头房子。房子贴着石壁建起来,偏东南斜向,有三间。石屋旁边,是一溜贴着石壁的圈棚,外边扎着栅栏。石屋中间开门。北屋靠石壁有一个天然石台,伸进屋子内有将近两米,屋子里搁着几条许久没人坐过的旧板凳。南屋内有个套间。套间是一个宽三米、进深四米多的山洞。洞内靠里是个大通铺,能睡七八个人。床板架在洞壁两侧和一道垒在中间的石脊上,离地很高。床外放有一个老式立柜。床板下空空的,可以看出山洞由宽收窄的缓慢走势。光线暗时,洞内总是黑乎乎的。老羊倌和信说,在这屋子里住久了,进进出出时,就有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每天上午,和信都在屋前的门墩上晒太阳。就是夏天,他也披着一件老羊皮袄。这山上的石屋,很少有村子里的人上来。它像是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遗忘。
太阳晒着他。起初他还能看见远处村子边的漳河。水流在他模糊的视线中泛起一片闪闪烁烁的银色。看水容易让人犯困。一会儿老羊倌就睡着了。睡着了,他的梦里跑的就都是羊群,看不到边的羊群,是那种艾山地区独有的黑山羊。羊群是黑的,他的梦也就黑乎乎的一片。梦里也有像是云朵的东西,一块块地飘来飘去。那是黑羊群中的几只白羊。艾山人放羊,总是在黑羊群中夹带几只白羊。问牧羊人为啥要这样做?都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具体原因谁也说不清。
羊群还在跑。像是在他的身上跑。羊蹄子踏在他的胸腔上,就像是鼓槌有节奏地敲在鼓皮上。他喜欢这声音。他觉着自己的身子在跟着一个纷乱的节奏颤动。好似他也跑起来了。
年轻时他能一口气跑两个山头,去会山那边的女人。然后再一口气跑回来。
和信跑回来时,他的羊群还在一道沟里耐心地啃吃酸枣棵上的嫩叶。
那时,他真能跑啊。和信都不相信自己这么能跑。人年轻,能跑,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他在梦里对自己那些能跑的时光充满了怀恋。就在他的怀恋中,羊群从他的梦中跑过去一波,又是一波。
羊也能跑。艾山的黑羊,那一身鲜美健硕的膘肉,也都是跑出来的。
不过,羊跑的样子,在和信看来,就跟走一样。
细狗老黑最能跑。年轻时和信和它赛过。他一次都没跑过老黑。老黑能跑的结果,就是隔上几天,就给他逮住一只野兔子。艾山的野兔子,也能跑。但它们像和信一样都跑不过老黑。老黑逮住野兔子,他吃肉,骨头都是老黑的。一个野兔子头骨,老黑能叼上六七天,不停地玩儿。他把它扔出去,老黑就叼回来。再扔出去,它再叼回来。晚归时,这个野兔子头骨他就放进自己的背袋里。老黑只有看到和信把头骨放好了,才追着羊群往回走。
老黑也闹情绪。心情不佳时,野兔子凑到它的嘴边,看都不看一眼。那时,老黑总是表现得很烦躁。羊还没吃饱,它就在沟地里不安分地跑来跑去。和信躺在向阳的坡地上眯眼打盹。老黑就过来,蹭他,拱他。一副急着想下山的样子。
和信知道,是村子里的母狗缠磨得老黑难受。
老黑又在羊群边上跑起来了。它一跑起来,羊群就不动了。它跑下一个台地不见了。老黑回来了。它仰着头,不慌不忙地慢慢往回溜跑,那架势像个得胜的将军,一脸骄傲。
它嘴里衔着一只野兔子。到跟前了,老黑就绕着他撒欢,直到跑停了,才撒嘴,把野兔子交给他。
野兔子在他的手里沉甸甸的。羊群还在他的身上经过。
它们才不管他手里是否掂着一只野兔子。它们不关心野兔子的命运,羊群只关心眼前的青草,和酸枣棵、荆条子的叶子,是否有足够鲜嫩。
他想等着羊群过完,再收拾手中的野兔子。可这羊群像是总也过不完。黑乎乎的羊群从他的身上经过,像是把夜色也带到了他的心里。可能就是天黑了吧。他这样想着。突然他听到一阵公鸡打鸣声。
那声音兴奋,亢亮。
他醒来了。找到这声音的来源。那是一部老年手机。他摁下一个键,那声音消失了。他知道,该下到村子里去吃晌午饭了。
老羊倌和信还能吃下一大碗拽面条。就着这碗面条,吃下一头蒜。他有一口好牙。孙子媳妇又给他盛上一碗面汤。这一顿饭吃下去,他的脸上又浮起一层油光。他摸出一根烟卷,点上,向门外走去。他那高大的身影刚出门,就很响地咳嗽了一声。呸!他吐出一口浓痰。
和信来到小卖店外的石桥上。这里已经聚集起几个吃罢午饭的老人。“桥长”乱子还没来。乱子是和信本家的侄子。前年刚从一家国有煤矿退休。在那家煤矿,乱子干过一个单位的小头头。退休回家,混进桥上的老人堆里,没几天就得到一个“桥长”的绰号。他个子不高,但说起话来却嗓门洪亮,蛮横霸道,又狠吃吃的,像跟人有仇一样。
老羊倌来到桥上,一般不说话。他靠住一根桥柱,就眯上眼晒睡。
乱子一来,桥上就热闹起来。乱子能没边没沿地瞎吹。
和信在想,村里的老人什么时候把这座石桥当成晒晌时的“会场”了呢?是九成家开起小卖店后?像是还早点。
他想不起是在哪一天开始的了。
起初没几个人,慢慢就多了。人一多,老羊倌就觉得像有几百人,桥面上都是热烘烘的人影。这些人,影影绰绰地来往,擦肩过去,又擦肩回来,不停地在他眼前晃动。
和信也不睁眼,像看电影似的感觉这些人带着他所熟悉的样子晃动。
乱子说话高一声低一声的,没个正影。他扯开话头,说起村子里当年的老地主李有顺和李家院子。
和信也在心里管李有顺叫老地主。他伺候过老地主。那时,和信喊他“老爷”。
和信在山上的石屋中不止一次看过在北坡上的老地主的家院。那是占据了一面缓坡的一个巨大家院,大院套着小院,进进出出有无数的门,和信跟着爹走在里面,像是走进迷宫内。和信最喜欢在高处看过年时的李家院子。院子的门上、廊道内,挂着一对对的红灯笼。夜间,蜡烛点着了,一片灯笼红的院子,就像传说中天上的宫殿。要是下过雪,院子里红的红、白的白,就更好看了。
在艾村,北坡那一片一直被叫做李家院子。
李家院子在解放前被一场大火烧成半个院子。那是艾村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火。那晚,刮着北风。火从中院烧起。火烧起后,就没停下来,它的大舌头一口气就把南院舔光了。
李家院子被烧掉半个后,老地主李有顺就把家里人遣散了。他像是在那焦糊味中嗅到了危险。家里只剩下老地主与和信,两个伺候他们洗衣吃饭的婆子。那时,和信还只是个小羊倌。遣散人后,李家没了羊群。
遣散人时,李有顺对和信的爹说,你也走吧。跟着大少爷走。
和信爹说,二弟要跟着大少爷走,我就不走了。
他必须得走。大少爷离不开他。李有顺说。稍停,他又说,你不走……也是,你还有一家子人呢。
和信爹说,还不都是老爷的人。
李有顺说,那你不跟大少爷走,就自己去过吧。
和信爹说,我听老爷的。
李有顺就说,在河滩上给你一亩水地,行吧。
和信爹说,行。
李有顺又说,在南山坡下再给你五亩旱地。行吧。
和信爹说,行,老爷。
李有顺继续说,把山上放羊的石屋也给你,行吧。
和信爹说,行,老爷。
李有顺像是说累了,就停下话头。他嘬过一口烟,在鞋底子上磕烟袋里的灰。这时,和信爹就走过去,接住烟袋,又给他装满烟锅,摁瓷实了,再递过去,点上。
李有顺深吸一口烟说,村东那四间老房子也给你吧。
和信爹说,我们一家子人,谢谢老爷了。
李有顺隔着烟,看一眼跪在地上的和信爹说,起来吧。接着他又说,让和信留下,早晚服侍我,行吧?
和信爹答应了。
这事没过半年,村子就解放了。又过去两年,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老地主李有顺被拉上一辆车,押到谢台镇批斗。批斗完,李有顺就和另外七个人,被车拉到河滩上枪毙了。和信记得那是发生在五月间的事。河滩地里的麦子刚泛黄。在观兵台下的一个土岗子边,那八个人被一阵排枪的响声放倒了。
老地主被枪毙了。李家剩下的半个院子就拆掉围墙分给了村里的穷人。和信被从李家院子撵出来,回了家。
这时的和信已经是个十六七岁的愣头小伙子。他人长得瘦高,两条腿细长。
村集体要养羊,就找和信爹。说是借他家在半山腰上的石屋做羊圈,还要请他出山,给村集体放羊。和信爹没答应。他不是没答应这个事,而是没答应自己再到山里放羊。和信知道了这事,就跟爹说,他想去放羊。听了和信的话,爹闭着眼半天没说话。等爹睁开眼时,和信看见爹的眼里都是泪水。
和信说,爹,我喜欢跟羊群待在一起。我去放羊,还能保住石屋。
爹擦擦眼,点头答应了。
乱子还在那里东一句、西一句地瞎吹,似乎李家的事,他都知道。像是他就生在李家,长在李家。老羊倌一想,这狗日的还真是在李家院子长大的。解放后,乱子的爷爷分到李家三间房。之前,他们一家住在河边的两间草屋里。那时,乱子的奶奶刚病死,乱子还在他娘的怀里吃奶。
乱子的嗓门一声高过一声。和信不想搭理他。他狗日的,知道个屁。老羊倌在心里骂道。
乱子说,你们知道不,那老地主尿尿的夜壶,都是景德镇的精瓷。
这狗日的,真是放屁不怕砸脚后跟啊。和信想。
乱子又说,老地主用的那把夜壶,据说是他爷爷的爷爷用过的。乱子停下话头,扭过脸来,探头看着老羊倌和信说,是吧,和信叔。我叔爷给我这样讲的。
和信闭着眼晒太阳,没应他的话。他不想当众戳穿乱子的谎言。何况他还搬出了爹。但他清楚,乱子又在他娘的说屁话。这狗日的!他在心里又骂一句。那老地主的夜壶,就是本地烧的一种粗瓷。他还不小心打碎过两个呢。
和信没说话。这在乱子看来就是默许,就更口无遮拦地胡说了。
人遣散后,老地主的家空了。和信知道,那是被十几辆大马车拉空的。门厅内的八仙桌上,就只剩下一套白底红花的茶具。原来在八仙桌上挂着的中堂画,墙上的紫檀挂屏、字画、条几上的青铜器和花瓶,都不见了。有一阵子,和信天天陪着老地主走进一间间空屋子里,再从一间间空屋子内走出来。一天下来,进进出出的没遍没数。老地主不在院子内进出,就去河边,看那一大片整齐的河滩地。站在地边,老地主能一句话不说,倒背着手站立一个上午。
老地主来了心情,就教和信识字、写字。在一块石板上,他用手指蘸着水,耐心地教和信读写。那时,和信觉得一笔一画写字的老地主,和平时比起来,像是换了一个人。
每到半晌,老地主就坐在门厅内的八仙桌边喝茶。
起初,还有人从外边回来看看。等战事紧张起来,连书信也少了。有天晚上,家里来了人。和信在下屋悄悄听来人说话。那人在劝老地主走。说这会儿走,还来得及。但老地主没答应。那人就连夜走了。
老地主桌上那套喝水的茶具,从不让和信沾手。他自己都是小心翼翼地拿放,好像这茶具有多珍贵。但在和信看来,不过是一把精致小巧的茶壶,和两盏更精致的雕花盖碗。
和信听爹说,东家不仅在谢台一带有着上千亩的地,还在北京、天津有买卖,像是南方也有。这家里,原来摆放最多的就是瓷器。那些瓷器,全是景德镇等名窑的物件。听东家说,还有更珍贵的钧瓷,只是他没见过。爹说,你二叔见过。二叔从小就伺候大少爷。老爷有一间库房,收藏的全是磁州窑的制品。爹还说,老东家活着时,比小东家还喜爱瓷器。他偏爱收藏磁州窑的物件。东家遣散家人时,这些瓷器就都不见了。
和信爹还说,老东家死时,停灵七天。发丧时,出殡的队伍从村口排到坟地。这事,和信也听村里人说过。但那都像是瞎传。可传说就跟真的一样。人们说李有顺他爹的棺材里,装满半匣子各式各样的瓷器。就是墓穴中,也埋下不少。出殡那天,埋进祖坟的是假棺。老东家的真棺,早就偷偷下葬。谁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后来有消息泄露出来,也是猜的,说那老东家可能埋在河湾内的西坡一带。
但和信觉得,这事爹应该知道。村里人也都这样想。和信问过爹,爹回答得干脆,不知道。他问多了,爹就会说,我一个羊倌,能知道这事?
有一年,谢台镇来了一个港商,说是要在谢台考察投资。他在镇上住了一个星期,不仅走遍谢台的老街,还跑到艾村去看古磁州窑的遗址,还专门打听过李家院子的事情。末了,又到和信住的半山腰上,看过石屋。有一天,这人来到漳河边,默默坐了一个下午,直到天黑。
后来这港商走了,一去便无消息。再后来,有人说这港商就是李家后人。
和信问过爹,当初为啥不跟大少爷走。爹说,他拖家带口的,不方便。那时,爹真想走。爹没走成,就让二叔跟着走了。这一走便无音信。爹临闭眼前,还后悔,不该让二叔走。
乱子还在瞎吹。听我叔爷讲,老地主的爹出殡时,棺材到了坟地,家里还有人没走出院门。人太多了。那排场,讲究得跟皇上似的。
和信咳嗽了一声。
乱子说话的声音低下来一点。但还在瞎吹。村里有人传,说那天,老地主的爹,根本就没在那口棺材里。他早被偷偷埋了。陪葬的宝物太多,怕人掘墓偷盗。我叔爷活着时,我问过这事。叔爷告诉我,这是真的,他亲眼见过。
和信又在心里骂着乱子。这狗日的,真敢瞎说。
乱子越说越玄。他说话时,别人根本就插不上话。他还真当自己是“桥长”了。
老羊倌和信觉得自己太阳晒够了,心情疏散够了,也听烦了,就站起身,谁也不打招呼,起身离去。
他又回半山腰上的石屋去了。
这几年,村子向外扩张了不少。原先,在村子里看,那石屋蛮远的。这会儿,穿出主街,再转过一道小街,出村,就走到石屋所在山坡底下。村子在变大,人却越来越少。这山里的村子,已经养不住年轻人。他们的心,都被外边的世界勾走了。
但也有例外。和信的孙子少朴,在外面折腾几年后,却回来了。
少朴回来,闷头接过爹的羊群,当起羊倌。老羊倌和信搞不懂,少朴心里是咋想的。一说起这事,他那儿子就摇头叹气,像是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少朴养羊,和老辈人不一样。他回村没多久,就建起“艾山黑羊”网站。并联络周边村子的养羊户,搞起联合养殖销售合作社。几年下来,这艾山黑羊的名声就在南方市场上打响,愈来愈火爆。少朴进山放羊,也是手里拄着一根对节棍,背着大号水杯,挎着装有食品和杂物的背篼。但他的背篼里,还多出一样东西,那就是一台和手机连在一起的平板电脑。这台电脑,让他和外边的世界神秘地发生着联系。对于这些,老羊倌一无所知。在和信看来,少朴的心中装着一个他无法懂得的秘密世界。
少朴却从未冷落过爷爷。他一有空闲,就守在石屋中,不停地问老羊倌和信过去放羊的经历。他喜欢爷爷像故事一样的人生。他还把一些细节问得不厌其烦。和信随口讲给他的各种牧草,少朴也听得用心,记得仔细。没过多久,他竟弄出一个艾山黑羊的食谱,收录各种植物一百多种,并详细列出它们的生长季节、药理属性、营养价值。等少朴再把这些讲给老羊倌时,他就想,少朴心中不仅装着一个他弄不懂的秘密世界,这孩子还在神奇地创造着一个世界。
太阳又落到艾山后边去了。远处的漳河水,在暮色中泛起一层柔柔的暗亮。五六只黑喜鹊惶惶归来,它们掉队了。刚过河岸,这几只黑喜鹊就一头扎进村边的柳树林中,不见影迹。远处的河水,像是在轻轻抬高着点什么,慢慢地经过村子。它隐身进一片树林中,又闪出来。这时,它已折弯,向北流去。
艾山后,只有一片青黛的暝色了。天在黑下来。
和信不记得他已看过多少这样的日落日出。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看多少次。他想不会很多了。他老了,艾山却没有变,流过村子的漳河水,也没有变。
出山的沟道上,走出最后一群山羊。它们被一座小丘遮住,又转出来,出现在村道上。它们在一点点地向半山腰的石屋接近。牧狗大黄早已蹿到老羊倌身边,在蹭着他的身子绕转,嘴里发出低低的吠声。和信看到跟在羊群后边身材高大的少朴。他越长越像一个人。有一天,和信对儿子讲,你没觉得少朴越长越像你爷。儿子沉吟半天,像是在记忆中走回很远,又走出来一样说,爹,你这么一说,我再看少朴,还真像俺爷。
也许,那些在家族记忆中渐渐走远的人,就是这样在后人身上顽强地复活着。
老羊倌和信又到石桥上晒晌来了。今天,他比以往晚到了会儿。“桥长”乱子还在海喷。桥头那边停着一辆摩托车。有个年轻人趴在摩托车上,眯着眼像入神一般在听乱子胡侃。他偶尔会摆弄一下手机。和信想,这个人他见过。有几次,他来晒晌时,这个人都在,也不言语,就趴在车身上听大家说话。
和信没多想,找到一根桥柱,他靠身坐下,眯起了眼。太阳真好,暖劲也足。
这桥上不断有陌生人出现。他们都是来听这些迟暮的老人说古。就像早些年没电视的时候,和信在半山坡上的石屋内,天天夜晚都聚满了人。起初,都是本村的人。慢慢地就有外村人来。他们到石屋来,就是为了找一个说话和听人说话的地方,来消磨那一个又一个漫长无尽的黑夜。这些人,面影模糊,围着一盏集体的电石灯,成夜成夜地说话。那时,和信还不算老,爹也活着。那些夜晚,像河水一样不知疲倦地流淌着,流过艾山和艾山脚下的村子。它焕生的烟火人间气味,粘稠、腥膻又无比馥郁,无边地腐蚀着山里人的心性。
那些日子怎么就突然中断了呢?
不知何时起,到石屋来的人,越来越少。慢慢地就再没人来了。世道在变。人也在变。这不变的石屋,就寂寞了。
桥上有人说,最近村子边,还有山里,经常出现走动的陌生人。
乱子抢过话头说,你才知道啊。我早听人说了,这些人都是来山里寻宝的。河湾西坡那边,天天来生人,一波波地没断过。
和信仍闭着眼。但他在听。这人都免不了被财气迷住心窍。他想。
河湾西坡那里有什么?有一个被传说炒热、炒得离奇的财富秘密。当年,刚兴办煤窑时,村长大兴就跑到西坡去打煤窑。之前,他见天往自己家跑,不是找爹,就是找他。爹和他都知道,这狗日的大兴哪有闲心来听他们说话。他有目的,是想来套话,打听李家祖上的秘密。他以为爹知道真相。在艾村,谁都知道西坡没煤。大兴却扬言,他找过大矿的工程师,人家说那里有煤。他就去那里打井了。谁都知道,他是去挖李家的神秘宝藏。他把西坡翻遍了,啥也没找到。
这会儿,西坡又有人来了。
和信晒足太阳,就回山上的石屋去了。
石屋外边有人。和信不认识的人。他的石屋从来都不关门,多少年了,这座石屋连门锁都没有。这人在石屋前来回踱步。和信想,他已经进过石屋了。
和信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那人转过脸来,并不惊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眼狭长,有点肿眼泡。
那人说,这是您老的屋子?
和信说,我爹就在这里给东家看羊。
那人说,这石屋还有年头了?
和信说,我爷爷也在这里给东家看羊。
那人递过来一支烟,和信不客气地接住。那人啪的一下,打着火机。和信把脸凑过去,点燃。那人也给自己点上一支。
那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和信听,这石屋造得好,地方也选得好,更是借得巧。他自己说漏了。他确实进过屋子里了。和信没回他的话,只是把目光投向了石屋。他也觉得这石屋造得好。他住了几十年,第一次觉得这石屋造得好。真是好。
一支烟抽完,那人走了。
和信慢慢走进石屋。屋内靠墙摆着一只淘汰的旧沙发,陈旧的已看不清皮色,像是许久没人坐过。沙发前有一个玻璃茶几,浅浅地蒙着一层灰尘。上边摆放着一个填满一半烟头的玻璃瓶子。靠里有一张木桌,上边放着一只竹皮暖瓶,还有一把电热壶。暖瓶边,有一个大号塑料水杯。和信在屋子内默默地站立着。他闻到一股陌生人的幽谧气息。
他深吸一口气,来到南屋。他没进套间。在小窗前,静静地向外伫望。墙角边,立着几只废弃不用的羊鞭,两根油光锃亮的对节棍。窗外,午后阳光下的事物,都还很亮,亮得有点假,让人眩晕。山坡下的村子,虚虚缈缈浮在游移的光影中。狭窄的小街,像穿行在暗影中的蛇。
和信觉得心里一阵晃动。就在这晃动中,村子消失了。
他的眼前一片昏暗。像是他又陷入到那个一直跑着黑色羊群的梦中。
有一天,和信记得是刚吃完晌午饭。按习惯,老地主吸过一袋烟后,就要去午睡。那天,老地主没去睡,他要喝午茶。老地主以前从不喝午茶。和信有点奇怪。但又不敢问。他就下去拎来水壶烧水。那天,和信发现八仙桌上多出一个精致的木匣。老地主在屋内喝茶。和信坐在屋外的石阶上,看院子内的石榴树。石榴树开满一树像血一样鲜红的花。稠密的花朵,引来不少野蜂、蜜蜂,还有一种长着大翅膀的蛾子。那蛾子嘴上长着长长的吸管。它飞到一朵花前,并不降落,而是在悬停中把吸管探进花腔内,一伸一缩地吸食花蜜。
和信被这蛾子吸引住了。就慢慢凑过去,想看得更真切些。
他忽然听见老地主在喊他。
他就扔下蛾子赶紧跑进屋去。
老地主闭眼躺在圈椅中,像是很累、很困。他不说话。和信就一直静静地在他面前站着。他看一眼桌面,老地主喝茶的茶具不见了。他再看,就发现那个木匣子,被一块灰布方巾包了起来。
老地主还没睁眼,但说话了。小信子,你去把这个盒子藏好。
和信一愣说,老爷,藏哪儿啊?
老地主说,藏哪儿都行,就是别藏在这个家里,也别让你爹知道。
和信傻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从未办过这样的事。
老地主轻轻用手敲一下桌子,说,还不赶紧去。
和信抱着那个裹在方巾内的小木匣,回到自己屋内。
第二天,老地主再喝茶时,就换成平时吃饭用的一只小号粗瓷碗。老地主用碗喝茶,不像和信是用手掌端着碗喝,而是用三根手指头捏着碗沿凑到嘴边,小口小口地啜饮。老地主也没问和信,把那套茶具藏哪儿去了,像是知道他天生就会把它藏好。
第三天傍晚,有一群人闯进家来,把老地主带走了。
有陌生人来石屋了。老羊倌和信想,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呢?难道这石屋内还有秘密。他在这石屋中住了几十年。他闭上眼都知道石屋内的每一道墙缝是什么样的。就是在墙缝里的蛐蛐,他都能听出来那叫声中的喜怒悲乐。
那一年,要在谢台投资的港商也来过石屋。他也说过类似陌生人的话。和信像是回答那个陌生人一样,答过他的话。
等他走了,和信才听人说,这个港商可能是李家后人。
让老羊倌眩晕的光亮不见了。屋外的光线慢慢暗下来。他听见羊群走近的蹄音。少朴进山放羊回来了。
老羊倌和信仍站在窗前一动未动。
少朴圈好羊,走进石屋。他来到爷爷身边,默默站住。大黄兴奋地在屋里屋外蹿进蹿出。
和信说,有人来石屋了。
少朴说,这些天,我在山里一直碰到陌生人。
和信说,人是一种日怪东西。
少朴没答话,暗暗地笑了。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少朴说,爷爷,该下山吃饭了。
老羊倌和信已经三天没到石桥上来晒晌了。有人就问“桥长”乱子。乱子说,我听少朴说,他爷爷崴着脚了,这两天吃饭都得人往上送。
老羊倌和信真的是崴了脚。但并不严重。
不能下山了,上午他就靠着石屋的门框晒太阳。中午,他就会挪步走到石屋对面,靠着一截土坡晒晌。初夏的太阳足够暖,又不伤人。真是好时光。他眯住眼,一个光亮的世界,就暗了下来。眼前暗了,像羊群一样的事物就在他的记忆中跑起来。它们似乎从未停止过跑动。
山那边的女人就像这阳光一样,又暖又好。
一天,山那边的女人说,她要嫁人了,想要和信给她样东西,做念想。那时和信还是生产队的羊倌,穷得只有自己那让女人喜欢的身体。但他答应了女人的要求。再见面时,他手里拎着一个小包。包皮就是那条灰布方巾。方巾内,是一条素色绸巾,绸巾内包着一把茶壶、两盏盖碗。女人看了,欢喜得不行。女人欢喜过后,就哭了。
女人并没有远嫁。只是从山那边的一个村子嫁到了另一个村子。和信仍在山这边放着集体的羊群。羊群进山了,和信会突然在一条羊道上遇到山那边的女人。她等在那里。女人还像以前一样,又暖又好。
又过去几年,和信还在山里放羊。有一天,和信再见到女人时,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女人说这孩子是他的。她送还给他。她说,有了这个孩子,也算两人不白好一场。那一年,到处都在闹饥荒,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之后,女人再也没出现过。
和信的梦中,黑色的羊群滚过之后,就亮了起来。梦一亮,女人就来了。和信喜欢那个来到梦中又暖又亮的女人。
和信觉得自己沉在梦中的时间越来越长,长到他不愿再从梦中醒来。
这一天,他喊来孙子少朴。他躺在石屋内那张宽大的床上。少朴坐在床边。他让少朴打开床边的立柜。在一件旧棉袄中,少朴找到一个木匣。一只上好的紫檀木匣。那个匣子,在少朴手里像是只有自身的重量。
少朴问,里面装的是啥?
里面啥也没有。老羊倌像是没有力气回答少朴的话。
少朴又问,外边传说祖爷的事,是不是真的?
和信反问道,你听的都是传说,传说有真的吗?
少朴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又问,匣子里的东西呢?
和信说了山那边的女人的事。他说得很慢,像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但他在中途突然沉默不说了。他沉默了,也像是故事就讲完了。过去许久,和信说,扶我出去晒晒太阳吧。
少朴把他搀到门前的石墩上。他在铺展开的老羊皮袄上慢慢扭动身子,终于坐得舒服了。坐舒服了,他就靠住墙,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他刚闭上眼睛,羊群就跑了起来。黑色的羊群,一群接着一群,从他的身体内向外奔跑。他担心羊群这样不停地跑起来,会把他整个人跑空。他不知道羊群把他跑空之后,自己还会剩下什么。人老了,还能剩下什么呢?
羊群终于跑完了。羊群跑完了,也把老羊倌和信的心跑空了。
和信跑空的心,豁亮起来。那明亮中,弥漫着光线和温暖。那是很轻很轻的光线和温暖。
又过去两年。少朴已经不放羊了。他做起乡村特色旅游。
他承包了村子南边的荒坡和梯地,都种上了树。那树都是经过规划后的景观。是一片片的杏园、桃园、梨园。石屋下的丘地上,一梯一梯种满艾山野菊。他又在石屋周围的山坡种上一片黄栌。秋天到来时,野菊开出一片金黄,黄栌的叶子火红如炬。远远看去,秋阳中的一切,像是在燃烧。而在这金色与红色映衬中的石屋,像是也在沉静着燃烧。
这时,山腰上的石屋,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艾山羊倌纪念馆。纪念馆进门正墙上,有一张老羊倌和信的照片,它混在众多的照片中。照片全是黑白照,有种被渲染的做旧效果。照片上,老羊倌和信坐在屋前的石墩上,眯着眼,静静地看着村子方向……
左马右各:本名骆同彦,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职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阳光》杂志签约作家。在《收获》《当代》《十月》等报刊杂志发表过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随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