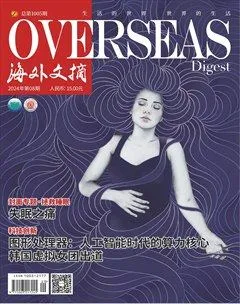梅利利亚血案
梅利利亚,这座地中海边缘的飞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成为了由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印度教徒组成的“四重文化”之城。一场血案的发生,使这座城市隐藏已久的多元文化冲突浮出水面……

| 冲突爆发 |
2022年6月24日,1700多名非法移民(大多来自苏丹和南苏丹)沿着摩洛哥东北部的古鲁古山脉向梅利利亚方向跋涉。梅利利亚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是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面积为12.3平方公里,人口约8.5万。移民一路前行得十分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有些不同寻常,毕竟此前几个月里,摩洛哥警方曾多次突袭藏匿在深山中的移民。不仅如此,政府还禁止当地商店向移民出售食物,并拦截搭载移民的出租车,以防他们前往附近纳祖尔市的西班牙领事馆。
移民们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由于害怕被捕,他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但又无法通过官方渠道申请庇护。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非法越境。摩洛哥和西班牙当局以及当地人拍摄的视频显示,6月24日早上8点,大批移民抵达摩洛哥和梅利利亚边境一处自疫情以来就处于封闭状态的废弃口岸,开始翻越隔离墙。数百人争先恐后地翻过围墙顶部的铁丝网,闯入摩洛哥一侧检查站的空地。在他们对面,一扇紧闭的大门隐约可见。门后便是西班牙的领土。
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摩洛哥警方在检查站周围拉起警戒线,朝移民投掷石块、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移民们用电锯强行锯开封闭的大门。催泪瓦斯让他们呼吸困难、视力模糊,但他们没有退路,只能拼命向前冲。
来自苏丹的24岁青年巴希尔目睹了这一切。此前,他已在古鲁古山脉的帐篷里躲了数月。6月24日清晨,他和其他移民一起翻过摩洛哥边境的围墙,挤过大门,越过5.5米高的铁栅栏,成功踏上了西班牙的领土。历尽千辛万苦后,他走上了一条主干道,两边长满了橄榄树和仙人掌。站在这里,梅利利亚的轮廓清晰可见:摩天大楼、教堂的尖顶和宽阔的港口。
可惜,巴希尔没有时间欣赏这一切。没过几分钟,他就被西班牙国家宪兵队逮捕,并强行遣送回摩洛哥检查站。在被推搡回去的路上,巴希尔看到边境围栏上零星挂着一些移民的尸体,像耷拉在晾衣绳上的旧衣服。其余人仍挤在那块空地上,密密麻麻、摩肩接踵——别说转身,他们甚至连肩膀都无法扭动。不少人在呻吟,一些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警方铐住巴希尔的双手,强迫他和其他几百名移民一起趴在边境墙下。整整八个小时,他们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即便在阴凉处,气温也有27摄氏度。视频显示,摩洛哥警方全副武装,多次用警棍殴打趴在地上的移民。巴希尔口干舌燥、嘴唇开裂,但他不敢挪动也不敢出声,其他人也一样,巴希尔不确定那些人是不是为了逃脱警方的毒打故意装死。

因为摔伤和殴打,一些移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折和脑震荡,迫切需要治疗,可现场的医护人员只负责运送尸体和救治受伤的警察。之后,大巴车抵达现场,移民们被押送上车,分别运往摩洛哥几个边远城市。九个月后,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一家旅舍的小房间里,巴希尔向我讲述了那天的悲惨遭遇。尽管房间里的冷气很足,但他还是不停地冒汗,“他们根本没拿我们当人。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畜生。”
根据官方数据,当天约有1700名移民试图越境,其中133人成功申请到了庇护;470人和巴希尔一样,在进入西班牙领土后被强行遣返回摩洛哥;至少37人死亡,77人下落不明。此次事件被称为“梅利利亚血案”。
西班牙选择淡化这一惨剧。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赞扬了警方在冲突中的表现,称6月24日的大规模越境未遂事件是“对西班牙领土的袭击”。摩洛哥起诉了65名参与越境的移民,其中33人以破坏公共财产、袭击摩洛哥警方的罪名被判处11个月监禁,剩余32人被控贩卖人口罪。另一方面,摩洛哥警方被指责试图掩盖其暴力行径。摩洛哥人权协会称,流血事件发生两天后,有人看到摩洛哥边防官员在边境附近挖了大约20个坟坑。
|“四重文化”之城 |
2023年早些时候,我从马德里飞往梅利利亚,想实地考察政府对梅利利亚血案的处理情况。从机窗向下望去,这块西班牙飞地大约是直布罗陀市面积的两倍,仿佛一块缝在非洲大陆边缘的怪异补丁。降落过程中,我收到短信,通知需要收取漫游费,就好像此地不属于欧盟一样。下了飞机,干燥的热气扑面而来。
我在机场附近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款上世纪80年代的银色奔驰,布满灰尘、破旧不堪。十分钟后,我抵达市中心,映入眼帘的是熠熠生辉的大理石街道、艺术长廊,修剪整齐的棕榈树、灌木,以及出自加泰罗尼亚建筑师恩里克·涅托之手的现代主义建筑——这些建筑放在巴塞罗那也毫不违和。15世纪保留下来的堡垒紧贴着海岸的峭壁。碧绿的地中海上,渡轮和货船穿梭不息,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
对居住在欧洲大陆的西班牙人来说,梅利利亚既熟悉又陌生。这里的居民说话带有北非和安达卢西亚口音,穆斯林名字和西班牙名字经常被混搭使用。虽然西班牙语是官方语言,也是使用最多的语言,但阿拉伯语、柏柏尔语和塔马齐格特语也极为普遍。在这里,薄荷茶和啤酒一样流行,羊肉和猪肉同样常见;天主教教堂、清真寺和偶尔出现的犹太会堂共同点缀着这座城市。梅利利亚近半数人口信奉天主教,另一半人口是穆斯林,另有1000多名犹太人和100多名印度教教徒。
虽然摩洛哥对梅利利亚文化的影响非同一般,但该市居民还是更认同自己的西班牙身份。梅利利亚议会副议长杜尼娅·翁彼雷斯称,每当欧洲大陆的西班牙人因为某些梅利利亚居民的穆斯林名字而错将他们当作摩洛哥人时,他们都会感到异常沮丧。在这些人看来,自己作为西班牙穆斯林生活在梅利利亚的事实不应当需要额外解释。他们为此曾提出过强烈抗议。
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盟前,曾制定了关于如何获得西班牙国籍以及如何在西班牙生活和工作的全新法律。新法规为与西班牙历史和文化相关的特定群体(如拉丁美洲人)提供了诸多便利,却将同样来自其殖民地的摩洛哥人和西撒哈拉人拒之门外。结果,约1.4万名出生或生活在西班牙领土上的梅利利亚穆斯林,突然之间竟成了名副其实的“外国人”。他们为此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翻看当地旧报纸,就能看到警察持枪对着在城市主广场抗议的穆斯林妇女的照片。最终,长期居民获得了永久居留卡和西班牙国籍。从那时起,梅利利亚开始拥抱自己的多元化特征,成为由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印度教徒组成的“四重文化”之城。
| 移民问题 |
除梅利利亚外,西班牙在非洲大陆还有一块领土:休达。休达位于摩洛哥最北端,与直布罗陀隔海相望。两座城市对试图逃离贫困和饥饿的移民都极具吸引力:与其冒险乘小船穿越整个地中海偷渡欧洲,不如翻过围栏直接抵达。正因如此,在很多人看来,这两块飞地俨然成了“欧洲堡垒”的前哨阵地,其主要功能就是阻挡寻求庇护的移民。
的确,梅利利亚的前哨地位对任何游客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梅利利亚的公职人员比例乃全西班牙最高,接近50%。几乎每条街道都能看到警方和国家宪兵队的车辆。梅利利亚的边防人员多达1200名,此外还有约3000名士兵驻扎在这里。
移民事务更是渗透到梅利利亚生活的方方面面。红十字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以及各种小型非政府组织均在此处设有办事处。一位律师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他经常在夜晚开车去边境,停在那里等待过境者。“白天律师工作很忙,所以我经常凌晨三四点开车去边境,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移民。”他会在夜色中等待,见到移民就尽力帮扶,陪他们去警局办理手续。那时,城外的移民接待中心还没有建成。
抵达梅利利亚的第二天下午,我拜访了移民临时停留中心。此处距离市中心约三公里,是新移民的临时居住地。与我同行的赫苏斯·布拉斯科是一名当地记者兼摄影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报道移民和梅利利亚边境问题。移民临时停留中心背靠少年监狱和高尔夫球场。来自苏丹的巴希尔原本希望在这里申请庇护。

该中心可容纳480人,但我去的时候只看到三个移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西班牙当局希望在处理移民申请时将他们留在梅利利亚。寻求庇护者的临时身份证上清晰地写明“仅梅利利亚有效”,即他们不能去西班牙本土工作或旅行,因此临时停留中心总是人满为患。2015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称,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标准。该组织的西班牙代表指出,“移民绝不应该在中心停留超过三天。”
2020年,马德里最高法院裁定,梅利利亚的移民只需持护照和庇护申请即可在西班牙境内自由通行。此后,大多数移民离开了临时停留中心。从那时起,除疫情暴发后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那段时间,临时停留中心一直没什么人,长期滞留在梅利利亚的移民大幅减少。与此同时,梅利利亚的常住居民也在努力淡忘移民问题。
在布拉斯科看来,将移民临时停留中心建在城市边缘,就很能反映梅利利亚人的心态。“大家希望能将移民事务从日常生活中彻底抹去。”在梅利利亚,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室、警局和军事基地随处可见,但这里也有一个由企业员工、教师和市政公务员组成的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生活同欧洲大陆的西班牙居民并无二致。没人愿意在咖啡馆和酒吧讨论移民问题。一位当地居民曾略显疲惫地向我抱怨:“媒体只知道不停地念叨‘边境墙、边境墙、边境墙’,除此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梅利利亚的普通居民也有自己的生活,谁也不想日复一日地背负着边境上演的移民悲剧。
| 西班牙的对策 |
自1497年西班牙人从柏柏尔人手中夺取梅利利亚以来,该地成为西班牙领土已有500多年。19世纪,西班牙与摩洛哥签订条约,正式划定了梅利利亚的边界。现在,西班牙政府将梅利利亚和休达定义为“自治市”。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一直试图收回这两座城市的主权,但遭到了西班牙的强硬拒绝。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允许梅利利亚和邻近纳祖尔市的摩洛哥居民跨境自由流动。许多摩洛哥人开始在梅利利亚工作,大多从事建筑业和跨境贸易,每天通勤于两地之间。
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盟,随后于1992年加入申根区。自此,西班牙开始受到来自布鲁塞尔的压力,被要求减少从欧盟以外地区进入西班牙的移民。为解决这个问题,西班牙在1996年建造了一座高3米、长11公里的双层围栏,并于当年年底投入使用。
不过,由于梅利利亚连绵起伏的山脉和陡峭的悬崖,沿着边界线修建围墙并不现实。当局只能在接近摩洛哥边界的地段修建围栏,导致一些梅利利亚居民一夜之间被隔离在祖国之外,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别墅原本属于梅利利亚,可在新围墙建成后,却被划到了摩洛哥那边。
20世纪初,埃尔南德斯搬到了梅利利亚市中心,如今依然在此居住。他已经70多岁了,满头银发,留着长长的胡子,看起来有些消瘦。他拿出一堆剪报和文件,都是关于当年别墅离奇事件的报道。“当地警长那天来找我。”埃尔南德斯回忆道,“他说:‘欢迎来到摩洛哥,我们随时为您效劳。’”最后,当局不得不在埃尔南德斯的住所与边境之间修建了一条一米宽的通道,方便他从最近的过境点进入西班牙。每次回家,他都必须向警卫出示证件并解释一番。
从非洲入境梅利利亚的移民不断增加,西班牙的边境墙也越修越高。2005年,当局将围栏高度增至六米,2014年又安装了防攀爬护栏,并在部分区域加装了铁丝网。2020年,为了展示人道主义姿态,桑切斯政府宣布拆除铁丝网,却将部分边境墙增固至九米。同年,疫情暴发,梅利利亚禁止纳祖尔市的摩洛哥人自由进出。现在,所有摩洛哥人须持西班牙签证才能入境。
| 前路漫漫 |
抵达梅利利亚的第三天,我同当地记者哈维尔·加西亚一起去了血案现场。加西亚是这场悲剧的目击者之一。那天,他从同事那里听到移民大举越境的消息,不到十点便赶到了边境。他看到数百名移民已经踏上西班牙领土,集中在围墙旁的小路上,被西班牙国家宪兵队和警方包围。一群妇女正在清扫冲突后的现场。他还看到摩洛哥警方与西班牙宪兵队一起抓捕移民。根据视频和目击者的证词,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检查站后遭到关押,并被送往尽可能远离边境的地方。
2014至2020年间,欧盟以规范移民流动为由,向摩洛哥政府支付3.46亿欧元,并计划于2027年之前再支付5亿欧元。欧盟与其他北非国家也有类似协议。欧盟的逻辑非常简单:只要能将移民留在非洲,他们就不会成为困扰西班牙和欧盟的道德问题。
这些政策引发的恶果显而易见,巴希尔对此深有体会。15岁时,他亲眼看到父亲和哥哥死于部落冲突,于是萌生了逃到梅利利亚的念头。他逃离了原本居住的村庄,投奔到苏丹森纳尔州的叔叔家,不料又要面对改宗的压力。他忍了整整五年,才攒够钱去欧洲。他辗转到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中途四次被拘留,一次甚至被阿尔及利亚当局丢在沙漠里等死。一路上,他曾多次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求助,但工作人员的态度都极为冷漠。
梅利利亚血案发生后,巴希尔和其他苏丹移民被大巴运往摩洛哥中部城市贝尼迈拉勒,距离边境有八个半小时的车程。医院拒绝为巴希尔治疗,工作人员甚至对他大肆辱骂。他不得不从摩洛哥中部跑到西海岸,在不同城市之间辗转,靠着陌生人的善意解决温饱。不少移民同伴表示会再次冒险越境,但巴希尔倾向于走合法渠道。他联系了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在他们的援助下接触到一家马德里的律师团队,这些律师表示会帮助他向西班牙驻拉巴特大使馆申请庇护。
接受采访时,巴希尔已经等待数月,却没有等来任何回音。为了躲避警方搜捕,他四处漂泊,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定。他说,眼前总是不断浮现同胞们在午后阳光下悲惨死去的场景。经历了这一切后,巴希尔只想不再躲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给桑切斯首相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最朴素的心愿:“我只是想要哪怕一丝希望。”
在梅利利亚的最后一天,我站在这块飞地西部的小山上,从这里可以俯瞰移民临时停留中心、郁郁葱葱的高尔夫球场以及摩洛哥法尔哈纳居民区的清真寺宣礼塔。黎明时分,召唤祈祷的铃声从摩洛哥方向传来,回荡在翠绿的球道和沙沙作响的棕榈树之间。我不由得想起一张摄于2014年的照片。照片上,两个人正在这里打高尔夫,不远处,十几名移民正在翻越边境围栏。能看出其中一名球手的余光瞥向移民,而她的球友则只顾专心打球。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梅利利亚的精髓:这座城市存在着两种格格不入的现实——即使它一直在努力屏蔽那个不和谐的音符。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