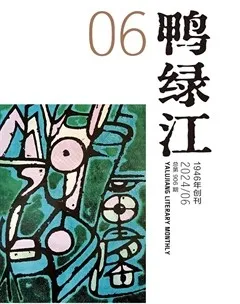还乡记
爹给我打电话,说后腰街佟家老爷子叶落归根回来了,他儿子当了县长。爹让我抽空回去一趟,给他长长威风。
佟家祖上曾在朝廷为官,后来没落了,回到老家我们村。爹说,他小的时候,佟家也和村里人家一样,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家书多。佟家的孩子都爱看书,放猪放羊手里都拿着书。
村里老辈人没事靠墙根儿晒太阳,就爱拿佟家的老皇历说事儿:那家人,祖上曾出过皇妃。本来是舞枪弄棒的武将,后来慢慢也出了文官,当了大官,当时人称佟半朝。佟家家族大,得势时几乎都搬走离开村子了。至于佟家这一支为啥回来了,有人说是这儿的风水好,绿水青山养人;有人说,是忘不了老祖宗,人得有根。具体啥原因,没人说得清楚。
我爹说,佟家人从老辈起就拿书本当回事儿,穷得叮当响也得看书。时局动荡那些年,为了把书保存下来,一家人起早贪黑,在后山的山洞里找了个地方,把家里的书都藏了起来。乡里乡亲的,大家也都睁只眼闭只眼,没人去检举揭发。
恢复高考后,佟家的书又回到了台面上。孩子们手不释卷,相继考学走了,在村子里轰动一时。当他们家最小一个孩子考上大学,佟家也搬走了,只剩一个老宅,一把铁锁锁着。院里的大枣红了落了,落了红了,院门一直没再打开过,我小时候还和同伴翻墙爬树,摘过他家的枣子。
爹年轻时在村里争强好胜,可惜在学习上一窍不通。跟村里人一样,爹眼巴巴地看着佟家孩子一个接一个考学,直到举家搬走。
我考上大学时,爹兴奋得请了全村的人来吃酒。醉酒的爹逮着人就说:“我家祖坟终于冒青烟了。”
我参加工作后,从老师做起,在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直到当上市高中的校长。爹每次给祖宗上香都说:“咱家祖坟冒青烟了,也出了读书人了。”
虽然现在村里也出了几个大学生,但村里人因为我的缘故吧,还是敬重爹。爹也毫不谦虚,逢人就说,俺家也是书香门第。说这话时,爹的眼睛总要往佟家老宅望望。
这回,佟家回来了,儿子还当了县长。在村人眼中,县长可是了不得的大官。靠墙根儿晒太阳的四太爷八十九了,捋着花白的山羊胡说:“在过去,那就是县太爷。出门是要鸣锣开道、净水泼街的。”
爹坐不住“金銮殿”了,他说,自己在村民心中的地位这回要不保了,三番五次打电话,让我务必抽时间回去一趟。
国庆节单位放假,我正好回村看爹。再不回去,爹该魔怔了,一天打好几遍电话催。媳妇有礼要随,不能陪我回去,我自己又不想开车,就找个朋友陪我,正好帮我开车。
一出市区,朋友就狠踩油门,车开得像一支离弦的箭。我在一旁不住地嘱咐他慢点儿,乡路村屯多,不知道从哪儿就钻出人来。他说,放心吧哥,我脚下有准儿。
来到乡下,空气里满是秋天的味道。大田里,农民正在忙着收秋。新擗下来的玉米棒子堆放在割倒后的秧秆间,远远望去,黄绿相间,阳光下,像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金灿灿地铺展在大地上。路旁地头的喇叭花一团团、一簇簇,水粉的、浅粉的、紫的、蓝的、白的,各种颜色混杂,闹哄哄地开着。看到这些花,总让我想起离家上大学时的情景。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我离开了村子,在大家羡慕的目光、关切的叮嘱中,踏上了求学的路。
村村通工程将乡下的路都修得平平坦坦,车跑起来非常快。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平安地抵达了老家的村前。
女儿河清亮亮地从村前奔流而过。河上的石桥是前两年新修的,栏板、柱子上刻的《二十四孝图》,还是我出的主意呢。每次回家走过这里,我都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过了桥,再有一里多地就到家了。
这个季节,山上橙红青紫,流光溢彩,各种颜色的草木混杂,远远望去,就如色彩斑斓的丝绒绸缎,披在山上。绚烂的秋色,绝不次于春花的烂漫。女儿河与马路相伴的河段,哗哗的流水声叮咚悦耳。朋友不住地夸赞:“真是灵山秀水,一看就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住在这里的人肯定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不敢说,人才倒是真出了几个。我不是说我自己啊,是……”我话还没说完,一个急转弯,车颠簸几下后停了下来。我往外一看,车窗外白花花一片,传来咩咩的羊叫声,我们陷进了羊群里。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放羊人的鞭把子已经“咚咚咚”敲在了我们的车前盖上。
“下来!下来!会不会开车?”
冤家路窄。那张愤怒扭曲的脸,正是因房基地跟我家有过纠纷的大满。
我家和大满家是邻居,两家中间最初有一条能过一人的小道,应该是老祖宗为了排雨水留下来的。前两年,我爹看别人家都盖起了亮堂的“北京平”,也要翻盖新房。打地基时,我爹让往外扩了尺寸,将原来与大满家中间相隔的小道占为己有了。
在农村,这种小道都是约定俗成,属于两家共的。如今,我爹一声不吭就占为己有,任谁都不能答应。为此,大满和他爹找我家理论,曾一度闹得我家开不了工。最后闹到村委会,因为我给村里的小学捐过桌椅,还帮村里协调解决了大棚蔬菜的销路问题,再说我家的地基已经打完了,村里当时就劝大满家,让我家给他们补偿点儿钱,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爹觉得村主任给了他面子,走路都仰着脖儿。大满一家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虽然气愤,但也认了。大满爹逢人就说,看在他家老大帮咱村儿办事儿的份儿上,这个屈俺认了。只是大满从此再没搭理过我。
车窗贴了膜,外面看不清里面的人,里面看外面却是清清楚楚。附近地里干活儿的人很快围了上来。朋友看我皱着眉,不说话,知道乡里乡亲有时更不好说,就叫我坐着别动,他下去处理。我确实不知道该咋面对大满,就坐在车里没动,说:“该咋赔咋赔,多少钱我出。”
车门打开那一瞬,大满拎着朋友的脖领子喊道:“你是怎么开车的?把我的羊都撞死了。”
朋友掰开大满的手说:“撞羊赔你钱就是了,动啥手啊。”说着让大满报个价。大满拽着他过去数羊,说:“一共撞死两只,还有一只受伤的,你掏五千块钱吧。”
“五千块钱?你抢劫啊?两千!”
“不行,五千少一分都不行。”
“就两千,你在马路上放羊,你还有理了咋的,赔你两千不少了。”
“你在这儿耍横啊?你撞死的可是母羊,那只受伤的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呢,你赔我两千够干啥?你寻思啥呢?”
“喊啥喊,你还想讹人咋的?知道车里坐的是谁不?赶紧拿钱把羊弄走,让我们过去,否则耽误了正事,你吃不了兜着走。”
朋友这一诈唬,有人劝大满把羊抬走,认了吧!有人嚷嚷五千块钱一分不能少。有的干脆就不吱声了。
“别说没用的,就是里面坐着县长,今天也得赔我羊。”大满梗着脖子喊道。
“就你这样子,信不信我告你敲诈勒索。”朋友甩开大满的手想回到车上。大满赶紧拽住朋友的胳膊,就是不撒手。
两下推搡着,谁也不让谁。我正寻思该不该下去呢,一个拿着镰刀的人拨开人群走了过来。他穿着迷彩服,头戴一顶迷彩遮阳帽,脚上一双迷彩胶鞋,戴着橡胶手套。这人我瞅着眼生,他站到副驾驶的位置,敲了敲车窗玻璃。朋友说:“你干啥?”他说:“撞了人家的羊,里面的人总得下来给个交代吧,你一个司机做得了主吗?”
“你算干嘛的?该干啥干啥去。”朋友冲着迷彩服一边嚷着一边就想推开他。
大满见状,一把薅住朋友的胳膊,扭到背后,朋友疼得直接爆了粗口。我再也坐不住了,打开车门下了车。
外面羊群咩咩地叫着,人群大声地嚷嚷着,就连天上的白云都凑热闹似的,一团一团地向这边涌来。我站到车前,吵嚷声忽然停了下来,有人咬着耳朵窃窃私语,有人和我打着招呼。
大满看到我那一刻,眼神像刀子一样从我脸上迅速划过,脸上表情复杂,刚才的愤怒瞬间变成了冷漠。他一句话没说,直接松开了薅着朋友的手,转身想去拖车前的死羊。迷彩服一把拉住他,转头对我说:“是你啊!进村咋不慢点儿开。把人家羊撞了,赶紧给赔了。”
迷彩服认识我。认识我还张口让我赔羊,这人不是脑子缺弦儿就是胆子太大。我满脸堆笑,说:“大满,你看看咋赔合适。”
大满黑着一张脸,一句话没有,扭头又要走。迷彩服再次拽住了大满。朋友不乐意了,上前一边推搡迷彩服一边说:“你算哪根葱,本家都不说话了,你还搁这旮旯拦……”朋友话没说完,只见一道黑影,大满一拳将朋友打了个趔趄,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最终,我按市场价赔了大满的羊钱,大满也被派出所的警车带走了。我不在乎钱,是丢了面子。毕竟是我邀请朋友来的,没想到刚一进村就遇到这事。在我家门口,朋友还挨了打,我心里很是窝火。
爹气得在屋里跳着脚说:“本来让你给我长威风,倒让人家灭了威风。”要不是我和朋友拦着,爹非要去大满家讨要说法。
我们在家正唠这事呢,就听门外有人喊:“老叔在家吗?”
我从窗户往外一瞅,是迷彩服,手里拎着东西,已经到了院子里。他来干嘛?
爹捅咕我一下,一边往出迎一边小声说:“他就是后腰街佟家的县长儿子。”
“啊!”我赶紧小跑两步,撵在爹的后面迎了出去。
按村里辈分,爹虽然比迷彩服小几岁,但他得管我爹叫叔。那天,迷彩服拿来两瓶西凤酒,就着炖羊肉,我们喝了起来。
酒过三巡,迷彩服说:“校长,你可是咱村的大恩人,要不是你,孩子们能用上那么好的课桌椅,用上那么明亮的教室?”我赶忙摆手示意他,言过了。他举起酒杯说:“一点儿都不过。我一回到村里,就听大家夸你。说你让咱村人挣了钱,光蔬菜大棚一项,就让大家日子富了起来。我得敬你一杯。”我只好端起酒杯,跟着他一饮而尽。
迷彩服拿过酒瓶要给我满上,我赶紧抢过来,怎么能让县长给我倒酒呢?我把酒杯倒满递过去,迷彩服接到手里,端着酒杯说:“校长,你好人做到底,还得给派出所打个电话,给大满证明一下,不是敲诈,就是纠纷,把人给放回来。一个村儿住着,往上论还连着亲呢。他打人不对,该掏药费掏药费,该掏营养费掏营养费,但性质咱可不能弄错了。”还没等我说话,他又转过头,对着我朋友说:“兄弟,我替大满先给你赔个不是。”迷彩服站起身,对着朋友举起酒杯。
朋友的右半边脸已经肿了,眼睛乌青。他瞅着我,我假装不看他,这个主我不能替朋友做。再说了,大满打的何止是朋友的脸。
迷彩服见状,又转过身子对我说:“你们都是文化人,大满是个粗人,他动手打人肯定不对。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从这点看,他就是个蠢人。正因为这,警察把他带走,我没拦,也是想给他个教训,让他长点记性。这位小兄弟受苦了,我在这里替大满给你和校长赔不是了。”
那天喝到最后,我搂着迷彩服的脖子叫大哥。迷彩服说:“虽然我是县长,你是校长,在村里,咱俩就是家人。家人就得劲儿往一处使,得想办法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都有学上。”
“咱一起帮村里把经济和教育搞上去。”我拍着胸脯向他保证。
大满爹拎着东西上门时,我挺意外。我一直怀疑,那天是迷彩服和大满爹串通好的。
大满爹把各种水果和补品堆到炕上,手脚就不知道咋放着好了。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我爹把他按到椅子上,拿来碗筷非让他一起喝点儿。大满爹哆嗦着重又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桌子上,说:“大侄子,你给咱村没少帮忙,让大家都挣着钱了,这羊钱俺们不能要。另外多出来的,是俺们给这位大侄子的补偿。大满浑,不懂事,他不该动手打人,给他个教训是应该的,俺们不怪你。大侄子,俺只求你跟派出所说一声,大满他不是敲诈。要那样,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大满爹说着就要往下跪,迷彩服和我爹一起扶住了他。我瞟一眼旁边,看见朋友拿起手机出去了,我也跟了出去。
迷彩服走时我送他,他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我攥住他的手,使劲晃了晃,眼前浮现出那群羊和大满的脸。倏忽间,一切又变成了无数的小星星,然后星星里开出了无数的喇叭花。还没等我看仔细,那喇叭花又变成了手拿唢呐的大满,正站在金灿灿的玉米地旁,鼓着腮帮子,使劲地吹着《百鸟朝凤》。
迷彩服可能不知道,我和大满是从小的光屁股娃娃,还是同学。我考上大学那年,村里村外的喇叭花开得正盛,大满就是吹着《百鸟朝凤》,送我离开的村子。只是后来,说不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迷彩服扶着我,说:“你哭了。”
我抬手抹去眼里的泪水,说:“风迷的。”
后来,在市里一次会议上又见到了迷彩服,他说:“晚上聚聚?大满也来了,参加新农村电商培训学习呢。”我说:“好啊,我做东。”
迷彩服,不,县长说:“你做东行,就是别像上回似的又喝多了。”
“上回?哈哈哈。”我笑了。上回我也没喝多。喝多了我怎么还能记着把钱给大满爹揣回去。
作者简介>>>>
梁玉梅,辽宁葫芦岛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电影家协会会员,葫芦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协会理事,连山区作家协会主席,《连山文艺》编辑部主任。作品发表于《天池小小说》《芒种》《海燕》《鸭绿江》《辽河》《辽宁日报》《中华辞赋》《诗词》等报刊,有作品被选刊转载,出版长篇人物传记《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