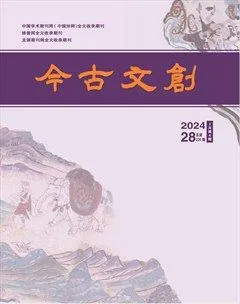“结束” 的词汇化及演变动因
【摘要】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汉语动词“结束”的历史演变,结合CCL语料库中的语料,在前人词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究“结束”的词汇变化和演变动因。“结束”在六朝至唐朝期间从并列式短语词汇化为动词,宋元明清时期词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其间韵律要求、语义变化和使用频率都在推动它词汇化的进程。
【关键词】结束;词汇化;演变动因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12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39
“结束”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有两个义项,都是动词用法:一是指“发展或进行到最后阶段,不再继续”;二是指“装束,打扮(多见于早期白话)”。[1]与“结+束”作为并列式短语的本义有所差异。虽然目前尚未有学者对“结束”一词进行研究,但针对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得出的某些普遍性结论也可以运用到其他双音节词词汇化的研究中。下面本文就将结合CCL语料库①中的语料,在前人词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结束”的历时演变情况以及词汇化的动因等进行具体分析。
一、“结束”的词汇化历程
词汇化是指从非词单位变为词汇单位的过程。“结束”由并列结构“结+束”词汇化而来。“结”在《说文解字·糸部》中注为:“结,缔也”,本义为用长条物绾系或编织,又引申出“结子(打结而成的疙瘩)”“凝聚”“连结”等义。“结子”又隐喻出“纽带”的义项,又因“结子”是“结”这个动作产生的结果,所以又引申出“终了”义。“束”在《说文解字·束部》中注为:“束,缚也”,本义为捆绑,后引申出“包扎”“约束”等义,又从“捆成一条的东西”引申出量词用法。
(一)两汉时期:“结+束”并列式短语用法
“结”“束”二词上述的引申义大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偶有两汉,使用频率不一,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早的连用出现在东汉。
例1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
意思是“为什么不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啊,人生苦短何必处处自我约束!”“束”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单用表示“约束、拘束”的用法,如例2,而“结”到东汉为止所具有的词义(“打结”“编织”“结子”“连结”“凝结”“纽带”“订立”“结成”“终了”)中并没有与“拘束”直接相关的义项,但“结束”在例1中明显是作“拘束”义,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是采用“结”和“束”的本义—— “用绳子打结”和“捆绑”,“结束”就是“用绳子打结捆绑”,代入语境作“拘束”义解释。二是这里的“结束”已经发生词汇化,但“结”的语义脱落。我们更偏向于第一种可能,因为汉代才开始有双音词汇化的趋势,“结束”第一次出现就作为词来使用的可能性不大。
例2 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也,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二)六朝至唐朝时期:短语“结+束”初步词汇化为双音词“结束”
东汉时期“结束”的连用只有例1一例,六朝后逐渐多了起来。但虽然是连用,但意思大不相同。
例3 男子皆露紒,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三国志·魏书》)
例4 其女果活。乃结束随平还家。(《搜神记·卷十五》)
例5 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万山见采桑人诗》)
例3中的“结束”是“连结捆绑”之义,“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指的是早期日本男士服装都是将几幅布帛横过来连结捆绑在一起的,因此“略无缝”。例4的大意是:父喻果然活了过来。于是她整理打扮了一番,跟着王道平回家了。例5的大意是:倡优不能忍受愁苦,梳妆整理后离开了青楼。两例中的“结束”连用都作“结发束带”义,指整饰衣服、梳妆打扮等。后又引申出整理行装、装束整齐的意思,如例6、例7、例8,这一引申义显然不是“结”和“束”单个词义的引申,组成成分的意义与整体意义的联系已经变得迂曲了。词汇化是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结束”在词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既可以称之为并列式短语,又可以称之为词的过渡阶段。而语义的变化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标准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在“整束行装”这个意义上,“结束”已经凝固成一个词来使用。虽然这种用法在南朝的文献里已经出现,但只有几例,从唐朝才开始普遍使用。
例6 便闻雁门戍,结束事戎车。(《雁门太守行》)
例7 行人结束出门去,马蹄几时踏门路。(《别离曲》)
例8 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最能行》)
又因为“梳妆打扮”“整束行装”等带有“整理、收拾”的语义特征,后来又引申出“安排 、处置”等义,见例9。
例9 青春如不耕,何以自结束。(《赠农人》)
另一个词汇化证据是“结束”词性的转变。“结”和“束”都是动词,而在唐朝一些诗文中却出现了名词用法,表示“装束、装备”等义,如:
例10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清明》)
例11 上略在安边,吴钩结束鲜。(《送灵武范司空》)
例12 老还上国欢娱少,贫聚归资结束轻。(《送蒯司录归京》)
(三)宋元明清时期:“结束”进一步词汇化
北宋时期,以《太平广志》为代表的大部分诗文中所用的“结束”之义与唐朝差别不大,还是以“装扮”“整束行李”“收拾整理”为主,词性不一。如《全宋词》《朱子语类》以及佛语录等为代表的南宋诗文语录中“结束”皆延用历代用法,未产生新义,如例13中的“结束”指的是打扮、装束,例14和例15中的“结束”都是收拾行装之义。所收诗文中也有偶然连用的用法,见例16,大意是:“一条珍珠聚拢而成的束带”,此处的“结”为“凝聚”义,“束带”自成一词,表示古时衣冠上的腰带。
例13 寻常结束,珊珊环佩,短短裙襦。(《全宋词·眼儿媚》)
例14 或言温公利餐钱,故迟迟。温公遂急结束了。(《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
例15 宗曰:“子在此多年,装束了却来,为子说一上佛法。”师结束了上堂。(《景德传灯录·卷十》)
例16 真珠蹙结束带一条。(《大金吊伐录·卷三》)
散曲、杂剧等发展推动了元朝文化进一步的繁荣。“结束”一词除了“打扮”“收拾”等常用义外,与其他字词搭配形成了固定用法,见例17、例18、例19。
例17 可怜风月地,番作战争场。自这个官家,怎生结束?进有徽宗闻宅外叫闹……才离阴府恓惶难,又值天罢地网灾。看贾奕怎结束?进有李妈妈急忙前来……(《大宋宣和遗事》)
例18若非是包龙图剖断不容情,怎结束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例19 则为这刘员外云锦百尺楼,结束了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结束”一词发展到唐朝已经引申出“安排、处置”义,例17中的“怎生结束”的大意是“怎么应对处置(这件事)”,也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能终了(这件事)”。例18和例19中“结束”的“终了”义更为明显。由此可见,到元朝,“结束”一词通过“处置”义引申出“终了”义(通过“处置”达到“终了”的结果),但“终了”义的结果只固定出现在某些元曲的文段之间作衔接语或文末作结句,使用有一定局限性。
明朝时期,“结束”一词在原来的词义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例20 那小将军怎生结束?但见:戴一顶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锦团花白银铠。(《水浒传》)
例21 却说黄忠归寨,传令来日四更造饭,五更结束,平明进兵,取左边山谷而进。(《三国演义》)
例22 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养着,不知作何结束。(《醒世恒言》)
例23 毕竟不知押赴东门怎么结束,且听下回分解。(《三宝太监西洋记》)
例24 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束时,一件也用不着。(《金瓶梅》)
例25 须得天师,才有个结束还他。(《三宝太监西洋记》)
例20的“怎么结束”根据上下文,很显然是“怎么装扮、装束”的意思,这与元曲中的“看某某怎生结束?”中的“怎生结束”又大不一样了。例21的“结束”是“整顿军队(准备战斗)”的意思,由“整束行装”引申而来。例22中的“结束”是“处置”,大意是不知道老亡八会如何处置两匹瘦马。例23的“结束”就是由“处置”义引申出的“终了、终结”义,即不知道押赴东门这件事会怎么终了。例24的“结束”指的不是事情的终结而是生命的终结,可见“结束”由“终了、终结”义引申出了“死亡”这个义项。例25是“终了、终结”义的另一个引申用法,表示“结果、了断”等义,由动词转变为名词,大意是只有天师才能给他一个结果或了断。
清朝“结束”的用例繁多,大多延用旧义“装扮”“整束行装等,“终了、终结”义也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逐渐运用到各种文书与史稿中。由于“结束”本身带有“连结”义,在战争的大环境下又引申出“结盟”义,见例26。另外,“结”引申的“缔结”义与“束”引申的“条约”义也产生了“缔结条约”的新用法,如例27和例28。可见直到清末,“结束”的词组和词的两种用法仍共存在语言系统中。但结合各个语言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出随着词汇化的推进,词的用法逐渐占了上风。
例26 各国如能协同合议,则与中国结束一事,当不甚难。(《西巡回銮始末》)
例27英新政府既有意转圜,仍饬该使臣在京续商。在我自当早图结束,以保主权。(《清史稿》)
例28其非出生於和属之侨民,仍可认为华籍,与我国国籍法亦不致相背。就此结束,俾可迅派领事,以慰侨民喁喁之望。(《清史稿》)
(四)民国时期:“结束”基本完成词汇化
到民国时期“结束”已基本完成词汇化。这一时期,“结束”主要用作动词表示“终了”义,其间也产生了新用法,即作名词,表示文章、书法、画作等文艺作品或话题的“结尾”“收尾”。
例29 一场大乱,总算从此结束。(《清史演义》)
例30 严冬之象征的店员风潮结束以后,人们从紧张,凛冽,苦闷的包围中松回一口气来。(《蚀》)
例31 不肖生写到这里,笔也秃了,眼也花了,暂借此做个天然的结束,憩息片时,再写下去。(《留东外史》)
例32 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而已集》)
例33 至于“花”字,“山花零落”句,即是结笔,可就不必再结束了。(《评讲聊斋》)
例34 “有什么尼姑庵,教会,清苦些,我也甘愿!”黄夫人叹口气结束着说,眼眶也红了。(《虹》)
例29、例30中的“结束”都是典型的表“终了”义的动词用法。例31、例32中的“结束”指代的都是作品的结尾部分;而例33的“结束”是“完成作品的结尾部分”,即“收尾”义,整个句子的大意为:“山花零落”句已经是结笔了,可以不用再收尾了;例34中的“结束着说”是只在民国的书面语中出现的特殊用法,这里的“结束”修饰“说”,表示说话人的目的,用于说话人想终了对话的情况下。例31、例32、例33、例34这四例中“结束”一词的含义都是含有[末了]这样的义素,实际上也就是“终了”义引申而来,只不过其中涉及了词性的变化。
因为传记、史书等不可避免会沿用所记录的朝代的常用词义,所以如“系”“整理”“装扮”“处理”等历代的常用义也偶尔会出现在民国的文学作品中。当然也有民国的其他文学作品和口语中会使用这些义项,但主要还是以上述的新义为主,见例35-例38。
例35 广结束了衣冠、梳洗完毕,已是天色大明。(《隋代宫闱史》)
例36 一脑青丝,本是披散了,不曾结束,一大哭,一乱动,更乱蓬蓬的。(《留东外史续集》)
例37 每当风和日暖天气,么妹蛮装窄袖结束得天人相似。(《清朝秘史》)
例38 家里的事,就让敏之和二姨太结束。(《金粉世家》)
但由于词组形态的义项的存在,让我们不能判断表示这类义项的“结束”究竟是属于词组用法还是词的用法,所以目前只能姑且推断“结束”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词汇化。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彻底完成词汇化
根据CCL语料库提供的语料,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结束”一词无论是在书面语中还是口语中,基本上都作为动词使用,表“终了”义,只在小部分文学作品中还有“结果”“结尾”等名词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的“整理”“装扮”等由本义引申出的过去的常用义项已经彻底消失在人们的日常语言系统中,只保留“终了”义,名词用法就算出现在个别文学作品中也是被当成“结束”在该语境下的特殊用法。至此可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彻底完成词汇化,动词“终了”义成为最普遍的用法。
二、“结束”的词汇化动因
(一)韵律的制约
一个韵律词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而“结”“束”作为一个双音节短语,满足了一个音步的要求,构成一个韵律词,具备了造词的形式基础。因为音步是在语音上结合最为紧密的自由单位,处在同一音步中的短语组成成分之间的距离就被拉近了,在反复的使用中它们之间的句法关系可能逐渐变得模糊,最终变为一个在句法上无须再做分析的单纯的单位,韵律词就发展为词汇系统中的词。“结”和“束”词性都为动词,董秀芳先生曾说过,双音节音步的出现给汉语词汇构造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并列式双音节词的产生,所以“结+束”词汇化也是合乎构词规律的。[2]且“结+束”首次出现是在东汉,冯胜利先生认为双音节音步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它的建立大约就是在汉代[3],双音节化的趋势也促进了这一短语后期的词汇化。
(二)语义的变化
大部分短语结构词汇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语义的变化。这些语义变化会使得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由直接变得迂曲,双音词的理据性大大低于作为其源头的同形短语,甚至某些意义很难从它的内部形式看出来,这一类复合词往往进一步向单纯词演化。[2]
1.语义泛化与虚化
所谓泛化与虚化,是指实词语义的抽象化、一般化和扩大化,以实词部分具体义素的脱离和词义的适用范围扩大为前提。[4]语义的泛化和虚化是促进词汇化历程的重要因素。
因为“结+束”有“结发束带”用法,所以引申出“梳妆打扮”“整理装束”等义(例4),原先只指整理头发和衣带,现在泛指整个人的形象。在这一意义上,又引申出“整理行装”的意思(例8),之后用在战争情境中又引申出“整顿军队”的意思(例21),从专指整理人穿在身上的装扮到泛指整理临出发前的所有行装,再到临战斗前整顿军队,行为动作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
因为这些引申义都带有“整理”“收拾”的语义特征,所以又引申出“安排”“处置”义(例9),在此基础上又引申出“终结”“终了”义(例19),最后又引申出“死亡”义(例24),不断抽象化。
理清上述的语义引申链,再回头看“结”与“束”的本义:“结”本义为用长条物绾系或编织,“束”本义为捆绑。我们可以发现“结束”从“梳妆打扮”义开始,之后的引申义就逐渐抽象化,脱离具体义素并且适用范围发生了扩大。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从“行域”到“知域”,这其中隐喻机制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2.部分语义弱化或脱落
语义演变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具体义素脱落,甚至有时会造成偏义复合词的出现。比如:例39的“结束”为“捆绑”义,例40的“结束”是打结的意思,例41的“结束”作“连结”义等。
例39 背后结束着一个包裹,胯下藏着一柄单刀。(《施公案》)
例40 绳索结束牢固,惟恐不能收口,只好顺著风头飘了。(《镜花缘》)
例41 天海两结束,月酒两钩联。(《野叟曝言》)
语义演变的过程是复杂的,有时往往会几种形式叠加在一起。就像“束”本身就有“收拾”“整理”的意思,“束装”就是“整理行装”,见例42,所以“结束”的“整理行装”义究竟是从“梳妆打扮”引申而来,还是“结”的语义脱落,也是个值得考究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结束”的“终结”“终了”义,“结”本身也有该义项,所以“结束”的这个义项是从“安排”“处置”义引申而来,还是“束”语义脱落造成的,也尚待解决。
例42 一日宿在饭店,天明起来束装,不见了一个盛银子的顺袋。(《无声戏》)
3.转类
转类而引起语义变化在“结束”的词汇化过程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装备”“结果”等义为代表的明显发生词性转变的义项,由原本动作性成分“整理装备”“终结”变为名词“装备”“结果”。另一类是以“装扮”为代表的本身就兼作动词和名词的义项,正因为这类义项的存在,所以导致从句法位置来判断词性的变化变得困难。
无论是语义引申还是语义脱落,都是“结束”凝固成词的证据。唐朝是“结+束”结构词汇化历程的重要节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抽象化的“整束行装”义和名词性成分“装备”,这证明了双音词“结束”已经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三)使用频率的增加
双音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隐藏着人为的推动因素。只有两个成分经常在一起出现,才有词汇化的可能。汉代以后双音词开始频繁进入人们视线,其中又属并列式双音词作为同义单音词的风格变体最受语言使用者们喜爱。[2]“结”和“束”都需要对长条状物体进行操作,语义上有一定相近性,为语言使用者使用它们作为并列短语提供可能。唐朝后,“结束”一词使用频率显著增加,又不断发展出其他词义。直到清朝后,在战争的大背景下,“结束”的“终结、终了”义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逐渐发展成现代汉语中“结束”最常用的意义。
三、总结
“结”“束”两词连用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结束”的词汇化虽然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但CCL语料库所收文例较少,相较于六朝,“结束”在唐朝诗文里出现得更为频繁,且意义更丰富。因为“整束行装”义(语义泛化和虚化)和“装束、装备”义(转类)在唐朝诗文中的大量使用,所以我们姑且可以推断出“结束”在六朝至唐朝时期实现了词汇化,但只涉及部分义项。宋元明清时期进一步词汇化,词义继续引申与发展,其间也涉及部分组成成分语义的弱化或脱落。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常用的“终结、终了”义是从元朝开始出现,且只出现在固定段落。直到明清时期,在战争的大背景下,“终结、终了”义的使用频率逐渐上升。民国时期“结束”基本完成词汇化,围绕着“终了”义的[末了]义素又产生了一些新用法,但一些传记、史书仍保留过去的常用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的动词用法(表“终了”义)成为语言系统中的最常用的用法,词组时期产生的义项在语言系统中完全消失,才彻底完成词汇化的历程。
注释:
①本文所使用的语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本文只在论述“结束”的词汇化过程时标注引文的具体出处,其他例句并未标明其具体来源。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67.
[2]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节词的衍生和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8-44.
[3]冯胜利.汉语双音化的历史来源[J].现代中国语研究,2000,(01).
[4]张谊生.试论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J].历史语言学研究,2016,(0).
[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古代汉语词典:大字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许少锋.近代汉语大词典(上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李昉.太平广记(全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21.
[9]孟郊,郝世峰.孟郊诗集笺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11]孙文良,董守义.清史稿辞典(上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12]张秀松.词汇化与语法化理论及其运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13]张峰.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特征探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25):42-46.
[14]陆露露.“不止”的词汇化与语法化[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5(04):64-69.
作者简介:
时新语,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