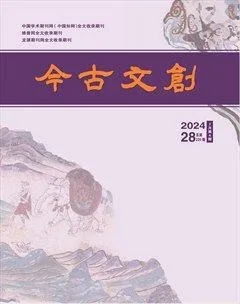概念隐喻视角下《玉米》中的本体隐喻英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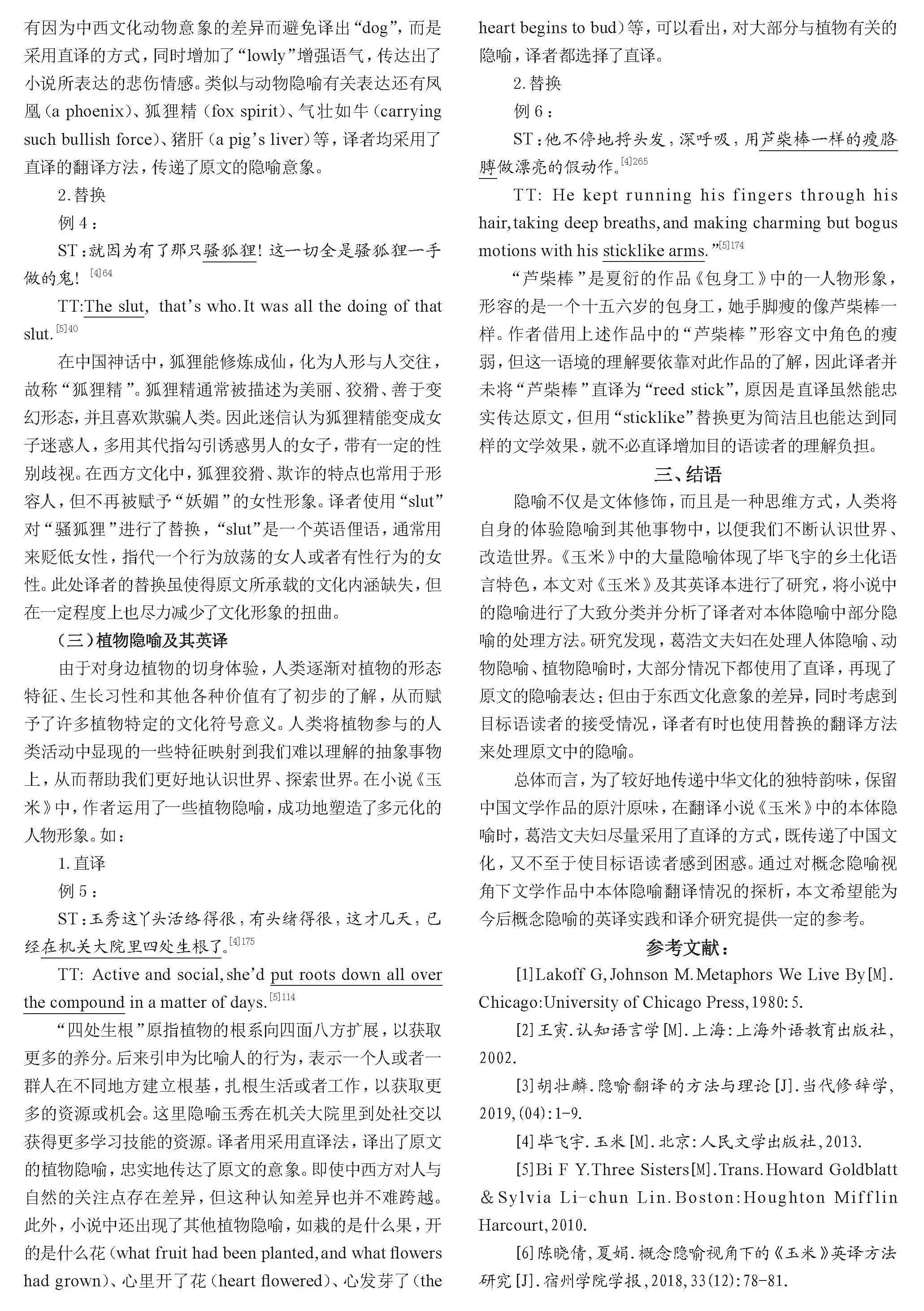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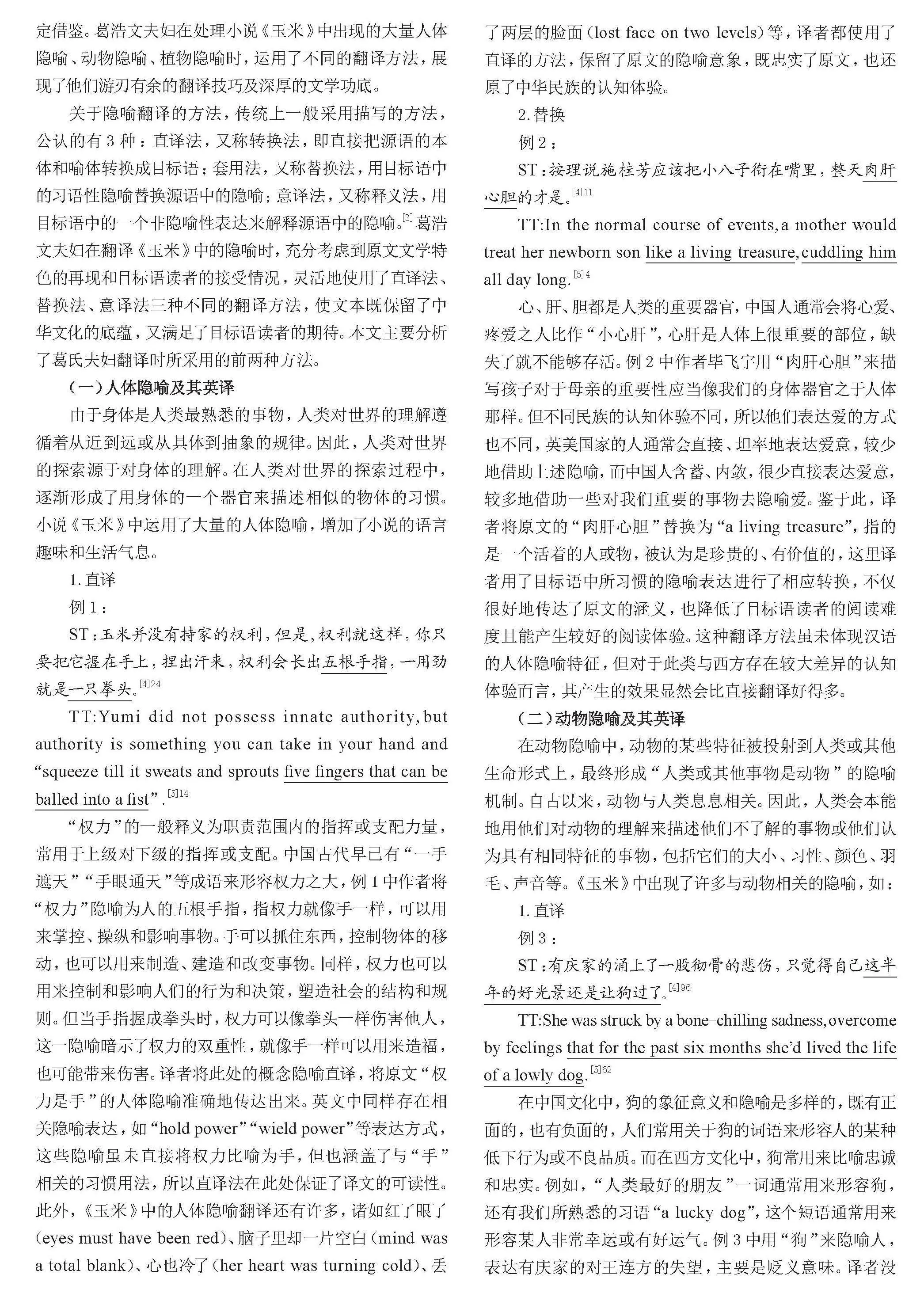
【摘要】概念隐喻作为人类的一种认知与思维方式,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话语表达。小说《玉米》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表达,译者葛浩文夫妇对其中隐喻的灵活处理可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一定借鉴。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玉米》英译本中的本体隐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译者在处理人体隐喻、动物隐喻、植物隐喻三种本体隐喻时,较多地使用了直译,保留了原文的隐喻意象;但由于东西文化意象的差异,同时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情况,译者有时也使用替换等翻译方法来处理原文中的隐喻。
【关键词】概念隐喻;《玉米》;本体隐喻;隐喻英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1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34
《玉米》这部由当代作家毕飞宇创作的长篇小说,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小说围绕着王家三姐妹在与命运相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堪层层展开,让读者得以窥见特殊年代下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小说运用了大量的经典隐喻,充分彰显了作者精湛的写作手法。《玉米》英译本Three Sisters由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及其夫人林丽君合译而成,并得到了西方文学界的极大肯定,获得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国内对《玉米》的英译研究主要从形貌修辞、霍恩比“综合法”视角、生态翻译学及作者、译者与读者的视界融合等方面展开。从概念隐喻视角阐释的文章目前仅有一篇,即陈晓倩和夏娟从概念隐喻视角对《玉米》隐喻英译方法的探析,其主要从宏观层面阐释了映射相同、映射有差异及映射完全不同三种情况下译者对隐喻的处理情况。但该研究仅从宏观上总体探析了三种映射条件下的隐喻翻译,尚缺乏对具体隐喻类型下隐喻翻译情况的探索。本文将基于概念隐喻视角对《玉米》及其英译本的本体隐喻翻译方法进行案例分析,进而探讨译者对原文中本体隐喻的处理情况。
一、概念隐喻理论
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或几个词,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隐喻的映射过程。[1]莱考夫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隐喻是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隐喻是一种从源域到目标域的系统映射,它通过联想事物的相似特征使概念具体化,将基本经验映射到抽象认知域上,从而达到理解抽象事物的目的。莱考夫和约翰逊经过深入研究,揭示了英语中众多表达的深层含义,它们均源自一系列基础而核心的隐喻。例如,“辩论是战争”“人生是旅途”和“思想是食物”等,他们将这样的隐喻表达称为概念隐喻。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过程,源域是言者完全熟悉的明确的概念,而目标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需要在源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解。
二、《玉米》中的本体隐喻及其英译
本体隐喻是指人们将抽象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有形的实体,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谈论、量化、识别其特征及原因等,其中可分为三小类:实体和物质隐喻、容器隐喻、拟人隐喻。[2]第一,实体和物质隐喻:把经验视作实体或物质,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就可对经验做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如指称、量化、分类等。[2]第二,容器隐喻:将本体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边界、可量化、能进、可出。[2]第三,拟人隐喻:将事体视为具有人性就是一个明显的本体隐喻。[2]人体及其器官是隐喻的重要源域,同时也在特定语境中作为目标域,展现了隐喻的丰富性。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加深,人类逐渐使用与其息息相关的动植物来实现隐喻。因而出现了动物隐喻和植物隐喻。无论是人体隐喻、动物隐喻,还是植物隐喻,它们以人体、动物、植物作为本体映射于抽象物体上,实现跨域映射,最终实现对相关概念或概念结构的理解。然而,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民族的认知体验也存在着差异,导致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和认知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认识世界时产生的概念联想也会有所不同,这可能对中国文学外译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基于此,对隐喻翻译的研究将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定借鉴。葛浩文夫妇在处理小说《玉米》中出现的大量人体隐喻、动物隐喻、植物隐喻时,运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展现了他们游刃有余的翻译技巧及深厚的文学功底。
关于隐喻翻译的方法,传统上一般采用描写的方法,公认的有3种:直译法,又称转换法,即直接把源语的本体和喻体转换成目标语;套用法,又称替换法,用目标语中的习语性隐喻替换源语中的隐喻;意译法,又称释义法,用目标语中的一个非隐喻性表达来解释源语中的隐喻。[3]葛浩文夫妇在翻译《玉米》中的隐喻时,充分考虑到原文文学特色的再现和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情况,灵活地使用了直译法、替换法、意译法三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使文本既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底蕴,又满足了目标语读者的期待。本文主要分析了葛氏夫妇翻译时所采用的前两种方法。
(一)人体隐喻及其英译
由于身体是人类最熟悉的事物,人类对世界的理解遵循着从近到远或从具体到抽象的规律。因此,人类对世界的探索源于对身体的理解。在人类对世界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用身体的一个器官来描述相似的物体的习惯。小说《玉米》中运用了大量的人体隐喻,增加了小说的语言趣味和生活气息。
1.直译
例1:
ST:玉米并没有持家的权利,但是,权利就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利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4]24
TT:Yumi did not possess innate authority,but authority is something you can take in your hand and “squeeze till it sweats and sprouts five fingers that can be balled into a fist”.[5]14
“权力”的一般释义为职责范围内的指挥或支配力量,常用于上级对下级的指挥或支配。中国古代早已有“一手遮天”“手眼通天”等成语来形容权力之大,例1中作者将“权力”隐喻为人的五根手指,指权力就像手一样,可以用来掌控、操纵和影响事物。手可以抓住东西,控制物体的移动,也可以用来制造、建造和改变事物。同样,权力也可以用来控制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塑造社会的结构和规则。但当手指握成拳头时,权力可以像拳头一样伤害他人,这一隐喻暗示了权力的双重性,就像手一样可以用来造福,也可能带来伤害。译者将此处的概念隐喻直译,将原文“权力是手”的人体隐喻准确地传达出来。英文中同样存在相关隐喻表达,如“hold power”“wield power”等表达方式,这些隐喻虽未直接将权力比喻为手,但也涵盖了与“手”相关的习惯用法,所以直译法在此处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此外,《玉米》中的人体隐喻翻译还有许多,诸如红了眼了(eyes must have been red)、脑子里却一片空白(mind was a total blank)、心也冷了(her heart was turning cold)、丢了两层的脸面(lost face on two levels)等,译者都使用了直译的方法,保留了原文的隐喻意象,既忠实了原文,也还原了中华民族的认知体验。
2.替换
例2:
ST: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4]11
TT: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a mother would treat her newborn son like a living treasure,cuddling him all day long.[5]4
心、肝、胆都是人类的重要器官,中国人通常会将心爱、疼爱之人比作“小心肝”,心肝是人体上很重要的部位,缺失了就不能够存活。例2中作者毕飞宇用“肉肝心胆”来描写孩子对于母亲的重要性应当像我们的身体器官之于人体那样。但不同民族的认知体验不同,所以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也不同,英美国家的人通常会直接、坦率地表达爱意,较少地借助上述隐喻,而中国人含蓄、内敛,很少直接表达爱意,较多地借助一些对我们重要的事物去隐喻爱。鉴于此,译者将原文的“肉肝心胆”替换为“a living treasure”,指的是一个活着的人或物,被认为是珍贵的、有价值的,这里译者用了目标语中所习惯的隐喻表达进行了相应转换,不仅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涵义,也降低了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难度且能产生较好的阅读体验。这种翻译方法虽未体现汉语的人体隐喻特征,但对于此类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的认知体验而言,其产生的效果显然会比直接翻译好得多。
(二)动物隐喻及其英译
在动物隐喻中,动物的某些特征被投射到人类或其他生命形式上,最终形成 “人类或其他事物是动物” 的隐喻机制。自古以来,动物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人类会本能地用他们对动物的理解来描述他们不了解的事物或他们认为具有相同特征的事物,包括它们的大小、习性、颜色、羽毛、声音等。《玉米》中出现了许多与动物相关的隐喻,如:
1.直译
例3:
ST:有庆家的涌上了一股彻骨的悲伤,只觉得自己这半年的好光景还是让狗过了。[4]96
TT:She was struck by a bone-chilling sadness,overcome by feelings that for the past six months she’d lived the life of a lowly dog.[5]62
在中国文化中,狗的象征意义和隐喻是多样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人们常用关于狗的词语来形容人的某种低下行为或不良品质。而在西方文化中,狗常用来比喻忠诚和忠实。例如,“人类最好的朋友”一词通常用来形容狗,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习语“a lucky dog”,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某人非常幸运或有好运气。例3中用“狗”来隐喻人,表达有庆家的对王连方的失望,主要是贬义意味。译者没有因为中西文化动物意象的差异而避免译出“dog”,而是采用直译的方式,同时增加了“lowly”增强语气,传达出了小说所表达的悲伤情感。类似与动物隐喻有关表达还有凤凰(a phoenix)、狐狸精 (fox spirit)、气壮如牛(carrying such bullish force)、猪肝(a pig’s liver)等,译者均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传递了原文的隐喻意象。
2.替换
例4:
ST:就因为有了那只骚狐狸!这一切全是骚狐狸一手做的鬼![4]64
TT:The slut, that’s who.It was all the doing of that slut.[5]40
在中国神话中,狐狸能修炼成仙,化为人形与人交往,故称“狐狸精”。狐狸精通常被描述为美丽、狡猾、善于变幻形态,并且喜欢欺骗人类。因此迷信认为狐狸精能变成女子迷惑人,多用其代指勾引诱惑男人的女子,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在西方文化中,狐狸狡猾、欺诈的特点也常用于形容人,但不再被赋予“妖媚”的女性形象。译者使用“slut”对“骚狐狸”进行了替换,“slut”是一个英语俚语,通常用来贬低女性,指代一个行为放荡的女人或者有性行为的女性。此处译者的替换虽使得原文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缺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尽力减少了文化形象的扭曲。
(三)植物隐喻及其英译
由于对身边植物的切身体验,人类逐渐对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和其他各种价值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而赋予了许多植物特定的文化符号意义。人类将植物参与的人类活动中显现的一些特征映射到我们难以理解的抽象事物上,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探索世界。在小说《玉米》中,作者运用了一些植物隐喻,成功地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形象。如:
1.直译
例5:
ST:玉秀这丫头活络得很,有头绪得很,这才几天,已经在机关大院里四处生根了。[4]175
TT: Active and social,she’d put roots down all over the compound in a matter of days.[5]114
“四处生根”原指植物的根系向四面八方扩展,以获取更多的养分。后来引申为比喻人的行为,表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不同地方建立根基,扎根生活或者工作,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或机会。这里隐喻玉秀在机关大院里到处社交以获得更多学习技能的资源。译者用采用直译法,译出了原文的植物隐喻,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意象。即使中西方对人与自然的关注点存在差异,但这种认知差异也并不难跨越。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其他植物隐喻,如栽的是什么果,开的是什么花(what fruit had been planted,and what flowers had grown)、心里开了花(heart flowered)、心发芽了(the heart begins to bud)等,可以看出,对大部分与植物有关的隐喻,译者都选择了直译。
2.替换
例6:
ST:他不停地捋头发,深呼吸,用芦柴棒一样的瘦胳膊做漂亮的假动作。[4]265
TT: He kept running his fingers through his hair,taking deep breaths,and making charming but bogus motions with his sticklike arms.”[5]174
“芦柴棒”是夏衍的作品《包身工》中的一人物形象,形容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包身工,她手脚瘦的像芦柴棒一样。作者借用上述作品中的“芦柴棒”形容文中角色的瘦弱,但这一语境的理解要依靠对此作品的了解,因此译者并未将“芦柴棒”直译为“reed stick”,原因是直译虽然能忠实传达原文,但用“sticklike”替换更为简洁且也能达到同样的文学效果,就不必直译增加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负担。
三、结语
隐喻不仅是文体修饰,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类将自身的体验隐喻到其他事物中,以便我们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玉米》中的大量隐喻体现了毕飞宇的乡土化语言特色,本文对《玉米》及其英译本进行了研究,将小说中的隐喻进行了大致分类并分析了译者对本体隐喻中部分隐喻的处理方法。研究发现,葛浩文夫妇在处理人体隐喻、动物隐喻、植物隐喻时,大部分情况下都使用了直译,再现了原文的隐喻表达;但由于东西文化意象的差异,同时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情况,译者有时也使用替换的翻译方法来处理原文中的隐喻。
总体而言,为了较好地传递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保留中国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在翻译小说《玉米》中的本体隐喻时,葛浩文夫妇尽量采用了直译的方式,既传递了中国文化,又不至于使目标语读者感到困惑。通过对概念隐喻视角下文学作品中本体隐喻翻译情况的探析,本文希望能为今后概念隐喻的英译实践和译介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5.
[2]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3]胡壮麟.隐喻翻译的方法与理论[J].当代修辞学,
2019,(04):1-9.
[4]毕飞宇.玉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Bi F Y.Three Sisters[M].Trans.Howard Goldblatt&Sylvia Li-chun Lin.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
[6]陈晓倩,夏娟.概念隐喻视角下的《玉米》英译方法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18,33(12):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