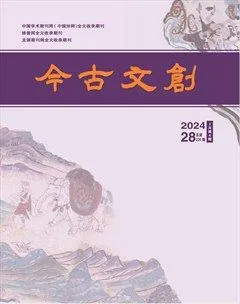想象力消费电影的伦理化情感建构研究
【摘要】《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是中国“神话史诗片”的里程碑之作,将历史底蕴与宏大场面相结合,谱写荡气回肠的上古神话故事,收获广泛关注。创作者对文学文本进行别出心裁的改编,选择姬发作为主人公,讲述青年英雄的成长故事,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同时,电影提炼出“家国同构”的叙事核心与情节结构,运用家国一体的叙事方式,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想象力消费电影中焕发活力提供思路。
【关键词】《封神第一部》;想象力消费电影;伦理化情感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9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30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观众对于充满想象力的电影的艺术欣赏和文化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大。[1]传统东方奇幻电影作为中国想象力消费电影的主要类型,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恢宏壮丽的奇观空间,为观众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一方面在想象力消费电影中建立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另一方面进行现代化转型,自觉参与到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中。
国产电影具有伦理化情感的特征,将理性化的思想主题进行情感化的艺术表达,在家庭伦理叙事中产生对现实的多重反映,通过特定的情感语境,传递不受时代话语限制的普遍价值,这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有关。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形成了与之对应的生活模式与情感模式。尽管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们对传统伦理的重视程度有所削弱,但是,人们对亲情的依赖,仍然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呼唤和挖掘民族共同记忆和情感经验,仍然是当下电影创作的重要思路。
想象力消费电影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现代观众提供情感体验,获得共鸣与认同。将想象力消费与伦理化情感相结合,有助于电影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取材于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充分发挥神话史诗富于想象力的特点,构建庞大瑰丽的世界观,借助父子的伦理冲突,讲述王朝更迭的故事,在回应民族记忆的同时,也在不断重构传统文化,实现古老神话的当代演绎。
一、《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伦理化情感叙事策略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一改以往封神改编作品以神为核心的叙事思路,把人的权力斗争作为电影的主要内容,选择姬发作为主人公,讲述青年英雄的成长故事,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电影提炼出“家国同构”的叙事核心与情节结构,运用家国一体的叙事方式,实现古老神话的当代演绎。
(一)人物形象重构:青年英雄的成长故事
家庭伦理情感是当下观众观影时重要的潜在情感需求。千年来,受“君臣父子”的儒家文化影响与近些年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当下青少年的情感天然亲近家庭情感缺失式的青年英雄主人公,也天然能够共情他们的成长故事。想象力消费电影以青少年为目标群体,选择家庭情感缺失的青年主人公,能够以他们的成长故事增加观众对家庭的期待与认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选择姬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以成长中的青年男性的第一视角讲述商末人神混战的神话史诗。姬发作为质子,从小在商朝都城朝歌长大,立志成为英雄,将骁勇善战的殷寿视为“精神父亲”,一度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姬昌。在殷寿借助狐妖的能力弑父坐上王位后,姬发面临被逼弑父和亲生父兄受难的困境,认清了纣王残暴不仁的真实面目,完成自我的觉醒。于是,他杀死纣王,回归故土西岐与父亲重逢。英雄成长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代观众的期待,家庭伦理的叙事也呼应了观众自身的情感经验。
电影对青年群体价值选择的刻画,凸显出当下年轻群体对个人身份选择的态度。姬发的觉醒过程是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在姬发撞破四伯侯密谋谋反的现场时,面对姬昌脱口而出的“这是我儿子姬发啊”,姬发的回应是“我是殷商王家御前侍卫姬发”。而在龙德殿弑父情节后,受到冲击的姬发听到姬昌“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内心受到触动,对自我的身份进行反思。经过一系列考验和磨难后,姬发完成了自我觉醒与“精神弑父”。纣王之子殷郊、“质子旅”的其他一些成员均有与姬发相似的成长经历。殷郊从最初相信父亲是被狐妖迷惑到发现纣王的残暴本性,实现自我的觉醒。质子旅的成员最初都视殷寿为英雄和父亲,随着龙德殿“弑父”一事内心受到巨大冲击,被迫做出选择。姬发的兄长伯邑考为了营救被殷寿囚禁的父亲姬昌,违背父命,携珍宝前往朝歌,选择替父受死。电影中的青年群体的价值选择在铺就人物心路历程的同时,将“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的信念传递出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姬发与殷郊、伯邑考等人的相处与情感交流,也传递出中华传统文化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朴素信念。
(二)叙事技巧更新:家国同构的故事表达
中华文明是一个世俗化的文明,文明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靠日常家庭生活的凝聚力逐层扩展到社会来实现的。[2]因此,国产电影不乏以家事喻国事的表达。借由家庭矛盾表现历史变革和政治动荡,既能够与观众建立起有效的沟通途径,也能够丰富电影的意义空间。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王朝更替的宏大史诗被融入两个家庭的矛盾叙事之中。由此,一个历史性的主题被转变成更为封闭、更贴近观众的情感主题。同时,电影利用作为国君和父亲是否仁慈正义暗示国家兴衰与王朝更迭。电影为主人公姬发设置了两位父亲。亲生父亲西伯侯姬昌勤勉、仁义、忧民,作为父亲深爱并牵挂着自己的儿子,远赴朝歌时告诫儿子伯邑考,告诉姬发“环”的真正含义是“还家”。姬昌的家庭是千百年来儒家所倡导的和谐美满的家庭范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谐的家庭情感赋予姬发健全的人格,因此姬发即便遭到殷寿的蒙骗,也能迷途知返、捍卫正义。“精神父亲”纣王殷寿则是与姬昌截然相反的国君与父亲形象。面对自己的父兄,他毫无敬爱之心,利用狐妖法术操控太子殷启当朝刺死父亲商王帝乙。作为国君,他残暴不仁、践踏人伦,逼迫四大伯侯之子杀死父亲,强迫姬昌食子。最终殷寿被姬发刺死,姬昌在故国西岐等待姬发还家的情节设置,为电影的伦理冲突赋予更深层次的家国含义。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以父子冲突为故事核心,借伦理秩序的崩坏与重建,讲述伦理背后的权力斗争,以现代视角重述上古神话故事。电影主人公姬发作为质子入朝歌八年,成长受殷寿影响,渴望成为像殷寿一样骁勇善战的英雄,纣王之子殷郊被父亲多次怀疑仍然相信父亲是被狐妖蒙蔽。电影以细腻的镜头语言讲述两个“儿子”对于“父亲”如何从崇拜到失望乃至绝望,将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转变为更能引发现代观众共情的家庭伦理冲突,赋予了“武王伐纣”现代语境下的合理性。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君权与父权是一体的,姬发与殷寿之间亦父亦子、非父非子的君臣关系在被颠覆与瓦解后,权力斗争的真相得以表达。这也暗合了《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作为神话史诗类型电影抛弃神仙中心叙述,转而讲述人的故事的初心,父子相残是残酷权力斗争的产物,而非天谴。
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的伦理化情感
表达机制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重塑
人类社会进入后现代,各种艺术形式也表现出后现代特征,消解、颠覆现代性是其核心。《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伦理化情感建构以解构权力的方式实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敬畏权力,将其视为牢不可破的存在。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解构主义的兴起,个体与群体的联系较以往更为疏远,人与人的相处存在虚拟化、分散化、碎片化的特点。千百年来所塑造出的权力的权威性被打破,从而成为被质疑和解构的对象,使电影呈现出个体与环境、自我进行抗争的重塑自我的过程,最终表达出关于人性的人文主义关怀。电影中权力化身殷寿被青年英雄姬发刺死,代表着电影创作者解构权力、质疑权威的意图。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回避了宏大叙事,借家庭伦理冲突引发观众共鸣。传统电影通常通过宏大叙事表现社会责任感、精英意识、严肃的价值追求。[3]但是,现代社会观众难以共情君权至上的伦理观念,厌恶说教意味浓厚的道德宣传。电影通过构建多重的父子伦理关系,通过姬发这一成长中的青年英雄视角,将历史事件转变为父子冲突。姬发的心理过程是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同样会面临的伦理困局。基于父子的伦理UTZyadpUi7VbjsBe6JDlONBuTIX3ldNrFUqoUVTeUb8=冲突,电影连接起了古人和今人,成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在表现对传统道德的颠覆时,电影将缺乏传统伦理道德约束的人性阴暗面,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在“龙德殿四大伯侯父子对峙”和“伯邑考之死”两个情节中,将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弑父与食子的内容设置,在为观众带来强烈冲击的同时,体现出传统伦理的崩塌。而最终姬发杀死纣王殷寿,千里奔逃回归故国西岐的情节,也暗示着人性的回归。在伦理的崩塌与重塑中,电影实现了个体对自我价值的建立与反思,同时,又表现出对生命的希望。
(二)情感共振与代入式想象
网生一代对于情感的需求呈现出虚拟性的特征,即他们不再固执地追求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生活,而是寄托于虚拟的文本,建立个体与虚拟存在的情感连接。[4]作为观众,他们秉持着具有鲜明情感倾向的视角,对故事中的虚拟角色投注情感。《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个人化叙事视角强化了这种情感体验。观众最初跟随姬发的视角,对强大勇猛、骁勇善战的殷寿投注敬佩之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殷寿对殷郊、姬昌、伯邑考的迫害有目共睹,观众对姬发的内心挣扎感同身受。由此,银幕内外,虚拟人物和现实观众的情感达到同频共振。
由于互联网时代游戏文化的盛行,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将自身对获得他人关注的渴望投注于虚拟角色上,期待看到落寞的个体角色成长为拯救苍生的英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代入式想象赋予观众最直接的情感刺激。消费主义刺激下,游戏式的生命体验,使得网生代观众面对电影所表现的伦理困局时,产生一种敢爱敢恨的直率,且不吝于使用以暴制暴的简单法则。因此,在被观众所认为的“理想中的兄长”伯邑考,被纣王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折磨致死后,姬发与纣王的决裂获得观众的共鸣,家与国的叙事达到高度统一。在故事结尾宏大混乱的战斗场面中,观众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得到宣泄。而在姬发刺死纣王,回归西岐时,电影对等待儿子归家的姬昌的刻画,使观众感受到来自家庭情感的治愈。
三、想象力消费电影的伦理化情感建构意义
现代社会观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更多的是一种寻找主体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而这一文化消费中,通常代表着当下观众对情感的需求与想象。国产想象力消费电影植根于传统文化,根据现实语境进行具有时代特色的改编,一方面获得观众的文化认同,建构起民族想象;另一方面助力中国故事向外传播,平等自信地与其他文化交流。
(一)重塑集体记忆,呼唤价值理性
安德森将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同源共生的族群在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影响下,对内消弭分歧,对外区分“他者”。这种社会心理依托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在造就各民族品格的同时,也建立起独一无二的文明。互联网创造了崭新的时空语境和权力关系,为集体记忆的书写和阐释带来了挑战。在互联网的冲击下,集体记忆走向平面化和庸常化。海量的信息消解了集体记忆的存在感。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衰微凋敝,伦理、审美、信仰面临缺失之苦。
叙事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状态的呈现。伦理叙事的内核是道德精神,通过故事表达理解,目的是要促进道德自觉,关键是要产生道德实践力量。[5]以《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为代表的想象力消费电影取材于传统文化,将集体记忆融入电影创作,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从而提升民族的凝聚力。
同时,想象力消费电影以网生代青少年群体为目标群体,借助伦理化情感表达,能够将宏大主题转化为符合民族情感模式和网生代观众解读思路的价值传达。特定的影像空间成了为观众提供创造集体记忆的重要场域,情感化的艺术表达相对于史实资料更具活力,观众对内容的多元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集体记忆的挖掘与重塑。而这些借助互联网得以重构的集体记忆,也会形成新的民族集体记忆,从而实现民族精神的传承。
(二)关注普遍价值,助力海外传播
国产电影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往往由于面临文化语境的巨大差异,而无法完整表达电影展现的情怀,使国外观众无法对电影所传递的精神产生共鸣。巴拉兹认为:“任何一部影片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先决条件之一是要有为全世界人民所能理解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东西方民族存在文化差异,这种“文化折扣”的存在,要求国产影片在进行国际传播时,要尽力表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关注人类共有的亲情、爱情与友情。伦理化情感着眼于家庭关系,将复杂的思想主题,借助情感化的叙述手段表达,降低文化传播的门槛。同时,伦理化的情感叙事,作为中国电影常见的一种叙事建构方式和原则,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与价值。当下的中国电影正处于多元文化融合与追求文化创新的时代,需要在文化建设中不断包容多元文化,在世界视野下不断重构传统文化,使中国电影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在电影走向市场的当下,由于社会变革、观念多元,想象力消费电影的创作面临巨大挑战。借助伦理化的情感叙述手段,有助于想象力消费电影在商业价值和人文情怀中寻求平衡,使观众对伦理情感的依赖与电影的价值传播实现和谐共生。随着中国想象力消费电影的蓬勃发展,如何让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与价值在互联网时代大放光彩,建构青年一代的认同,仍需不断思考与努力。
参考文献:
[1]陈旭光.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J].当代电影,2020,(01):126-132.
[2]钟大丰.类型电影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折射现实[J].当代电影,2020,(01):4-8.
[3]彭成,田鹏.从动物到“上帝”的黑色寓言——影片《一出好戏》的后现代伦理[J].电影评介,2018,(15):21-25.
[4]宋法刚,丁明.当下国产动画电影的文化景观与想象力消费[J].电影新作,2021,(01):100-105.
[5]林楠,吴佩婷.伦理叙事激发情感共鸣的机理探究[J].道德与文明,2019,(01):25-30.
作者简介:
马琳,女,汉族,河北邢台人,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