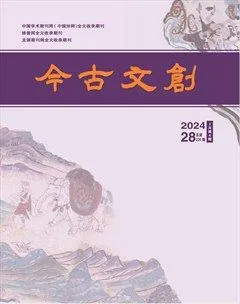电影《芭比》的女性主义解读
【摘要】真人电影《芭比》以幽默而不失讽刺的方式呈现了女性真实生存困境和性别身份焦虑,蕴含着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电影以女性叙事视角去构建故事世界,表达对于父权制的不满与抗争。同时,强调了女性互助作为成长的力量源泉,其中母女团结和姐妹情谊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女性觉醒与成长的最终归宿是要实现女性主义的平权目的,体现了对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芭比》;女性主义;女性意识;女性互助;平权思想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8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7
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大学2023年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后现代语境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重构”(项目编号:SLGYCX2333)。
《芭比》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在芭比乐园过着完美生活的芭比,突然发现自己身边接连出现不完美事件,意识到存在危机的她与肯试图前往现实世界探寻真相的故事。电影在叙事过程中深入探讨了父权制、女性主义等重要议题,能够启发现实中的人们对于女性意识、平权思想等内容的思考。
一、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所谓“女性意识”,似应包含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指影片编导或影片文本中应蕴含、具有和体现出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互敬互补的平权意识。二是指影片编导和影片本文不把女性形象作为男性的被动观赏对象,而是力求刻画和呈现女性自我的命运遭遇、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的形象塑造意识。两个层面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电影叙事意义上的女性意识。[1]电影《芭比》一方面从女性对于父权制社会的抗争出发,另一方面从女性作为第二性的肯的刻画与塑造出发,共同书写以芭比为代表的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对父权制社会的抗争
电影《芭比》不仅是一部关于玩具娃娃的奇幻冒险,更是一部对父权制社会进行深刻反思和抗争的作品。芭比所代表的女性的觉醒之路就是一条反对男性凝视、反对父权制的抗争之路。
电影的开场展示了完美无缺的芭比们日复一日的精致生活,直到某天芭比开始产生了死亡的意识,她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恢复到原来的生活,她和肯一起踏上了前往现实世界的旅途。而刚来到现实世界的芭比就明显感受到来自他者的凝视,她会认为打量的人不怀好意、另有所图。面对来自路边男人的骚扰,芭比因打人第一次进了警局,警察的反应却是“我超爱紧身衣”。芭比决定换身衣服,又因逃单第二次进警局,这一次警察的反应仍然是:“她穿得多了反倒更性感了”。不难看出,现实世界中的女性被多种角度地凝视是屡见不鲜的。
“凝视是一个物化过程,是对他者进行归纳、定义、评判的过程。被凝视往往意味着被客体化、对象化”。[2]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始终作为被男性欲望和权力统治的对象。在男性的凝视下,女性按照男权社会的惯例去构建女性应该有的样子,去迎合男性对于女性的标准,并且将这种观念内化为女性自我意识。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这只是基于男性凝视做出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只能存在于男性的凝视当中,是镜中的虚幻的“我”,而不是正确客观的主体性建立结果。因此,电影通过叙事努力打破这种对于女性的规训,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
首先,芭比作为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完美女性形象,其生活看似充满了选择和自由,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被限制和定义的完美循环。在芭比乐园中,女性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职业身份,从医生到记者,从建筑工人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是总统。这看似是对女性多元角色的肯定,但实际上却是对父权制下女性刻板印象的重现,女性真实的自我被忽略和压制。因此,芭比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规训面具的象征,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
其次,来自现实世界的萨沙及其母亲葛洛莉亚更是处于直面男凝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地受到规训。正如葛洛莉亚所指出的:“我们得保持身材,但又不能太瘦,还不能说自己想瘦,必须说是为了身体健康,但实际上还是得让自己变瘦;你必须有钱,但又不能张口要钱,否则你就是俗;既要强势,又不能咄咄逼人;既要承担领导责任,又不能压制别人的想法;既要热爱当妈,又不能整天把孩子挂在嘴边;既要事业有成,又要时时刻刻想着照顾其他人……”这是电影里最长的也是最经典的一段台词,它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
葛洛莉亚这番话也彻底点醒了陷入存在危机和被父权侵扰的芭比:“你指出了女性在父权制下产生的认知失调和要遵守的条条框框,让大家对父权制祛魅了。”至此,芭比们开始质疑肯乐园的现存秩序,挑战男性对女性赋予的期望。她们开始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自己的梦想,甚至颠覆了芭比乐园的既定规则。重新夺回芭比乐园这一过程展示了女性如何打破传统的刻板印象,解放自身思想,追求真实而独立的自我。这是一场温和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史,却也是对父权制有力的反抗。
(二)作为附庸的“肯”
波伏娃认为:“女性从来都是被建构的”。[3]而在芭比乐园中,男性才是被建构的。“芭比”们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女性群体,而“肯”们则代表了作为第二性的男性群体。肯的角色定位仅为芭比的男朋友,他们的日常都是围绕着芭比开展雄竞。肯的处境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女性在社会中常常受到的规训和限制。在芭比乐园中,肯的存在是衬托芭比的工具,没有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这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女性常常被限制在特定的领域和职责中,又或者只需围绕在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身边。
芭比乐园可以说是父权制社会的性转版缩影,而身处其中的肯同样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肯的存在于电影中成为对父权制社会的讽刺和批判,电影通过肯的视角揭露了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父权制影子。例如当肯意识到现实世界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社会时,他凭着男性的身份去一家公司谋职却遭拒,认为“你们这父权制显然搞得不太行啊”,对方却表示“我们这不但搞得好,现在还隐藏得特别好”,这段对话极具对现实世界父权制度的讽刺意味。当肯乐园的统治失败后,芭比劝肯哭出来,肯则说:“我又不是老顽固,我知道哭泣不等于软弱”以及“感觉当领导真是太难了,我一点也不想当”。显然,父权制对于男性也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在现实世界中,男性永远是成功、强大、勇敢等品质的代言人,而不被允许懦弱、失败,这同样是对男性的一种刻板印象。电影通过对肯的形象塑造和故事叙述,不仅显示了女性是父权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也反映了男性并非是父权制体系真正意义上的获益者,这显然是对女性主义的深入思考和对女性意识的深入挖掘。
此外,芭比与肯之间的关系重塑,也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随着思想的不断成长,芭比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被观赏和赞美的对象,而是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觉醒了的芭比意识到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因此她对肯道歉:“我不该把你视作理所当然”。受到芭比的启示,肯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和自身的存在意义,肯开始与芭比平等地对话。芭比与肯之间的平等关系重塑,不仅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成长,更是对平等的两性关系的深刻认识。
二、女性互助:女性成长的力量源泉
在电影《芭比》中,所有女性共同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彼此相互支持和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了各自思想上的成长。这种女性互助的力量和精神不仅让芭比等女性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和价值,也让观众对女性成长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
(一)母女关系:女性成长的重要前进动力
在电影中,女性成长始终与母亲紧密缠绕。《芭比》塑造了两对母女,即母亲葛洛莉亚和女儿萨沙、创始人露丝·汉德勒女士和创造物芭比。更重要的是,在两对母女的叙事中蕴藏着女性成长力量。
随着剧情的发展,可以清楚看到现实世界的母女葛洛莉亚和萨沙“共生——对抗——理解”的关系发展脉络。和母亲身体的亲密接触对于刚刚离开母亲子宫的婴儿尤其重要。生物学把这种亲密关系称为“共生(现象)”。[4]良好的共生关系建立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双方都能够从中受益,实现共同发展。
葛洛莉亚和萨沙初期处于一种共生状态。她们彼此依赖,母亲为女儿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支持,而女儿则依赖母亲的教导与爱护。这种共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的母女角色定位。随着萨沙的成长,她开始意识到个体独立性,不愿被传统的母女关系束缚。但在传统的母女关系定位中,葛洛莉亚一直竭力满足作为母亲的要求,而女儿的反叛与独立却让她一方面陷入未尽母职的焦虑,另一方面则是似乎要与女儿分离的恐慌。在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之下,葛洛莉亚和萨沙就形成了压抑、紧张的对抗关系。
但萨沙勇敢地决定回到芭比乐园并拯救其他芭比,成为推动母女关系发展的关键剧情。在拯救芭比乐园的过程中,葛洛莉亚开始了解萨沙的内心世界,意识到她作为年轻一代的女性,追求的是独立的自我。同时,萨沙也逐渐理解葛洛莉亚身为上一代女性的困境和无奈。至此,葛洛莉亚和萨沙开始产生精神共鸣。她们都渴望被理解和接纳,都希望能够追求真实的自我,进而传统母女关系转变为新型母女关系——萨沙和葛洛莉亚都首先作为一名独立女性而存在,她们相互理解和扶持,以一种更平等、更尊重的方式相处,以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团结一致,共同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芭比与“芭比之母”露丝·汉德勒对于存在问题的讨论也为母女关系的现存问题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影片落幕之际,露丝出现并为芭比解答她关于存在上的困惑——芭比成为独立的个体的关键,是与母亲建立一种适度割裂的关系。正如芭比问露丝:“您允许我成为人类吗?”露丝的回答则是:“你不需要我的认可”。“作为母亲,我们等在原地。当女儿回头望时,她们就能看到自己走过的漫漫长路”这句出自露丝的话不仅指向了母女的个体独立,更隐喻了女性主义的发展始终是温和而坚定地在前进的。
(二)姐妹情谊:女性互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姐妹情谊”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理论术语[5],意指“女性间息息相关的意识与体验,是通过女性中心的视角对女性的定义而产生的对自身的认同及肯定”。[6]由于女性独特的身体和心理结构,同为女性的她们更能理解彼此的遭遇,互相支持、鼓励,进而建立起具有正面意义的姐妹情谊,而这是推动女性主义发展的关键力量。
故事的主线围绕着芭比寻找她的玩伴人类葛洛莉亚展开,这个过程中,芭比与葛洛莉亚、萨沙、露丝以及怪咖芭比等角色之间的团结互助推动了女性主体的建构,唤醒了女性的思想独立和身份认同。对萨沙而言,芭比在她心目中最初便是使女性运动倒退的罪魁祸首,但在与芭比的相处中其观念逐渐改变。面对放弃挣扎的芭比,正是萨沙决定要原路返回,去拯救芭比乐园和芭比。对葛洛莉亚而言,在其成长时期芭比还未受到广泛批判,芭比于她不仅仅是一个玩具,更是她亲密的朋友,在她失意时赋予她力量。当芭比陷入迷茫和困境时,葛洛莉亚用她坚定而有力的话语唤醒了芭比的女性意识,并用同样的方式拯救了所有芭比。女性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和鼓励,用自身智慧和经验推动了女性主义运动的进行。
怪咖芭比的行为在女性成长的道路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怪咖芭比作为一个不完美的芭比,有着强烈的独特性和个性,她始终自信地展示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并不依赖他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为被父权制洗脑的芭比们乃至女性群体都提供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激励女性追求真实的自我,接受不完美的自己。露丝女士同样表达了这个观点。面对喝茶的芭比,露丝感叹她变了,芭比解释:“现在是特殊情况,我平时是很完美的。”露丝笑着说:“也许是吧,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就很好。”在姐妹情谊的照耀下,女性主体性的崛起与成长变得愈发明显,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
三、理想归宿:以“雌雄同体”为内核的平权思想
米利特在《性政治》中阐述:“两性之间的关系处于支配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意识形态,并且男权社会总是通过家庭、学校、教堂、法律等等来维护这一意识形态。”[7]无论是芭比乐园还是肯乐园,都是父权制的产物,都维护以从属和支配为主的两性关系。电影正是通过批判父权制进而表达以“雌雄同体”为核心的平权思想。
“雌雄同体”的心灵是对性别二元对立的一种解构和超越,打破两性之间的支配和从属关系,进而挣脱性别和思想的枷锁,最终实现平权主义。伍尔夫将“雌雄同体”的心灵状态阐释为:“唯有两性的力量和谐相处,于精神相辅相成,心智才会处于正常、安适的状态。即使身为男性,心智内的女性部分依然发挥作用;女性亦然,一样要和她大脑内的男性部分交流。”[8]在“雌雄同体”的心灵中,男性与女性的思维和力量应当是平等、和谐的,能够超越现实中两性所暗含的狭隘和斗争,最终在一种男女都能达到的和谐共鸣的境界中得到解放。
关于“雌雄同体”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执行者显然是艾伦,他也是电影中被父权制忽视和排挤的独特存在。艾伦这个角色代表了一种超越性别的价值观。他既不受限于男性或女性的刻板印象,也不为了证明自己而迎合或反抗社会期待。他只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生活方式,从始至终都在追求一个真实的自我,他既可以展现温柔和细腻,也可以展现勇敢和强悍。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从思想到行为上挣脱于性别束缚、进而达到“雌雄同体”状态的角色。
只有拥有了“雌雄同体”的心灵,人们才能真正跳出性别圈子,男性和女性才能拥有平等的人格和权利,实现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平权。就像芭比原本认为肯应该作为她们的附庸而存在,在接受到个体独立和平等的思想后,她认为肯应该去探索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而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追求真实的自我。
从中也能够透露出女性主义所要达到的最终归宿——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努力将男权社会转变成女权社会,女性成为强者而男性成为弱者的思想。女性主义是希望女性能够跳出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圈,发现独立的自我,建立女性的话语权。同时,能够平等尊重地对待社会上相对的弱者,让每一个都拥有平等的人格和权利,让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显杰,修倜.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J].当代电影,1994,(06):28-36.
[2]金莉,李铁.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美)南希·弗莱迪.我母亲我自己——女性独立与性意识[M].杨宁宁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5]刘亭.镜像与凝视: “她剧集”的女性叙事新视角——以电视剧《三十而已》为例[J].中国电视,2020,(12):95-99.
[6]谭兢嫦.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7]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8]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宋伟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