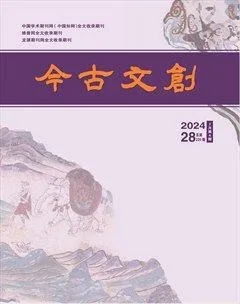郭象《庄子注》与王夫之《庄子解》相同词句注释的比较研究
【摘要】郭象的《庄子注》与王夫之的《庄子解》在解庄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庄子注》和《庄子解》不仅是《庄子》思想的阐释之作,也是宝贵的训诂材料,有待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字词注释的角度出发,针对《庄子注》与《庄子解》中对《庄子》文本的同一词句的相同注释或相异注释,尝试比较研究,并结合《庄子》文本进行探讨与分析,揭示王、郭二人各自注解的合理之处。
【关键词】《庄子》;《庄子注》;《庄子解》;注释;对比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7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4
基金项目:202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王夫之〈庄子解〉与郭象〈庄子注〉训诂对比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202310555106)。
《庄子》,又称《南华经》或《南华真经》,恢诡谲怪,风云开阖,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及其后学写就,分为内、外、杂篇三个部分,共计三十三篇,其内容涉及人生、社会、哲学等多个方面,具有杰出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郭象,西晋时期玄学家,彼时政局混乱,老庄之风盛行,出现了许多注庄者,而郭象的《庄子注》一书,清辞遒旨,以寄言出意的方式阐发义理,后又有唐代成玄英为之作疏。王夫之,明清之际颇负盛名的哲学家、诗人,与黄宗羲、顾炎武、唐甄三人并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庄子解》为其晚年解庄之作,体系成熟,“以庄解庄”,思想广博,捭阖自如。郭、王二人对《庄子》的注解内容既有相似之点,亦有不同之处。本文对《庄子注》与《庄子解》中同一词句的异同注解进行发掘,尝试做出分析与探讨,或有利于对《庄子》文意更深一步的解读与领悟。
一、对同一词句的相同注释
《逍遥游》:“之二虫,又何知!”
《庄子注》:“二虫,谓鹏蜩也。”
《庄子解》:“郭象曰:‘二虫谓鹏蜩也。’”
按:“之二虫,又何知”,当下较为通行的理解是:蜩与学鸠又哪里会知晓呢,其中“二虫”即指“蜩与学鸠”。而在《庄子注》中,郭象却将“之二虫”释为“二虫,谓鹏蜩也”,王夫之亦遵从郭象的注解,直引郭象之言。成玄英疏:“且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远近,各取足而自胜,天机自张,不知所以。既无意于高卑,岂有情于优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可见,对于“之二虫”究竟指代哪两种对象,从郭象“二虫,谓鹏蜩也”的注、唐代成玄英的疏,再到王夫之对郭注的直接引用;从彼时的“二虫,谓鹏蜩也”到今天的“蜩与学鸠”,似乎已生出较为明显的差异。依郭象之说,“之二虫,又何知”或可做此番理解:“何知”即“无知”,指鹏与蜩虽然飞行的距离远近不同,但都遵从着其自身的自然本性,二者都处在一种无知的无意识状态。而无论是鹏还是学鸠,又都可以指称为“虫”。然而,相比于“蜩与学鸠”之说,郭象“鹏蜩也”的注解或失之偏颇。《逍遥游》一篇,讲的是人应该超越外在功名利禄的桎梏,从而达到内在精神逍遥无碍的自在之境。文中首先展现了一个浩荡广博的奇特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于乘着大风展翅飞行九万里,背负青天而无所窒碍,准备飞向南海的鹏,蜩与学鸠却发出讥笑:“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而对于适莽苍者、适百里者和适千里者,他们目标不同,路程不同,所需准备的粮食的分量自然也不相同。抢榆枋而止的小蝉与小鸠不明白大鹏为何要乃今而后图南,不懂得脚程不同,所需准备的餐食的分量也不相同这样的道理,往近处飞的不能理解向远处飞的,即小知不及大知也。故从蜩与学鸠的何知可引发下文的“小知”“大知”,再引出“小年”“大年”,从而展开“此小大之辩也”的论述,语意连贯,逻辑自然。对于郭象所注的二虫谓鹏蜩也,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的俞樾先生认为“此恐失之”,二虫所指应为蜩与学鸠。依俞樾之见,后文说“奚以知其然也”,朝生而暮死的小虫哪里能懂得何为一月,只能存活一个季节的小蝉哪里能明白何为一年,说的都是小知不及大知的“不知”,故云“之二虫,又何知”,“其谓蜩、鸠二虫明矣”。可见“二虫”作蜩与学鸠解甚具其理。
二、对同一词句的不同注释
(一)《逍遥游》:“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
《庄子注》:“冥灵大椿,并木名也。”
《庄子解》:“冥灵,冥海灵龟也。”
按:对于“冥灵”一词,王夫之认为其指的是“冥海灵龟”,郭象则将其注释为“木名”。《说文解字》中说:“冥,幽也。从日从六,冖声。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莫经切。”《广雅》:“冥,暗也。”“冥”之本义为幽暗《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中的“其庙独冥。”“冥”字在此处便是指幽暗之意。再看“灵”字,《玉篇》:“神灵也。”《大雅·灵台传》中说:“神之精明者称灵。”“冥灵”,本来自于神话传说,而非实际所有,并非存在于现实世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六·庄子音义上》:“冥灵,木名也。江南生,以叶生为春,叶落为秋;此木以二千岁为一年。”将“冥灵”作为一种树木来记述。三国阮籍《咏怀诗》中也有“焉见冥灵木,悠悠竟无形”之语,“冥灵”作为木名的接受情况或较为广泛。郭象将“冥灵”与“大椿”两者归于一类,皆作长生之木来进行阐述。而在《逍遥游》中,除“冥灵”外,亦有“北冥有鱼”“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等语,皆以“冥”指称海。《正韵》指出,“通作溟。”故“北冥”即是北海,“南冥”即指南海。南宋末年时期的罗勉道的庄学著作《南华真经循本》中有不少名物训诂,其中就有提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可见,“冥灵”者,所指代的可能就是冥海灵龟。故虽两注各有其合理性,但从对原文语境的理解下出发,王夫之将“冥灵”作“冥海灵龟”注解或更有其理。
(二)《达生》:“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汨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
《庄子注》:“磨翁而旋入者,齐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
《庄子解》:“齐、脐通,水之旋涡如脐也。汨,水滚出处也。”
按:《说文解字》:“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凡亝之属皆从亝。徂兮切。”《说文解字注》:“从二者,象地有高下也。引伸为凡齐等之义。古叚为脐字。亦叚为脐字,徂兮切。十五部。凡齐之属皆从齐。”“齐”通“脐”,有中央之意,如《列子·黄帝》:“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齐”通“脐”,又指肚脐,如《左传·庄公六年》:“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庄子解》对《达生》中“与齐俱入”之“齐”的注解是“齐、脐通,水之旋涡如脐也”,此为王敔的增注。其意指漩涡的中心处状似肚脐,比喻可谓生动。而《庄子注》中说:“磨翁而旋入者,齐也。”是说石磨的中心,即连接上下扇的地方叫作“脐”,漩涡中水流回旋,正如石磨一般,故将漩涡的中心处称作“脐”。唐成玄英也疏曰:“湍沸旋入,如磴心之转者,齐也;回复腾漫而反出者,汨也。既与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齐汨,曾不介怀。郭注云磨翁而入者,关东人吹磴为磨,磨翁而入,是磴釭转也。”回到《达生》,此篇的主旨为重视人的精神作用,以臻于生命畅达之境。在《达生》的第九个寓言中,记叙了孔子及其弟子在吕梁游玩时所遇之事。孔子与弟子们观赏瀑布,瀑布高悬,水势浩大,激流汹涌,连鼋鼍鱼鳖这样的水生生物都不敢在这附近游水,但却看到一名男子游泳其中,以为他是因不堪遭受磨难苦厄的折磨而寻短见。于是孔子赶紧命弟子顺着水流去救下那人。而那男子却等过了好几百步才从水面浮出,披着头发,唱着歌,一边游至岸下。孔子惊异于那游水者的非凡的水性与本领,询问其蹈水是否有道,即游泳的窍门与方法,而游水者却回答说“吾无道”,之所以能在水中练就如此本领,只因其起初源于故常,长大后依从习性,再顺从自然之理达到有所成之境。对于三个阶段,可见唐成玄英疏,先是其“初始生于陵陆,遂与陵为故旧也”;再是“长大游于水中,习而成性也”;最后“既习水成性,心无惧惮,恣情放任”,于是达到“遂同自然天命也”之化境。而“与齐俱入,与汨偕出”之“齐”,便是指漩涡中心,游水者从漩涡中心处下潜至水底,又随着涌出的漩涡一起上游到水面。无论是《庄子解》中的“齐、脐通,水之旋涡如脐也”,还是《庄子注》里的“磨翁而旋入者,齐也”,都指的是漩涡的中心处,故王、郭两注均合理。
(三)《外物》:“其不殷,非天之罪。”《庄子注》:“殷,当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后失当,失当而后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庄子解》:“殷,盛也。”
按:《说文解字》:“殷,作乐之盛称殷。从㐆从殳。《易》曰:‘殷荐之上帝。’”《说文解字注》中说:“作乐之盛偁殷。此殷之本义也。如易豫象传是。引伸之为凡盛之偁。又引伸之为大也。又引伸之为众也。又引伸之为正也、中也。”可见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殷,盛也”之注释与“殷”字的本义一致。《说文解字》:“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从皿成声。氏征切。”“盛”的本义是指古时候放置在用于祭祀的器物中的谷物,如《周礼·地官·闾师》中的“不耕者祭无盛”之“盛”。而此处的“盛”或作兴盛之意解,同《论语·泰伯》中言,“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中的“盛”。结合文意,可以看到在《外物》中有这样的论述:“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文中将眼睛、耳朵、鼻子、口舌、心灵、智慧的灵敏状态分别称作“明”“聪”“膻”“甘”“智”“德”。“凡道不欲壅,壅则哽,哽而不止则跈,跈则众害生。”凡是道都不愿被壅滞,一旦壅滞便会导致梗塞,梗塞如果不能停止便会生出乖戾,乖戾的猖獗则会招致祸害。“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有知觉的事物依靠的是气息,倘若气息不盛,那并非是天性所导致的,故绝不可归咎于自然。“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自然之理,贯穿于世间种种事物,日日夜夜也不曾停息,但人们却堵塞自己的窍孔。正是因为人们没有顺应自然,影响了气息的生发,从而导致气息不够强盛,故王夫之对此处“殷”的注解符合文意。而唐成玄英疏:“殷,当也。或纵恣六根,驰逐前境;或窍穴哽塞,以害生崖;通蹍二徒,皆不当理。斯并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郭象将“殷”解释为“当也”,亦有其理。
(四)《则阳》:“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庄子注》:“所谓玄通。”
《庄子解》:“《循本》曰:绸缪,事理轇轕处。唯圣人为能达之。”
按,在《则阳》篇中,此处文段之旨为言说圣人之心态。对于“绸缪”一词,《说文解字》有言:“绸,缪也。从纟周声。直由切。”《说文解字注》:“缪也。谓枲之十絜、一曰绸缪二义皆与缪同也。”《广雅》中说:“绸,缠也。”“绸”为形声字,本是缠绕之意。《说文解字》中有“缪,枲之十絜也。一曰绸缪。从纟翏声。武彪切。”《说文解字注》:“缪,一曰绸缪也。唐风:绸缪束薪。传曰:绸缪犹缠绵也。鸱鸮郑笺同,皆谓束缚重叠。”《诗经·豳风·鸱鸮》有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传曰:“绸缪,言缠绵也。”王夫之引用了《循本》中“绸缪,事理轇轕处”的说法。“轇轕”为纵横交错之意,则王夫之对此处“绸缪”的解释即为事理复杂纠葛,这样的纠缠事理令人难得自在;而“达绸缪”,便是指圣人对世间复杂事理的认识处于一种通达状态。郭象的注解是“所谓玄通”。《老子》有言:“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河上公注:“玄,天也。言其志节玄妙,精与天通也。”可见,郭象对“达绸缪”之意的解释或为:与天道相通达。唐成玄英疏云:“绸缪,结缚也。”他解释道:“夫达道圣人,超然县解,体知物境空幻,岂为尘网所羁!阅休虽未极乎道,故但托而说之也。”圣人贯通天道,将普遍之万物合为一体,但并不知悉其中的所以然,只是出自他的本性啊。可见郭象与王夫之二人各自的注解均合乎文意。
(五)《天道》:“而口阚然。”
《庄子注》:“虓豁之貌。”
《庄子解》:“气盈,常若欲言。”
按:对于“阚”字,《说文解字》中说,“阚,望也。”《说文解字注》:“望也。望者,出亡在外,望其还也。望有倚门、倚闾者。故从门。”《集韵》:“兽怒声。”“阚”指虎啸之声。在《庄子注》中,郭象对“阚然”的注解是“虓豁之貌”。而“虓”在《说文解字》中的注解为“虎鸣也。一曰师子。从虎九声。许交切。”《说文解字注》也说:“虎鸣也。大雅:阚如虓虎。毛曰:虓虎,虎之自怒虓然。按自怒犹盛怒也。口部曰:唬,虎声也。虓与唬双声同义。从虎九声。”《诗经·大雅·常武》中云:“进厥虎臣,阚如虓虎。”毛传:“虎之自怒虓然。”《天道》一篇,主要阐述的是自然之义理。篇中,士成绮见到了老子,却出言讽刺:“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说自己听闻老子是圣人,于是不辞艰辛,远道而来,脚上生了厚厚的茧,希望能得见老子。见面之后,却说“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有余蔬而弃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但老子却漠然无应,并未作答。第二天,士成绮又来询问老子,说自己昨日讽刺了他,今日又心有所悟,这是为什么呢?老子说士成绮是“虓豁之貌”,即形容士成绮言语之专横粗暴。王夫之的注解“气盈,常若欲言”,则是说士成绮嘴巴虚张,好像将要说话一样,亦显其性格之特征,同时也契合后文老子对士成绮“似系马而止也”的生动形容。可见,郭象与王夫之的注解虽有不同的意义侧重点,然皆符合文意。
综上,通过比对王夫之的《庄子解》与郭象的《庄子注》,针对两书中部分相同词句的不同注释或同一注释,分析其间异同,或可帮助读者进一步厘清《庄子》文意,理解其中历久不衰的深刻蕴含。此外,在王夫之的《庄子解》与郭象的《庄子注》两书的注解中,仍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有待更深入的挖掘与探讨。
参考文献:
[1]郭芹纳.训诂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3]路庆兰.王夫之《庄子解》文献研究[D].鲁东大学,
2018.
[4]彭再新,彭粤珊.王夫之《庄子解》用字注释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04).
[5]彭再新,周霞.王夫之《庄子解》语法观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04).
[6]王夫之撰,王孝鱼点校.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64.
[7]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华书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