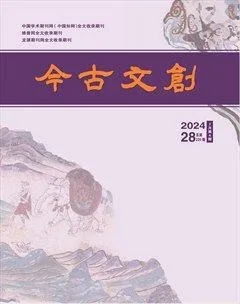哲学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及统一
【摘要】《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指出德国哲学似乎具有偏离现实的倾向。德国哲学抽象的形式和思辨的内容受到当时人民的指摘,但事实上真正的哲学是时代和人民的产物,哲学始终是对现实世界作出的带有自身特色的反映。马克思看到德国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具体内容与抽象形式间的对立,并指出德国哲学形成如此的局面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马克思在对海尔梅斯的批判回应中,为德国哲学面临的困境找到合适的出路——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
【关键词】哲学;《科隆日报》;马克思;德国哲学困境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6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2
1842年,《科隆日报》的编辑卡尔·海尔梅斯(Karl Hermes),作为一位保守的天主教徒和政府代理人,他在该报第179号上撰写了一篇社论向政府告密,指责《莱茵报》和《科尼斯日报》非法刊登一些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文章,质疑这些报刊的政治立场,认为他们存有攻击基督教和普鲁士政权的嫌疑。对此,马克思于1842年6月28日至7月3日写下《〈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以下简称《社论》)对海尔梅斯作出回应,揭露《科隆日报》的虚伪面貌。马克思在反驳海尔梅斯的同时,表露出对哲学与时代问题的独特思考和集中探讨。尽管整篇文章的字数不多,但马克思在其中展现了德国哲学遇到的二律背反问题:一方面,哲学不同于宗教神学,始终接触时代,是现世的智慧;但另一方面,哲学本身保持着自身的历史特点,具有不可忽视的思辨性和抽象性。面对哲学具体内容与抽象形式的对立,马克思坚定维护哲学的话语权,提倡人民自由的理性。
一、哲学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展现
在《社论》这篇短作中,马克思论及了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哲学是否应在报纸的文章里探讨有关宗教事务的内容?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只有批判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出答案,而在批判此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阐述了自己对于哲学本性的理解以及哲学与世界关系的看法。马克思在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时,看到了德国哲学(实际上指代更确切意义上的德国古典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当哲学受到时代的非议和来自报刊的否定时,马克思坚定地拿起理论的武器,对哲学真正内容和具体形式的关系展开了探析。
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存在着脱离现实的倾向。首先,德国哲学具备其自身特色,即追求体系的完满。正如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他们一味强调要构建庞大圆满的哲学体系,致力于理性法则的自我展现。长期抽象的哲学讨论中贯彻着脱离现实的形而上概念和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关系,德国古典哲学家所探讨的似乎总是形而上的内容,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构造和体系总是抱持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屑态度。因此,德国哲学基本不参与讨论现实政治,始终以一种旁观的目光注视社会。其次,德国哲学按照其体系的发展进步来看,始终是晦涩难懂的,因为哲学所讨论和使用的概念内容似乎总是超脱于现实之外的形而上学。如此一来,哲学自身的演进变化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总是不切实际的,“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1]219。
哲学自身的抽象性质使得人们对此常常退避三舍,而德国哲学愈演愈烈的思辨性也将哲学与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并且,哲学始终也没有尝试把“禁欲主义的教师长袍”变成和报纸一样的轻便服装,他们摒弃肤浅简单的言论,着力于采取喃喃自语的方式去阐述真理,哲学始终拒斥轻便的方式讲述内容,因为哲学本身的内容正是如此的晦涩和抽象,一旦采取极为下里巴人的论述形式,那么哲学探讨的内容就很难叙述清楚。哲学探讨的抽象内容规定了哲学的论述方式亦是如此,马克思也为之辩护道,哲学本身,一定不会如报纸一般如此迅速且充满激昂地讨论时事,海尔梅斯以报刊的方式去要求哲学改变路径显然是不合理的。
然而,尽管德国哲学有些固守传统,但其哲学始终是时代和现实的产物。马克思看到了哲学的本性,指出哲学的现实性,哲学是和现实相互作用的。哲学是对现实的反映,尽管不是对现实简单直接的反映。哲学不是悬置在世界外部,它所观照的正是这个现实世界。只不过不同于其他领域,哲学是理论展现早于实践活动。马克思强调哲学并不是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好似漂浮于世界现实之外,哲学拥有其现实性,不能因为哲学与宗教神学或其他学科采取的叙述方式不一致就断然否定其现实性。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偶尔跳出了黑格尔的哲学视野,黑格尔关注哲学的反思性和后发性,而马克思则侦察到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引导性,哲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立足于现实,也同样对现实具有批判的反作用。马克思阐述哲学具体内容与现实的不可分割性,因为哲学总是透视时代脉搏,抓住时代中各种运动和事件的集中表现,从而对时代现实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哲学的具体内容与抽象形式是不可对立而语的,二者是统一、相互尊重的,正是其思辨的内容规定了抽象的形式,而思辨内容的实质是对具体世界本身的超越性探析。回到马克思在《社论》中所研究的这个问题,马克思强调哲学是由于时代的要求而进入世界的,哲学当然拥有在报纸上对于此岸世界内容的发言权,这是源自哲学对于现实的深切观照和体察。
至此,哲学的具体内容与抽象形式间的矛盾便昭然若现。一方面,以往的德国哲学始终带着浓厚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而显得高高在上;另一方面,哲学的内容本性要求哲学必须对现实世界做出反应。由于黑格尔本人和青年黑格尔派始终保持哲学的晦涩特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纯粹理论的批判运动,加之当时普鲁士政府对于思想自由的强烈限制和打击,当时的哲学家不得不采取更为晦涩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免受到政府的攻击。如此一来,德国哲学的内容便愈加晦涩抽象,在人们眼中的哲学似乎始终是一种彼岸的思想,那么人们对哲学形成的误解和责难便情有可原,其晦涩抽象的形式使人们很难理解并把握其核心的思想要旨,只是浅于表面便断然抛弃。何况由于当时公众对宗教神学思想采取的是极为坚定的信仰态度,以至于哲学更被弃之边缘角落。但德国哲学形成如此的困境是当时社会的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彼时公众对于哲学的态度也是当时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所导致的。
二、哲学内容与形式的对立源头
马克思对哲学的话语权问题十分重视,但哲学之所以在当时的公众面前被束之高阁,除了哲学自身孤寂和晦涩的特点之外,也有时代背景的因素。回到《莱茵报》时期的社会环境,德国落后的社会状况以致对哲学自由发言的打压,神学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性对哲学的威胁,德国官方政治对共产主义新思潮的极致性管控,种种因素导致德国哲学受到人们的摒弃和责难,德国哲学继续发展的道路极其艰巨。马克思犀利地发现哲学具体内容与抽象形式间的对立问题,并试图对此进行调解、找寻二者统一的路径。但找寻问题的解决之路必须要回到问题的发生之中,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哲学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困境,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思想环境息息相关的。
首先,德国在19世纪40年代时期的经济政治状况是十分落后的。1840年前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工业革命之风迅速向整个欧洲大陆传播。然而当时的德国是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属于各种分散的城邦,工业革命面对极大的挑战,并未形成庞大的规模。德国在19世纪初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大工业生产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在国际贸易上也受到大西洋沿岸国家的排挤。而19世纪30-4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资产阶级力量非常之小,不仅受到封建统治势力的打压,也受到无产阶级的挑战。总体上,当时德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如意。而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0年登基,这位颇为保守的国王屡屡镇压自由新兴的改革,并且强烈抵制资产阶级的新兴力量,试图进行历史的复辟。这对于当时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是种无比巨大的阻碍。实际上德国的保守主义派仍然把握德国主要的话语权,他们始终强调社会内在稳定不变的固定秩序,很大程度地限制资产阶级和新兴思想的发展,国家陷入专制主义的死亡喘息之中。德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对抗不了封建传统的保守派,统治权力大部分始终是为保守派所把持,而为了让沉重腐朽的国家继续苟延残喘,保守派禁锢自由思想的发展,企图以基督教控制人民大众的思想。正如《社论》中海尔梅斯站在基督教会的立场上,反对《莱茵报》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
其次,在19世纪40年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所参与的主要舆论内容就是神学,因为宗教是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而“神学塑造了人们最深层的信仰体系与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方式”[2]。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无法将宗教与政治完全地分离开,哲学不可避免地会讨论宗教与神学,而对于公众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言,当时的宗教神学领域是处于“和物质需要的体系几乎具有同等价值的唯一的思想领域”[3]221。因此,马克思无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宗教神学的言论,但马克思始终是为哲学正名,强调哲学生于时代和人民之中,它虽然保持原本的抽象思辨性质,但是对现实问题,哲学并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哲学是哲学家对于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这种哲学成果带有必然的思辨性,尽管不是远离人民和时代的思辨性,但这种不可避免的思辨性在公众眼里就是无法触及的内容。而相反,宗教抓住人民的温情心理,利用这种可悲的心理去发展自身思想,给予人们来世的安慰。这样一来,在不了解哲学本质的思想背景下,为了追求未来天堂的或者将来人间的享受,大多数无知的公众都会选择臣服于教会的长袍。神学教会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势必会普遍地将利爪指向其敌人——哲学。于是,当社会的目光都固定在宗教神学之上,那么哲学这个无比思辨的内容就被置于冷板凳之上。
除此以外,德国当时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在德国思想界疯狂蔓延。1830年左右,法国共产主义思想传入德国,尽管一直处于十分边缘的状态。因为此时的德国依然沉浸在虔诚主义复兴中,他们陷入对新约和福音书的激烈论战,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耶稣形象的争论激化了当时宗教与政治的矛盾,德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出现纷争。但与此同时,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不断传入德国,而赫斯对于德国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理论联系的推进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除此以外,《莱茵报》时期,卢格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著作对于马克思关注现实政治以及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都有着催化作用。马克思在《社论》中多次提到费尔巴哈,马克思指出人们当时对于费尔巴哈的责难更多的是源于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的宗教方面,强调当时人们反对哲学的原因并不具备合理性。尽管此时的马克思大部分是处在黑格尔理性主义思想的笼罩下,但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和费尔巴哈等人对其的影响也展露在《社论》的一些观点中。比如马克思始终站在哲学的角度,指出当哲学“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时,哲学首先反对的就是宗教,因为宗教本身是非理性的异化。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判指责,以及对于无神论者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的维护,也侧面展现出当时马克思思想所受的多重影响。
因此,德国哲学之所以出现具体内容与抽象形式的对立困境,与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环境具有极大的关联,德国民众对于宗教神学的大肆信仰,德国资本工业经济的严重落后,德国政治国家对于宗教的官方推崇,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以及法国共产主义等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这些共同致使马克思察觉到德国哲学所面临的困境。面对德国哲学出现的困境,在当时《社论》的社会背景中:黑格尔总体性哲学体系的崩塌,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演进,以及政治官方对于哲学言论自由的管控,社会各种思潮的交织等等,马克思试图为德国哲学的困境寻找一条出路,探析哲学与现实的本质关系,强调哲学与现实的统一。
三、德国哲学困境的出路
受当时具体时代环境的影响,德国哲学受到无数来自人们和报刊的误解和责难,海尔梅斯就此指责哲学不应该甚至没有合法权利在报刊上探讨有关宗教的事务,并认为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哲学观点极易造成社会的混乱。马克思在对海尔梅斯的回应中,辨明了德国哲学本身的对立问题,并深化其博士论文中的思想和观点,试图对德国哲学内容与形式的对立找寻统一的路径。
面对德国哲学具体内容与抽象形式的对立,马克思指出了德国哲学的出路,即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到了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指出哲学世界化与世界哲学化。马克思强调哲学必定会走向现实,因为哲学作为一种理论,首先就是批判。理论阐述的是一种规范性的原则体系,但现实往往不符合规范性的设想原则,两者之间必定存在鸿沟和差异。但马克思坚定地强调,“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220。哲学在确定一种规范性的维度之后,必定会向现实过渡。哲学在与世界的接触中,哲学会影响世界甚至会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因为哲学作为一种理论的内在之光,它必定要渗透到外部世界之中,去吞噬一切不合理的成分,哲学通过把原则贯彻到外部现象事物之中去实现自身。但正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阐述的那样,“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5]76。在哲学与世界的接触过程中,哲学丧失了其自身的抽象性,其作为纯粹思辨理论的特色随之丧失。因为在哲学未与世界结合之前,哲学本身是极为抽象的。哲学唯一消除自身内在缺陷的方式就是与现实世界发生作用,如此一来,哲学不得不完善自身,其自身原本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就将被打破,丧失自身的抽象性。而通过哲学的世界化,使得人们易于透过哲学的晦涩和孤僻的形式,而看到哲学内容中包含的时代特性和规律特性,以此不再对哲学产生畏惧心理。不同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其是一个抽象的思辨总体,强调一种内在于世界之中的支配性原则即理性的力量。然而黑格尔的哲学始终是漂浮于现实世界之上,马克思则强调反思的力量,看到理论体系与现实状况的差异。因为按照理想性的原则,哲学与世界是统一的,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此,只有当哲学进入现实之中,才能够消除其自身与世界不统一的缺陷。所以黑格尔学派解体之后的自由派和实证派无非只是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哲学与世界的统一关系,割裂了实践与理论的一致性,最终造成自我意识的分裂。
哲学的出场是在敌人的叫喊声中被迫显露,因为哲学的本性仍然是站在在理性自主的前提上审视现实,这表明哲学在与现实进行结合的过程中,尽管会丧失自身的抽象本性,但并不是说要抛弃自身的本性。在《社论》中,马克思尤其强调“当代的真正哲学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与过去的真正哲学有所不同”[3]221。哲学在抓住实现的同时始终保有其特色,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思辨性不能被彻底抛弃,虽然长久以来德国哲学采取沉默的方式面对报刊的肤浅语调,但哲学曾经拒绝对报纸的使用是因为报纸不符合哲学本身的特征,而以往的哲学家喜欢宁静和冷静的自我审视,他们厌恶世俗的自吹自擂,追求思想的严格推理。所以即使哲学在与世界进行接触之时,哲学丧失自身的同时也不会彻底与世俗其他学科同流。因为哲学是哲学家对于时代和现实的苦思冥想、耗尽心力的成果。哲学的研究内容和形式要求决定了哲学的成果始终具有孤僻性和晦涩性,但这不是代表哲学将远离时代和人民,哲学的思辨和抽象只是形式的必然,哲学虽然从未考虑过抛弃自身的形式特征,但哲学始终是关注时代和人民的,哲学试图立足现实构建理性的法则,并以哲学成果去指导世界。
马克思对德国哲学面临问题的展开以及解决路径的阐述C4C1l4/5W49K1m3/O5hOEw==回应了当时人们对哲学所形成的误解,使人们明晰了哲学的真正内涵。哲学始终是观照现实的,以现实内容作为反思的对象,尽管采取抽象的形式,但这正是哲学本身不同于报刊等简易理论的最大特征。哲学晦涩的形式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就始终高高在上,只论及超出现实世界以上的形而上学问题,相反,哲学只是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和概念上升性地讨论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是马克思从书斋进入尘世的政论性文章之一,彼时马克思还深受黑格尔法哲学观点的浓厚影响,其思想处处彰显着黑格尔的印记。在这篇文章中,当马克思谈及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时,仍旧是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笼罩下的成果。然而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时期,就已经展露出不同于黑格尔的部分哲学观点,这表现在马克思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后期在《莱茵报》时期正是深化了其博士论文时期对于哲学与世界关系的看法观点,超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局限。除此以外,黑格尔主张国家的合理性依据,认为哲学不应在报纸上谈论和发表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本身的独特性要求哲学的论述方式就不同于报刊。但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指出哲学与世界的相关性,揭示哲学的真正本质,提出哲学应回归现实生活,实现哲学的世界化,而我们对世界本身的探讨也不应拘泥于具体时代和现实问题,必须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去发现和总结规律,实现世界哲学化。当然,哲学在下降到现实世界时,始终秉持其抽象的形式特点,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就不同于报刊等行业,哲学谈及的内容本身就是以形而上的形式所呈现,对此的责难是对哲学本质的误解。
总之,长久以来,德国哲学始终以其抽象思辨性著称,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曲解,认为德国哲学存在着脱离现实的倾向。为此,海尔梅斯对《莱茵报》上刊登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思想文章的行为十分不满,指责哲学不应该在报刊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利用此次契机,马克思通过对海尔梅斯的回应和反击,捍卫了哲学的言论自由权利,明确指出哲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但针对德国哲学所面临的抽象形式与具体内容之间的对立问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寻找到德国哲学的出路,即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哲学始终是对现实做出的带有自身思辨特征的反映,哲学体系也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规范性原则。为实现哲学与世界的统一,必须以哲学的方式干预和影响现实,并在实现哲学自身的同时丧失其抽象性,最终实现二者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9.
[2](澳)罗兰·玻尔.尘世的批判——论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M].陈影,李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4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6.
作者简介:
江燕君,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