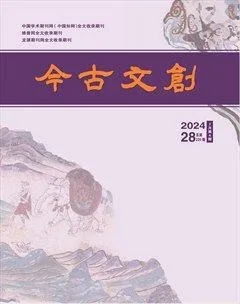从心物关系看刘勰《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从对于万物的感悟开始,将“道”的自然规律应用于“文”,以“自然之道”贯穿文学思想。从为文之用心与创作之用心建构“文心”,实现心与物的自然交融。刘勰从感于外物到与心徘徊,实际上是由外向内寻求精神上的家园,从而形成了具有生命意识与责任意识的文道自然观。天地之心与自然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共鸣的内在生命力,“心物交融”正是两者的契合,也是文道自然的体现。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心物关系;文道自然;自然观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4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16
心物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主要探讨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物之间的关系。主观之心既指诗人文心,也指吟咏情性;客观之物既指自然景物,也指现实生活。“心”对“物”有主导作用,“物”对“心”也有制约作用,二者相互交融、和谐统一方能创作出“情貌无遗”的佳作。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认为:“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56,将心有所感、发而为吟回归到自然而然的审美感受之上,肯定了人之情与物之感。刘勰从自然与人文相通的思想出发,一方面认为文学艺术根源于自然,另一方面认为作家可以创作出超越自然的艺术,可以说是将自然规律与艺术审美相关联,以“自然之道”贯穿其文学思想,建立起体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人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与自然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共鸣的内在生命力,“心物交融”正是两者的契合,也是文道自然的体现。
一、感悟自然: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中国古代,人们从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中逐渐形成“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2]1的诗乐舞形式,以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可谓“感悟自然”的萌发。《周易·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将“卦象”对应自然万物,奠定“感悟自然”的哲学基础。《诗经》创作时常常以自然之景或自然之物起兴,引起后文对于情感的抒发,是谓“感悟自然”的文学创作。《礼记·乐记》也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2]61表明心随物感、感物而动。而道家更是以“自然”概括“道”的本质,主张“道法自然”的感物之理。先秦诸子各抒己见,不仅重视对于自然的感悟抒发,更为其奠定了哲学基础与理论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玄学人生观将回归自然作为人生追求,进一步深化对于自然的感悟,不仅拓展所感之物的内容,更是为“感时”“感世”“感怀”等范畴建立起了诗性的话语空间。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2]158,将“气”视为文学创作的本原,基于万物变迁之感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159,提倡对于文学的追求。陆机《文赋》认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2]170钟嵘《诗品》也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4]为开篇,表明对于自然感悟的重视。《文心雕龙·物色》则以“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409开篇,认为季节变动、天气变换、景物变化都能引起诗人心情的感荡。人之心与自然万物交融互动,从而感悟万物活力与自然之道。刘勰继承古代“感物”说的诗性观念,又受到魏晋时期“自然”观的影响,将“感悟自然”的“自然之道”贯穿始终,成为其全书思想与文论批评的重要组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秦汉时期的作品仅仅“寻声得貌”,只停留于对于山水的外在描摹,而缺乏对于自身生命存在的认识。魏晋之后的作品,由于山水诗的大量出现,使得山水成为具有灵性的审美对象。刘勰虽然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批评宋初山水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1]61的情况,但这也客观的表明此时的山水自然已经人们抒发心灵的审美对象。在刘勰看来,山水自然不仅是“天道”“神理”的存在,更是具有生命活力与诗性存在的审美对象,从而以对自然的感悟开始,构建起其自身的天道自然观。正如童庆炳在谈到文心雕龙时认为:“‘天道自然’是返回到我们更古老的先人们对周围的自然世界的理解。”[5]因此《原道》篇认为“自然之道”存在于那些描述自然风貌的“道之文”与“人之文”。天道无时不在、无物不存,“道”将天地万物与人文相互贯通,因而自然万物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力足以感动人心,使心随物转、与心徘徊。
二、构建文心: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魏晋六朝作为精神上极为自由与解放的时代,人的主体性与情感性得到重视,个体的审美趣味也被重新发觉,因此审美心理活动成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关注焦点。古人认为,“心”是人们思想活动的中心,如孟子有:“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6]208认为“心”决定了人的所思所想,由此孟子认为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心”。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也有:“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7]将人心与道心相区分。随后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的观点,表明“心”具有“知善知恶”的道德能力,使“心”进入了伦理学的领域。可见,“心”不仅是人所独有的关键存在,更能够知善知恶、体察万物。因此刘勰十分重视“心”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的功用,倡导“拟容取心”,即作者通过描摹外在事物的状貌,以达到内在情感的抒发。同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重视对于“文心”的构建,寻求一条将“文”“道”贯穿于“心”的途径,既是对人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肯定,更是对于“文道自然”观的升华。
(一)为文之用心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借天地之文引出人文时,认为天地既然具有天地之文,那么人也应当具有人文。因此刘勰从肯定人的价值开始,认为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1]10,将人看作是汇聚天地自然智慧与灵气的中心,所以人对于“文”就具有决定性作用,能够产生人之文。同时,刘勰也区分了“有心之器”与“无识之物”,认为“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1]10表明那些无知的事物还有丰富的文采,有心智的人怎么会没有文章呢?刘勰采用了反问的手法,更加确认了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从“天地之心”到“有心之器”,是为“人”到“人文”,“人心”到“文心”建构了一条合理的道路。并且,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也有两处提及“道心”,一是“原道心以敷章”[1]13,二是“道心惟微,神理设教”[1]14。刘勰认为圣人先贤都是根据“道心”来创作文章经典的。“道心”即“道”的本心,或者说“道”的精妙之处,因此“道”作为文之为文的理论依据,也就体现在儒家的经典之作中,成了“文心”。刘勰认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1]443-444 “文心”即为写文章时的用心,此句可看作《文心雕龙》之解读。刘勰“为文之用心”与陆机《文赋》中:“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2]170一脉相承,都是表达写作文章需要作家之用心,但刘勰是从哲学的角度将“文心”与“道心”相互贯通,不仅认为“文本于道”“道沿圣以垂文”,更将《文心雕龙》之“文心”看作是自我生命意识的充分觉醒,是自然之道的具体表达。
(二)创作之用心
在人的生命意识、自我主体性觉醒的基础上,人不再是被动感受万物,而是能动性的感受自然。刘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构思中都强调人的审美能动性,因此“文心”亦是对于文学本质的探求,体现在作家创作时所具有的个体性与独特性。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以“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1]246开篇,化用《庄子·让王》中的典故,以此来说明文思能够凭借想象,不受约束的到达任何地方。文思即是作家在创作时的想象,也是创作之用心。作家达到“神思”的境界自然就会出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虚静状态。“神与物游”即是心与物之间的双向感应,从而带来审美情感的升华。刘勰提出“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1]431,认为审美主体能够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来选择感应的对象。这种审美感应说明“心”是个体情感的产物,与“情”相关,同时也是纯粹而独一无二的。刘勰强调“文心”的建构要以“情”为本。《文心雕龙·情采》篇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286刘勰认为“情”作为立文之本源,创作之文心,反对忽略情而追求辞藻艳丽的行文创作,认为这会阻碍文心的生发,也会妨碍情感的表达。刘勰在《物色》篇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409概括了“情”“物”“辞”之间的关系。此处的“情”可以看作是作家的文思与内心情感,刘勰强调“情以物迁”实际上就是内心情感在万物自然影响下不断生发的过程,是心随物动,心以物迁。如《物色》赞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1]413是作家通过反复揣摩外物,同时在构思中不断提取精炼出艺术形象与情感表达,从而在情与物、心与物的交融中构建文心。
三、文道自然: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刘勰从感悟万物的自然之道开始,遵循道心,构建文心,以“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1]10,倡导“文道自然”。正如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所言:“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8]在刘勰看来,由人的情志出发,触动万物,形成文辞,是“应物斯感”到“感物吟志”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之道与天地万物一样,都是自然而已。《定势》篇言:“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1]276由于作者的内心情感,思想感情各有不同,因此行文的创作手法也各有变化,但所有的文章都是依据情思来确定文章的体裁,依据体裁形成文势,这种文势便是自然而然的。《物色》篇在论述文学创作与自然现实之间的关系时说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410作家有感于外物,展开丰富的联想,从而随物婉转,选择合适的词语,以求与心徘徊。刘勰从感于外物到与心徘徊,实际上是由外向内寻求精神上的家园,这体现了刘勰自然观中的回归意识。这种回归意识一是回归自然、回归儒家、回归道家所具有的生命意识,二是回归经典、回归文章所具有的责任意识。
(一)文道自然中的生命意识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持之“道”虽然主要来自先秦《易传》和道家,但同时也兼有着儒家的圣人之道,以及儒道结合的文之道,这是刘勰顺应时代的产物,也表明刘勰之心与外在之物的复杂关系。刘勰试图将外物与文心构建一种具有生命意识的心物关系。正如《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1]10的命题一样,刘勰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生成的过程,而且表明“文”的本质和根源是来自于生命本体之“心”。这种从生命意识也即“心”的角度探究文学本体的思维方式,正是刘勰《文心雕龙》所具有的生命意识的最直接体现。由于刘勰处在文学的“自觉”时代,处在审美意识觉醒的时代,所以他的文道自然观中也有着独特的生命意识。《原道》篇首段论及天地万物之文,从自然之道论述人文之道的演变,表明了刘勰审美意识的觉醒与生命意识的回归。刘勰将“自然”看作《文心雕龙》的理论基石,也是批判齐梁浮华文风的武器。他指出齐梁是“为文而造情”而不是“为情而造文”,因而要“正末归本”,纠正齐梁的错误文风,回归自然之道上。同时,《文心雕龙》中也蕴含了对于自然万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赞美。如《原道》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1]10“林籁结响,调如竿瑟”[1]10 “泉石激韵,和若球惶”[1]10;《物色》篇:“山沓水匝,树杂云合”[1]413“春日迟迟,秋风飒飒”[1]413;《情采》篇:“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1]284等等,这些都是在符合自然的运行之道下展现的生命活力。
(二)文道自然中的责任意识
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的《原道》篇中以“天道自然”观照人的存在,彰显了人的价值意义,将人看作是“天地之心”。而在结尾的《序志》篇中,刘勰表达“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1]444认为宇宙无穷,只有依靠才智,才能超出常人。但时间流逝,才智也不能永存,所以唯有依靠创作,才能使声名和事功流传下去。刘勰基于“文心”以“原道”,实质上是从“原人”到“原心”。[9]因此,刘勰在全文的最后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1]450收笔,期望《文心雕龙》能够抒写心意,寄托文思,有益后人。“文果载心”之“心”既是“人心”之情感,也是“文心”之文学,更是“道心”之自然。可见,刘勰的天道自然观也包含了为文之期许与政治之抱负。尽管刘勰在《知音》篇中论及文人身份低微,难以赏识的问题,为天下之文人发出声音,但他却并不止于哀叹,而是认为“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1]439“擒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1]440-441,表明君子定要具备才德,建功立业。刘勰化用《孟子》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6]236一句,认为“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1]441,借此告诫世人得志时就及时建功立业,不得志时就发奋读书。“是以君子藏器,伺时而动”[1]440君子尚且养精蓄锐、伺时而动,常人也应如此。实际上,这是刘勰自己的作为,体现了刘勰儒道兼综的责任意识。
刘勰在自然世界之万物与主体创作之心灵间以“文道自然”相融合,一方面在亦儒亦道的理想之中铸造了进出自如的心灵空间,体现了“文道自然”观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又从文学创作的产生与审美意识的觉醒实现了心物关系的升华,展现了“文道自然”的生命意识。刘勰在感悟自然与建构文心之间,以“心物交融”的内在生命力,体现文道自然观。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80:86.
[4]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1.
[5]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心雕龙[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1.
[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18.
[8]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9]张利群.《文心雕龙》“物色”说之“感物”新论[J].社会科学辑刊,2019,(06):162-169.
作者简介:
高宇宣,女,山东泰安人,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