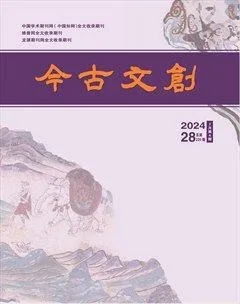论南朝士族创作下郊庙歌辞的新变化
【摘要】郊庙歌辞,始于《诗经》之“颂”,用于祭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先秦儒家主张“乐与政通”,其深层意蕴认为音乐应当以伦理政治为轴心,关乎国家兴衰。气势恢宏、庄重典雅是这类文本的基本特点,其创作受到传统与皇权的制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郊庙歌辞;南朝士族;神灵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4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13
郊庙歌辞是古代帝王用于祭祀的乐歌,从性质上看属于应制文学,反映了各朝君主统治下的国家政治、宗教活动和礼乐文化。罗根泽先生曾评价郊庙歌辞,说其“无性灵、无生气、纯出效颦之机械文字,绝无撮录价值”[1]。萧涤非先生总结这类应制之文曰:“皆类千篇一律,形同具文,了无生气也……颂德歌功,句模字拟,虽协金石,吾不谓之乐府矣。”[2]两位先生的评价有其合理性,但南朝士族创作下的郊庙歌辞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新的文学特征,有必要探究其语言文化方面的自身价值。
一、依五行数制辞
汉人普遍认为天有五方,各有其帝:东青帝、南赤帝、西白帝、北黑帝、中黄帝。汉代《郊祀歌》中的《练时日》有祭祀五帝之辞,分祀中、东、南、西、北五帝,五德分别为土、木、火、金、水。歌辞体式均为四言体。东汉以来关乎五帝祭礼典制继续发展,祀五帝之辞采用五行数体式,始见于刘宋谢庄《宋明堂歌》。而后,南朝萧齐作祀五帝郊庙歌辞沿用谢庄“依五行数制辞”的文体样式。
谢庄出身于东晋南朝高门陈郡谢氏,其父谢弘微在宋文帝时颇受重用。《南齐书·乐志》有载:“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3]172这指出谢庄所制订的郊庙歌辞形制与阴阳五行思想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早在《周易·系辞传》中,曰:“阴阳之义象日月。”[4]便是从对五星的观测以此发现五行学说。《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5]又见扬雄在《太玄》中明确提到:“一六共宗,居北方;二七共明,居南方;三八成友,居东方;四九同道,居西方;五十相守,居中央。”[6]
结合看来,谢庄制辞所依五行数盖为以上所述五行系统。其所作《宋明堂歌》中的祀五帝辞,三言诗《歌青帝》依木数,五言诗《歌黄帝》依土数,六言诗《歌黑帝》依水数,七言诗《歌赤帝》依火数,九言诗《歌白帝》依金数。这已突破汉郊祀五帝歌四言旧制。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谢庄依金数之《歌白帝》篇,《太玄》中既然提到四九同道,谢庄为何舍传统四言旧制而选用九言体。九言体诗句,西晋挚虞认为起于《诗·大雅·泂酌》,此篇三章首句皆为“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在他的《文章流别论》评“古诗之九言者……不入歌谣之章”[7]。颜延之又以“声度阐诞,不协金石”[8]谓九言诗。谢庄用九言体这种前人谓其“不入歌谣之章”的体式为庄严的祭祀仪式乐辞,是一种刻意而大胆的创造。他依五行数作祀五帝辞以适应“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需求。
宋孝武帝祠祭五时之帝“是用郑玄议也”。谢庄创制的祀五帝辞中,其句数和字数都与歌咏之物的五行相对应,由此说明雅乐歌辞的文本样式与祭祀仪礼的对象是一一对应的。《周礼·春官·大宗伯》篇论及祭祀制度时曾探讨以六色玉器祭四帝、天地四方的制度:“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注家郑玄解释说:“礼神者必象其类”,说明了祭祀礼器的选用原则为礼器的形状要像祭祀对象。他进一步阐释曰:“壁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锐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严;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惟天半见。”[9]六种玉器之形状分别对应天地四季,色彩相应地对应阴阳五行、天地四方之学说,配合成套,以为赂神的大典,玉礼器成为人与自然沟通的中介。郊庙歌辞既然用于郊祀礼典上,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祭祀礼器。谢庄正是采用五行数体式作祀五帝祀迎合了“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需求。
《南齐书·乐志》有载:“(齐)建元初,诏黄门郎谢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辞,并采用庄辞。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谢朓造辞,一依谢庄。”[3]172以辈分论,谢超宗为谢灵运之孙,谢庄是谢超宗的族叔。谢氏子弟谢超宗、谢朓作祀五帝歌辞依谢庄之制。
谢朓《雩祭乐歌》祀五帝辞的体式中,所用之数“一依谢庄”。郑玄汲取其前人观点,认为天地之数即五行之数。天数为奇,地数为偶。一到五为生数,六到十是成数。五行的生数和成数要相配合,方能“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如地六配天一,即天一生水,地六成水。谢朓制《歌白帝》九言,依金数取九而非生数四,遵循的也是谢庄依五行数以“象其类”的原则。《周礼·春官·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9]289注家郑玄解之:“春迎青帝于东郊,夏迎赤帝于南郊,季夏迎黄帝亦于南郊,秋迎白帝于西郊,冬迎黑帝于北郊。”[10]故若以万物生长的运行规律论五帝,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应当分别由青帝、赤帝、白帝、黑帝主掌。而若谢朓《歌白帝》选用生数四,则有违白帝在秋天主万物收成之身份。
总之,谢氏高门士族子弟接连为刘宋、萧齐朝廷制作朝廷歌辞礼乐,“依五行数”制祀五帝歌辞,展现了南朝雅乐歌辞的新变化。
二、神灵描写的拓展
纵观《诗经》祭祀之乐歌,诗人颂祖先功德时刻画祖先形象多以神秘而抽象的“无形之象”出现。这是因为在模糊而不精确的宗教概念领域中,人们对神灵的感情也是模糊的。只有通过虚拟化的神秘表象,人们才能在庄严的祭祀氛围中表达虔诚和敬畏。这种“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抟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11]的象外描写,恰好适用于《诗经》颂诗的庄重肃穆之风。
汉魏六朝的郊庙歌辞文本中,有大量对《诗经》颂乐作品中神灵形象的模仿。如汉郊庙歌辞《安世房中歌》,沿袭《诗经》颂诗文风,诗人作品中的神灵大多经历了抽象化过程,在缺乏具体形象的情况下,诗歌转而更注重营造一种虚拟的神秘感和神圣感。庄严的祭拜氛围的强化,促使祭祀者身处其中进而又强化自己精神上的虔诚。这类文本作品不仅缺乏神灵形象的特征,而且还强调神灵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刻意模糊神灵的个体表现。如昊天、上帝、皇天、皇祗等极为抽象的神灵形象。
南朝士族所创制郊庙歌辞,继承发扬了《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在当时重视形式美的风气影响下开始注意到乐辞创制时的意象、句式、句法结构等问题,描写神灵不再囿于抽象的神灵群体,而以细致的笔法、奇幻的意象使神灵形象更加清晰可感,生动细致地描写神灵出现和活动的场景,抓住现实社会中人们崇拜神灵的心理,描绘出神灵的威严和神秘,整体文风趋向艳丽。
早在《汉郊祀歌》中,对于神灵出现时的场景这样刻画:“灵之来、灵之至、灵已坐、灵安留。”而在谢庄所作的《宋明堂歌》的《迎神歌》篇中,他运用色彩词汇描述神灵出现的场景:“华盖动,紫微开”,更显灵动和美感。“柟瑶戺,从珠帘。汉拂幌,月栖檐”以动静之态着笔,细致描摹神灵降临后场景之美。“神之安,解玉銮”刻画神灵安坐后解下所戴玉銮的动作细节,以精微处彰显神灵形象丰富的视觉效果和极具想象的奇幻色彩。沈约《皇雅》辞中有云:“青絇黄金繶,衮衣文绣裳。”也是以工笔手法描摹神灵服饰,用词华丽典雅。又如:
紫坛望灵,翠幕伫神。(谢超宗《齐南郊乐歌·永至乐》)
祭天的圜坛通常用紫色的帷幔装饰,故称“紫坛”。“紫坛”“翠幕”尽展神灵飨坛场面的富丽堂皇和崇高神圣。其《昭夏乐》篇中“紫雰蔼,青霄开”、《齐北郊乐歌》中“灵正丹帷,月肃紫墀”也是类似手法。汉代以前,郊庙雅乐中的色彩词汇并不常见,后来逐渐采用愈加丰富的色彩性词汇,这反倒令神灵形象更加鲜明又添氛围的神秘空灵之感。谢超宗这篇《齐南郊乐歌·永至乐》篇中以“洞曜三光”描摹神灵出现的光芒之景,倒是与谢庄创制歌辞中的一句“贯九幽,洞三光”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意在显现神灵降临的华贵和神秘。
再观颜延之的《迎送神歌》:
金枝中树,广乐四陈……月御案节,星驱扶轮。
这是以烘云托月手法创造出“金枝中树”“月御按节”“星驱扶轮”等飘逸华美的意象词汇呈现祭祀环境。谢超宗所制《齐太庙乐歌》中的“重闱月洞,层牖烟施。载虚玉鬯,载受金枝”、《齐北郊乐歌》中的“溢素景,郁紫躔”等精心排列的意象组合也是如此,扫除了自前代以来雅颂的严肃板拙气息,更添华丽奇幻。
这一时期,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民风民俗,都不再执着于儒学,而选择延续楚辞《九歌篇》、西汉《郊祀歌》中的华丽奇幻风格。从艺术创作思路上看,俗乐已逐步真正渗透雅乐的创作之中。
三、语言风格由板拙向疏朗转变
从语言上看,南朝时期的郊庙歌辞出现了从典雅古奥向清雅流丽的文风转变。雅乐歌辞的典雅特征发展到一定阶段呈现出板拙趋势。南朝郊庙歌辞文风灵活多变,开始呈现出自然生趣,为日益僵化的郊庙歌辞带来一丝明快之风。
魏晋六朝时期道教的兴起和玄学思想的传播,使文人不止注意辞藻的华丽,也开始注重自然,讲究“自然”之美。文人认为修辞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的美。他们在文学创作中逐渐注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流露对生活的热爱、自娱自得的情态。刘宋时期,谢庄《宋明堂歌》中的祠五帝辞除前文所述的体式变化外,从本身的内容上看,增添了不少天然之色。如:
雁将向,桐始蕤。柔风舞,暄光迟。(《歌青帝》)
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大雁南归、梧桐生长的细节,一展明媚的春景。
百川如镜天地爽且明。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歌白帝》)
其中“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一句当是化用了《楚辞》的“洞庭波兮木叶下”[12],而这几句也与谢庄《月赋》的“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13]所描写秋景特质运用的笔法有共通之处。
水雨方降木槿荣。(《歌赤帝》)
景丽条可结,霜明冰可折。凯风扇朱辰,白云流素节。(《歌黄帝》)
玄云合晦鸟路。白云繁亘天涯。鹊将巢冰已解。气濡水风动泉。(《歌黑帝》)
谢庄一改郊庙歌辞厚重的政教色彩,以细腻独特的视角描写四季风光,乐辞风格代替以往的板拙更添清雅疏朗。较于前代严肃庄重的郊庙乐歌,谢庄所作《宋明堂歌》从语言艺术和内容新添上看都更展现出祭乐之辞生活化、文人化的一面。
萧齐时期,谢朓作《齐雩祭歌八首》。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谢朓的诗风清新隽永,展现了新体诗的特点。谢朓在写郊庙歌辞时也插入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符合新体诗特征。如:《歌白帝》:“夜月如霜,秋风方袅袅”“衢室成阴,璧水如镜”“鸟殷宵”“凝冰泮”;《歌青帝》:“景阳阳,风习习”等句。如果孤立地看,这些景物描绘并不逊色于同一时期文人的个人创作,甚至可以被视为郊庙歌辞中对神灵原始描绘的扩展和延伸。自然景物的描绘赋予单调沉重的郊庙礼乐呈现清丽疏朗风貌,此为南朝郊庙祭祀乐辞的独特之处。郊庙歌辞作为官方礼乐文化的载体,内容和风格都当遵循统治君王的明文规定。而南朝君主不乏好文之人,故而祭祀礼乐歌辞的创作在君王许可的范围之内贯入了自然风貌这一灵动因素,俗乐渗透入雍容庄重的宗庙雅乐中,皇权的话语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
萧梁时期,《乐府诗集》中的梁代郊庙之歌皆出自沈约之手。沈约出身于南朝高门士族,吴兴沈氏以武力而强宗。沈约与萧衍加入萧齐“竟陵八友”的文士集团,后萧衍建立萧梁王朝,下令制定郊庙歌辞,对乐辞提出明确规定,敕萧子云撰定郊庙歌辞云:“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14]然沈约所撰,不蹈袭郊庙歌辞典重旧习,而追求语言平易浅切,故不符合梁武帝所定乐制,被其斥为“亦多舛谬”。
如《牲雅》:“反本兴敬,复古昭诚。礼容宿设,祀事孔明。华俎待献,崇碑丽牲。其膋既启,我豆既盈。庖丁游刃,葛卢验声。多祉攸集,景福来并。”[15]260题名取《春秋·左氏传》云:“‘牲牷肥腯’也”,文字浅显易读。又如《寅雅》:“礼莫违,乐具举。延藩辟,朝帝所。执桓蒲,列齐、莒。垂衮毳,纷容与。升有仪,降有序。齐簪绂,忘笑语。始矜严,终酣醑。”[15]255“寅雅”取自《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15]255,寅亮意指恭敬信奉。此句大意是说,协助三公弘扬道化,敬天神祇,辅佐君王。这篇歌辞将意旨复杂的原句以三言体通俗呈现,细致地讲述了敬神仪式的过程,反映了沈约文学观的新变诉求,赋予了典重的郊庙歌辞灵动的文学特质。
南朝文学对文体韵律和修辞美的追求落到郊庙歌辞的创作上,致使南朝郊庙堂歌的语言风格一脱僵化沉闷,且歌辞中自然描写的增多,更显风格的疏朗灵动,些许淡化了郊庙雅乐一直以来庄重严肃的政治性色彩,文学价值进一步上升。
四、结语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郊庙歌辞可谓是微不足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否认郊庙歌存在的重要性和价值。它们是在君主专制国家的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更多的是对国家政治形势和权力斗争的一种回应。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赋予文学巨大的意义,并通过行政手段使其迅速繁荣起来,但这是以文学本身的自主性为代价的,郊庙歌辞在创作上的昙花一现验证了这一规律。
南朝士族出于维护自身地位的需要,在创作郊庙歌辞过程中,一方面保持了传统的郊庙礼乐范式,另一方面突破雅颂传统四言旧制,遵循“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需求按依五行创制雅乐歌辞新体式,内容上风格一改疏朗,通过增加自然山水、人文历史等内容,采用较为简单的语言进行创作,开始注意到乐辞创制时的意象、句式、句法结构等问题,以精美的意象组合和飘逸美感的词汇刻画神灵,增加了“毫无生气”的郊庙歌辞的可读性。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9.
[3]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王弼注,韩康伯注,孔颖达疏,陆德明音义.周易注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5]班固.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6](汉)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李昉.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清)严可均著,苑育新校.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郑玄注,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1.
[12]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沈约.沈约集校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