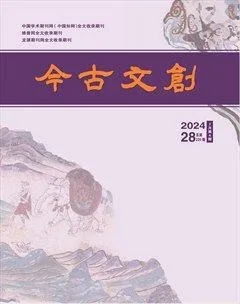从刘禹锡声诗创作看中唐士人对民俗的作用
【摘要】本文选取刘禹锡为中唐时期的士人代表,探讨其创作对民俗的作用。从刘禹锡声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与个人条件讲起。民俗为其声诗创作提供了素材与主题,是其贬谪失意时的情感寄托,相应地,刘禹锡身上也体现出对民俗之美的主动关注与发现。他将地域文化与风俗上升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审美内涵,在过程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有自觉的教化与引领。通过刘禹锡一人,可以以小见大,管窥中唐时期乃至有唐一代士人与民俗之间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刘禹锡;声诗;民俗;《竹枝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3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12
中国古代视阈下的“士”往往兼具读书人与官员身份,是文化的承担者与时代的引领者。唐代民俗是一个既向上联系着权力操控者与最高统治者,又向下联系着底层普通百姓的圈层,他们具有敏于观察、善于反思、善于交流的特性。底层普通百姓的民俗对他们而言,既有区别于自己的部分,又有相通和互相影响之处。①本文以中唐时期刘禹锡的声诗创作为例,致力于阐明士人阶层在这一时期与民俗之间的作用关系。
一、刘禹锡声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与个人条件
“唐声诗”一词为任半塘《唐声诗》一书首倡。唐诗有“无声”者,有“有声”者。他在文中对“声诗”名目由来、与“歌诗”“乐诗”等的区分进行了说明。②“声诗”的歌唱在唐代蔚为风尚,孟郊《教坊歌儿》一诗便发出“能诗不如歌”的感慨。③“诗”在有唐一代受到重视不必多言,但在“歌”前,也如此逊色。足见“歌”在当时风靡一时。中唐时期有声诗创作者不止刘禹锡一人。以在有唐一代一度风靡的竹枝词为例,刘禹锡、顾况、白居易等人均有创制。刘禹锡以其独特的贬谪经历与对民风的细致观察,则使其声诗创作在浩繁卷帙中脱颖而出。
刘禹锡一生先后被贬至朗州、连州、夔州,在这三处辗转近二十载,与三地的民风民俗接触密切。此三地均属于楚文化圈,自先秦便有荆巫祭祀、歌舞迎神的风俗。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一诗中有“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 ④,便是他在朗州时所观。赛神,即报神福。又如《南中书来》一诗中有直言连州一地风俗“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头” ⑤。《礼记·曲礼下》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⑥。可见朗州、连州、夔州三地由于与京畿文化圈相距甚远,地处偏僻、风俗简陋。刘禹锡与当地民俗的关系,在阶层的区别外,又更加注入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在这些条件下,民俗如何反渗刘禹锡,他又如何观照与引领当地的文明,则更加值得关注。
另一方面,以刘禹锡为代表的中唐士人普遍表现出一种对下层民众的关注。从中唐士人的身份来看,他们身上体现出社会角色多元化的特性。如在刘禹锡本人身上,便经历过举子、进士、京官、幕僚、地方官等多种身份转变,尤其是前文提及的外放经历,为他与底层民众的风俗有更深入的接触提供了许多条件。
从中唐士风来看,在经历藩镇割据、经济凋敝的重重乱象后,这一时期的士人文化承担者与时代引领者的自觉性被激发出来,普遍有儒家积极入仕、关怀现实的政治诉求。刘禹锡自称“世为儒而仕”,更可见其家庭有十分浓厚的儒学氛围。在文学层面,也体现为对底层民众的主动关注和细致描写,刘禹锡本人更有自觉向民歌学习的态度:“虽甿谣俚音,可骊风什” ⑦。
此外,刘禹锡本人在音乐、曲调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他在评价民歌时,能关注到其中的曲调与风格。如据《竹枝词》引,有:“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 ⑧他在作词时不仅遵循普遍的格律平仄,更观照了音乐的本质,做到了倚声填词。其对《忆江南》一词的创制,在调名下有自注曰:“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⑨前文提到,声诗除需音乐外,还要结合声乐与舞蹈。白居易《忆梦得》自注提到:“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 ⑩可见其《竹枝词》民歌的演唱水平已经很高。总言之,刘禹锡的声诗创作有以上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由此而生发以下探讨。
二、取用于民,自觉教化
民歌这一民俗文化与刘禹锡关系密切。民歌兼声、词、舞三重艺术形式,又不受场地与条件的局限,为刘禹锡的声诗创作提供了无穷尽的创作契机与创作素材。刘禹锡的有些声诗作品更是将歌辞的风格内容与怀古、个人际遇相结合,实现了内涵与艺术表现力的双重升华。相应地,刘禹锡在这一民俗的发展路径上,也可谓功不可没。前文提及过,士人阶层敏于观察、善于反思,是文化的承担者和文明的引领者。面对朗、连、夔三州的僻陋风俗,除对其中自然率性之处的欣赏外,同样有刘禹锡通过理性反思,认为应该被修正与引领的部分。其实,对远州陋俗的改顿是元和年间这一批南贬文人的共同举措,但各自的途径有所不同。刘禹锡顺应民俗的现实情况,改写《竹枝词》的途径体现了取用于民的特点,能有效地实现以风俗易风俗的教化路径。
元稹《赛神》《竞舟》等是建议通过限制此类集会举行的规模与频率,即一种政治举措来实现。这在整改民风中有强制性质,效果可能立竿见影。但需知民风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也有士人选择更为潜移默化的路径,如柳宗元利用佛教死后想象来改化柳州风俗。
佛教的死后想象将人的存在与实现善的道德路径紧密相连。这正为其用于匡正风俗规范提供一种合理性。面对柳州当地居民蒙昧、随意杀生,佛教轮回讲在世行善,以求来世得善果可资利用。这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有所记录。柳州当地民俗迷信祭祀,心中缺少仁义,对杀戮之事不避讳。想要革除,需要从当地民俗惯于血祭的风俗开始改变。但礼对民众内心约束力似乎不足,刑罚又很难完全使一种深入人心的风俗被禁止。于是,他提出“唯浮屠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并针对上述乱象,一一条列清楚了佛教可供借为改顿之处:
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其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使复去鬼息杀,而务趋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去焉而顺之。庶乎教夷之宜也。⑪
利用佛教果报及死后想象在较落后之处,能达到较为立竿见影的约束作用。但仍需看到,如果放纵佛教果报思想发展,则仅是在蒙昧上披了高级宗教的外衣。使民众陷入对于地狱想象的畏惧,以这种心理来约束行为,并不属于开民智之举。在文明开化之处,佛教于政治教化的施行反而有害。事实上,他所谓佛教“阴助教化”的功用发生背景本身便有所限定,类于一种“权宜之计”。
刘禹锡在以欣赏态度观照南方民俗时,也保持了理性态度。如《楚望赋》引中:“系乎天者,阴伏阳骄是已;系乎人者,风巫气寙是已。” ⑫此句便简略概括了朗州气候炎热、民风信巫鬼而性怠惰的特点,文中则记述更详。又如《南中书来》一诗,言连州风俗“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头” ⑬。新旧唐书对刘禹锡面对南方诸州风俗的举措均有记录,言语略有差异而内涵一致。即言朗州民俗好巫,祭祀时歌《竹枝》鼓舞。但原本的歌词十分俚俗。刘禹锡于是依照屈原沅、湘间作《九歌》的做法,倚原《竹枝》之声,新作《竹枝词》十余篇。从那之后,武陵百姓歌唱的《竹枝词》,大多都是刘禹锡新作的。又有刘禹锡自叙《竹枝词》九首引,更加清晰地记述了其创作过程与目的。刘禹锡首先提出“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由不同自然环境生长出的歌谣,虽然在声音的表现上有所差别,但都符合音乐的本质。《竹枝》有短笛、击鼓伴奏,融歌、乐、舞为一体,民众即兴、随口而唱。虽然存在言辞粗野等缺陷,但歌曲激越清脆、富有情韵。于是他效仿屈子《九歌》的做法,将其中鄙陋的词语加以删改修饰,并认为他所改订的《竹枝词》是为“变风”,和风骚之义一样能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刘禹锡《竹枝词》不仅对下起了教化民众的功用,他记录民俗,更有效仿“采诗”的意图。据《汉书·艺文志》: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⑭
先秦之后,随着“采诗”之风消逝,音乐、诗歌委婉含蓄批评朝政的功能逐渐淡化。但时至中唐,士人仍然期待诗歌能够担负起美刺功能。白居易曾呼吁重设采诗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刘禹锡同样有这样的思想,如《采菱行》题下在解释武陵的采菱风尚后,有一句:
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⑮
这句言《采菱行》的创作契机与意图。据《尔雅翼》记载:
吴楚之风俗,当芰熟时,士女相与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为繁华流荡之极。《招魂》云:“涉江采菱发《阳阿》。”《阳阿》者,采菱之曲也。⑯
可知采菱曲便是吴楚芰荷成熟,男子女子相伴采集时所唱和的歌谣。这里又引《招魂》,解释采菱所唱的歌谣便是《阳阿》。结合刘禹锡《采菱行》题下所言,可知采菱曲自古便有,但其歌词几乎没有流传下来的,于是刘禹锡倚声填歌词,来等待采诗者。即记录民风的同时,更显其对乐曲、歌词的自觉传承。再如前文提及《插田歌》引,写诗人连州登楼远眺村庄,有所感发,“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⑰。
如前文提及,士人既向上联系着权力操控者与最高统治者,又向下联系着底层普通百姓。刘禹锡书写俚歌,以俟采诗的做法即对南方民众有反馈民情与改造民风的双重效果。反馈民情的作品以《插田歌》为代表,前文已引前半段对田间俚歌场景的描述,此为反馈民情中自然民风的一层。后半段则笔锋一转,通过记录计吏与田夫的对话,进一步实现了诗歌的美刺功能—— “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⑱。一个无知又狂妄的计吏,靠着微薄的利益付出,竟然成了朝廷官员,可见当时卖官鬻爵之滥。
改造民风的部分则如前文提及将民间传唱竹枝词的俚俗之语加以修饰改变,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这一途径则与元、柳的方式有所不同。一方面,它补足了前者效果立竿见影但不足以深入人心的缺陷。另一方面,雅言教化民众,而不是引入其他宗教约束民众,是依民风而改民风的举措,充分考虑到了当地风俗习惯的独特性与可利用之处。体现了刘禹锡声诗创作从素材、形式到功用都取用于民的自觉教化路径。
三、将地域民俗整合为文化内涵
刘禹锡对《竹枝词》进行了有意识地规范与创作。他明确界定的《竹枝词》主题与功能,对于其形成独立的文体并得到传播发扬,显得意义重大。刘禹锡《纥那曲词》其一中有:“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杨柳枝》与《竹枝词》均集歌、乐、舞为一体。据任半塘《唐声诗》,《杨柳枝》为唐代舞曲,贞元年间白居易曾改制。⑲两种相似度的诗体相提,又指出了竹枝传情的特点。又有刘禹锡《堤上行》其二言:
江南江北望烟波,人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⑳
此诗中,他从感情基调这一角度将《竹枝词》与《桃叶》作了严格区分。他认为《桃叶》主传情,《竹枝词》主抒怨。即结合来看,《竹枝词》主要用于抒发怨情。在这样自觉的艺术风格认知下,刘禹锡《竹枝词》便体现出明显的幽怨的特质。现存其十一首《竹枝词》,均是描写景致与抒发哀怨情怀相结合。前九首用古体,后二首用近体,可见刘禹锡对《竹枝词》的改制选择较为自由,以此容纳了民歌的天然任情的情致。
钟惺评《插田歌》云:“风土诗,必身至其地,始知其妙。” ㉑作风土诗,尤其是《竹枝词》这一类深深植根于地方民俗的诗歌,更需要深入了解和感悟,并浸透于荆楚地域文化的熏陶中。刘禹锡在朗州、连州、夔州这三处辗转近二十载,加上前文所述诸多个人条件,才有机会倾尽自己的真情,将荆楚的风物人情、民风民俗写入《竹枝词》中。晚唐时期,竹枝的传唱已经不局限于荆楚巴渝,如杜牧《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一诗有:“楚管能吹柳花怨,吴姬争唱竹枝歌” ㉒,可见竹枝歌已经上升为楚地独特的文化标志。但刘禹锡后,文人的《竹枝词》写作蔚然成风,但大多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深入的契机体悟荆楚的文化,大多在文化成就上已经不及刘禹锡。
总的来说,以刘禹锡为代表的一代富有辞采的士人,在推动竹枝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楚文化符号中可谓居功至伟。一方面,他进一步明确了文人的《竹枝词》创作在情感、内容、艺术手法上与传统民歌如何达到一种调和的状态,使其雅俗得当、浓淡适宜,能够以一种民俗的途径修正其中鄙俗的成分。另一方面,作为贬谪士人,他以一种热情的目光欣赏与记录从未见过的风土人情,又致力于推广自己修订后的《竹枝词》,使其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为《竹枝词》文化内涵的形成与向楚文化圈外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注释:
①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346页。
②任半塘:《唐声诗上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③孟郊:《孟东野集》卷三《感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9页。
④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94页。
⑤⑬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71页。
⑥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曲礼下二》,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370页。
⑦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下》,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928页。
⑧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17页。
⑨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94页。
⑩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1页。
⑪(唐)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311页。
⑫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下》,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933页。
⑭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清乾隆四年刻本,第2684页。
⑮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4页。
⑯罗愿:《尔雅翼》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页。
⑰⑱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62页。
⑲任半塘:《唐声诗下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页。
⑳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3页。
㉑钟惺著,谭元春选评,张国光点校:《诗归》卷二十八,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㉒杜牧:《樊川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第151页。